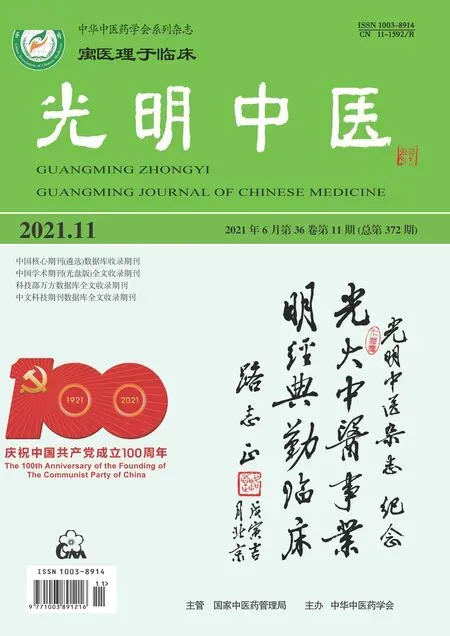王誠喜教授治療肺炎支原體肺炎驗案2則*
沈小芳 李 紅 王誠喜
肺炎支原體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MPP)是由肺炎支原體(MP)入侵機體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其西醫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中醫將MPP多歸屬于“咳嗽”“肺炎喘嗽”范疇,王教授認為其多因風溫內襲、肺衛不固、溫熱傷肺,導致肺絡受阻,肺氣郁閉,甚時痰、熱、瘀、毒互結而為病。MPP多發于兒童及青少年,其發病率在社區獲得性肺炎中占10%~30%,秋、冬季發病率明顯高于其他季節[1]。支原體肺炎雖然以往被認為是一種自限性疾病,但是結合最近幾年的臨床概況,該病的復發率和病重率都在逐年增加[2],其治療不及時或者初期治療未達到治療效果時,往往延誤病情,使其向重癥及難治性發展,甚至可以發展到肺外,引起心肝腎等臟器損害,尤其致病人群多以小齡兒童以及免疫力欠佳的人群,嚴重影響患者健康以及生活質量,甚至危害生命[3]。
恩師王誠喜教授是衡陽名中醫,研究生導師,防治呼吸疾病方向專家,其基于目前西醫治療該病的大環內酯類抗菌藥耐藥性不斷上升的環境背景[4],深入研究分析肺炎支原體肺炎,總結多年臨床經驗,根據其發病的病因病機以及發病特點,認為該病應強調防與治,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盡早用藥,筆者有幸跟隨王教授學習,現將其經驗淺述如下。
1 西醫發病機制及治療
目前MPP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目前主要的發病機制有:呼吸道上皮吸附作用、呼吸窘迫綜合征毒素、免疫學機制等,其中尤以免疫學機制為主[5]。當前MPP的西醫治療除了一般治療和對癥治療外,主要為抗菌藥治療、激素治療、免增強劑治療以及肺外并發癥治療等。臨床最常用的治療措施即為抗菌藥治療,根據MP的特性,臨床常用大環內酯類抗生素(以阿奇霉素為代表)治療,但由于MPP的發病率和復發率升高及耐藥率升高,導致臨床治療效果減弱。使得早期治療時未能達到預期治療效果難以控制病情或治愈疾病,其重癥、RMPP以及肺外損傷發生率增加。并且近年來常用的阿奇霉素在未成年患者使用的安全性至今尚未明確,而我國部分醫院存在盲目采用靜脈注射治療措施,這是有欠妥當的[6]。
2 中醫病因病機探討
王教授認為本病多為風熱毒邪侵襲肺系所致,可歸屬于咳嗽、肺炎喘嗽的范疇,肺為華蓋,鼻為其外竅,與自然相通,且衛氣固護機體,抵御外邪,故當外邪入侵,首犯肺衛,肺主宣肅,邪氣閉肺,氣機升降出入失司,宣降失常。又“六淫之邪皆從火化”,外邪入里,易郁而化熱,肺愈閉則熱愈盛,熱灼肺金,煉津生痰,痰熱互結,阻滯氣機,導致肺絡不通,久之痰瘀熱毒夾雜而為病。《素問》云:“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故王教授根據“熱淫于內,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在此基礎上自擬方制成支炎合劑,行“清熱化痰解毒,宣肺開閉通絡”之功,結合辨證論治,臨床療效肯定。
3 驗案2則
案1患者周某某,男,6歲。咳嗽3周。家屬代訴:患者3周來無明顯誘因出現咳嗽,干咳,咳黃痰,量稍多,晨起尤甚。在家予自服銀黃顆粒+霧化(具體用藥不詳)后咳痰癥狀稍好轉,但未愈。今為求中醫藥特來衡陽市中醫醫院就診。刻下:陣發性咳嗽,咳黃痰,量一般,質偏黏,活動后及咳甚時氣促,咽干咽癢,口干多飲,喉中時有異物感,無流涕、噴嚏、惡寒發熱癥狀,大便偏干,日一行,小便偏黃,量少,有熱氣。納呆,夜寐一般。舌質紅,苔薄黃,指紋紫滯。王教授見癥予查肺炎支原體,提示:肺炎支原體抗體陽性(1∶160),體查:咽部稍充血,無扁桃體腫大;肺部聽診未聞及明顯干濕啰音。結合患者癥狀、體征及相關輔助檢查結果,考慮中醫診斷:肺炎喘嗽(痰熱閉肺證),考慮西醫診斷:肺炎支原體肺炎。治療上予支炎合劑,處方:黃芩70 g,牡丹皮70 g,浙貝母70 g,地龍(燙)70 g,苦杏仁70 g,葶藶子70 g,海風藤70 g,白果42 g。上8味煎煮2次,蒸餾濃縮,丹參140 g研磨成粉,生姜210 g榨汁,魚腥草210 g與五味子42 g蒸餾提取揮發油合制而成。上方制劑以5瓶,每日口服3次,每次20~50 ml,若咳甚及咽干咽癢甚時可加服。
按:王教授認為現值冬春交際,陽氣始升,可見風溫夾雜犯肺,或風寒化熱侵襲機體,導致肺衛不固,宣降失常,肺氣閉阻,邪郁化熱,灼傷肺金,煉津成痰,痰熱氣閉而發為本病。小兒臟腑嬌嫩,且易陰易陽,用藥切勿過攻伐,加之患者現無明顯急癥,故支炎合劑治療,本方中魚腥草性味辛微寒,主入肺經,善清肺熱,可清熱解毒,消癰排膿。黃芩苦寒,主入上焦心肺,善清氣分之熱,二者清熱解毒共為君藥。丹參、牡丹皮走血分,涼血祛瘀,加強君藥清熱之功,使氣血兼顧。葶藶子、浙貝母、杏仁、白果共為佐藥,共奏清熱止咳、瀉肺平喘之效。五味子斂肺止咳,葶藶子瀉肺平喘,二者一瀉一斂,使肺之宣降功能恢復。地龍、海風藤走肺絡,和血脈,加強全方化痰通絡行氣之功。加生姜防止涼遏,且可溫肺止咳。諸藥合用,配伍嚴謹、標本同治、清溫并用,升降得宜,宣斂并施,使熱毒清、肺氣宣、痰熱除、經絡通。
案2患者謝某某,女,45歲,咳嗽咳痰1個月余。1個月前患者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體溫38.0 ℃,咳嗽,少痰,痰色白可咯出,頭痛不暈,未見鼻塞流涕、惡風癥狀,自服止咳糖漿+抗菌藥+退熱藥(具體用藥不詳)癥狀發熱癥狀緩解,繼續服藥止咳糖漿2周癥狀未見好轉,咳痰漸多,遂于當地社區醫院診查示:血常規:WBC:11.29×109/L ↑,MONO%:44.50% ↑,MP-IgM(+),肺部X片提示肺紋理增粗,左肺下野少許片狀浸潤影,考慮炎癥可能。今患者至我科就診,刻下:咳嗽氣粗,咳聲重,咳黃痰,量稍多,質一般,咳甚時伴胸悶痛,無痰中帶血,咽干咽癢,口干不苦,欲飲,納寐欠佳,二便調。舌紅,苔薄,脈滑。素體肥胖,既往體弱易感。王教授考慮該患者診斷為:中醫:咳嗽(痰熱郁肺證),西醫:肺炎支原體肺炎。治以清熱化痰,開肺止咳。治療上予支炎合劑6瓶,50~80 ml/次,每日3次,咽癢咳多時可加服;二陳止嗽散加減,處方:陳皮10 g,法半夏10 g,紫菀15 g,百部10 g,桔梗10 g,白前10 g,浙貝母10 g,桑白皮20 g,甘草5 g。上方5劑,日1劑,水煎服,分2次溫服。服藥1周后二診時癥狀較前好轉,稍有咳嗽咳痰,量不多,易咳出,偶有咽部干癢,無咽痛。納寐可,舌質淡,苔薄白,脈滑。囑患者繼續支炎合劑3瓶以鞏固治療。
按:王教授認為肺主呼吸,調節宗氣的升降出入,邪侵肺衛,肺失宣肅,肺氣上逆則咳;另王師還指出古言有云: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是以其治療咳嗽除關注肺衛之外,還基于“聚于胃,關于肺”的治肺理論[7],脾胃運化水谷精微,脾失健運,則衛氣不足,痰濕內生,衛氣不足則邪氣易侵,痰濕內生則加重肺病。該患者咳嗽1個月余,病程較長,系平素正氣不足,外邪犯肺,肺失宣降,久之邪氣入里,郁而化熱,火熱毒邪內蘊,煉津成痰,加之素體有痰,痰熱互結而發為本病。治療上予支炎合劑,清熱化痰,宣肺開閉;配合理氣止咳之二陳止嗽散加減,《醫學心悟》中云:“本方溫潤和平,不寒不熱,既無攻擊當過之虞,大有啟門驅賊之勢。是以客邪易散,肺氣安寧”;結合患者咳聲重而黃痰多,加大量甘寒之桑白皮、苦寒之浙貝母以清熱化痰、瀉肺止咳。是以共奏清熱化痰理氣,開肺通絡止咳之功。
4 結論
王教授認為該病多為肺衛受邪,邪氣入里化熱,蘊結痰氣熱瘀,灼傷肺金,導致肺絡受阻,痰氣熱瘀內閉而發病,秉持治病求本的原則,治療上多以驗方制劑支炎合劑為主,結合辨證論治,奏清熱化痰解毒,宣肺開閉通絡之功,臨床療效顯著。且根據患病人群特點,在遣方用藥方面注重攻補得當,多用平和之藥劑為主,根據其痰氣熱閉等程度進行用藥加減,以助邪出體。本病的中醫辨病辨證明確,中醫藥治療優勢明顯,積極的中藥介入有利于減少抗菌藥的濫用,且已有的中藥制劑口感好、攜帶方便,臨床收效頗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