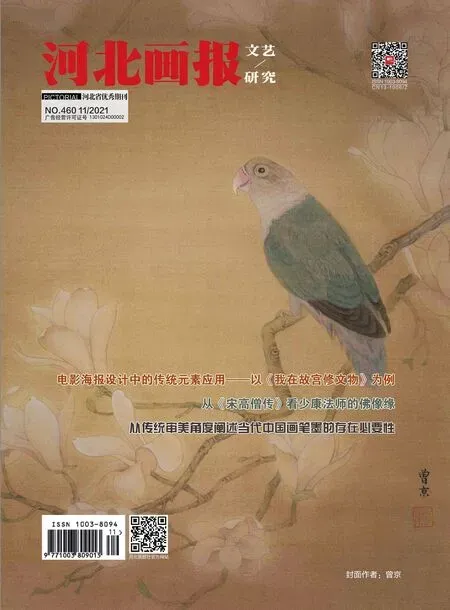探尋中西融合的美術家李文珍
于童
(作者單位:天津美術學院)
20世紀的中國畫壇涌入了西方各種帶有前衛先鋒色彩的藝術流派,中西藝術文化交流變得頻繁且密切。許多留學在外的學生,在回國后一邊傳授西方藝術理念和繪畫技巧,一邊探索和找尋著中西融合的道路,他們在藝術上的探索,已然成為了當時國內藝術變革的縮影。師從于王悅之的天津籍畫家李文珍,在探索西畫民族化的過程中,也在把自己對藝術的理解和思考播續給更多熱愛藝術的學生和青年。
李文珍(1914-1999),又名李昂,以字行,生于天津南郊雙港鎮高莊村一個開明士紳家庭,少時背離家庭只身學藝。1934年考入王悅之創辦的北平美術專科學校,系統學習西方油畫。1939年考入著名油畫家衡山映兒創辦的東方美術研究院。1945年進入天津耀華中學教授美術。1979年任天津文聯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天津分會理事。
在北平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期間,李文珍追隨著王悅之系統地學習到了西方印象派的繪畫技法,同時受其師的影響,也在摸索著中西繪畫語言融合的道路。王悅之所描繪的物象,用筆取中,取材用西,并能在顏色上找到二者的相同之處。他常用中國畫的必用色——黑色來作畫,他認為:“光色的混合是白色,顏料的混合達到飽和則是黑色;黑色包含了各種顏色,黑色是最豐富的顏色。”從李文珍30年代創作的作品中,發現他也沿用了黑色,如《自畫像》,人物輪廓是用墨線來勾畫的,流暢而不凝滯,整體色調偏黑偏暗。但相較于王悅之的人物肖像,李文珍更多的是保留了印象派對光影的處理方法,顏色明暗的過渡更為柔和。應該說這幅作品是李文珍早期在中西畫法融合上的初探。另外,在風景畫的創作中,他也有類似的嘗試。如《香山碧云寺》,所有物象皆是用黑油線來勾畫,表現遠近時又采用了中國畫的高低法,但作為一幅油畫,整幅畫面不留白,景物的大與小、明與暗、清晰與模糊與遠近自成比例。經過幾年在北平美術專科學校的學習,李文珍不僅掌握了印象派的表現手法和畫理知識,還嘗試在油畫中融入國畫的繪畫技巧,這也為他日后畫風的發展和成熟奠定了基礎。
1939年,李文珍畢業后加入畫家衡山映兒創辦的東方美術研究院,結識了三浦勝治、金冶等藝術家。1945年后,受到蔡元培“美育興國”理念的感召,李文珍從北平回到天津任教于天津耀華中學,教授美術。李文珍一面致力于美術教育事業,一面堅持創作。回到老家熟悉的環境,使得他在這一時期的作品與在北京求學時的沉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其50年代的《自畫像》為例,用色較于前者更為豐富、對比度更強,筆觸也更為明快,且逐漸顯現出后印象派的特點,展現出脫離王悅之畫風,自身風格漸臻的特征。
新中國成立后,在耀華中學韓峰校長的支持以及李文珍的建議下,于1954年專設了一間大學標準的美術教室。在教學中,李文珍重在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會要求學生怎樣去做,他經常對學生說:“我不管你怎么畫,畫得多爛,一定要畫出立體的感覺來。”[1]當時國內院校主要教授的是契斯恰克夫素描法,即用科學知識在二維的平面上對客觀物象進行立體化處理,還歸納出了“五大調子”的程序性、系統性和科學性的訓練方法。但李文珍認為素描不是繪畫練習的初步手段,而應是一件獨立存在的藝術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切不可按照所謂的步驟把人理解為不同面的外殼。在作畫前,首要的是先去觀察,之后再把自己的感受和思想用最短的時間畫出來,而不是長時間地去涂抹和摳劃某片調子或細節。看他所描繪的人物,不論是同事、學生還是家人,都能抓住每個人物的姿態和表情特點,傳遞出畫者本人對所描繪人物的感受。如20世紀50年代所作的《賣魚的人》。背景僅用寥寥數筆帶過,中景的賣魚人和前景的魚攤則多有刻畫。盡管賣魚人的五官并不清晰,但從其姿態上還是能感受到她在招攬生意時的熱情。另外在色彩的應用上,他認為應該要“因物象形,隨類賦彩”。他曾說過,“色彩是衣服,素描是人體,兩者是表和本的關系。”[2]在后印象派畫家的認識中,色彩具有獨立性,擁有空間和形體,無須依賴對客觀對象的描寫,而是要回歸內心與自我,成為表達的載體。在同名油畫作品中,背景選用了暖色調的紅色,既表現了賣魚人的熱情、魚的鮮活,又能讓人感到畫者的愉悅之情。賣魚人身穿黑色上衣和白色圍裙,售賣的魚都呈藍灰色與背景形成鮮明的對比。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是,賣魚人的圍裙非常干凈,這說明畫者趕在剛出攤的時候就來買新鮮的魚了,也表明他有多喜歡吃魚。由此可以看出,李文珍在處理色彩與素描之間的關系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而整幅畫面又能呈現出中國畫所追求的“氣韻生動”。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李文珍此時已經從中西技法的融合,深入到中式的藝術理念與西式技巧的交融。
在風景畫中,李文珍巧利用冷色和暖色,透明色和不透明色的對比,巧用同族色彩在一個調式中的演進關系等來構圖。比如《海河余暉》,畫面中以黑色和黃色為主色調。落日時分金黃色的海河,遠處咖黃色的建筑和近處橘黃色的岸邊把觀者的視線引向畫面右上角逐漸隱沒在黃色天際的紅色落日。停靠在岸邊的深黑色漁船與岸邊結伴而行的灰色人影,都在說明天將至夜。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海河上出現的一抹白色的桅帆,它的出現讓觀者的視線直接聚焦于此,如此就打破了焦點透視,轉而成為了中國畫的散點透視;近處的堤岸呈俯視的視角,而遠處的建筑又變成了平視的視角,多視角的處理方式又與西方后印象派大師塞尚的多點透視法相似。
另外在靜物畫的創作上,也同樣讓人容易與后印象派大師塞尚的作品聯系在一起。比如他畫的《瓶花》,背景是由透出一絲藍的黑色和前景中的淺紅色桌布構成的。桌上的花瓶呈藍白色,瓶中的花也是以藍白和粉紅色為主,好像要從背景中躍出來一般。此外,花瓶好似并沒有安穩地放在桌子上,整個桌布的格線是從左下向右上傾斜的,平底的線條與畫面邊緣平行而置,而花瓶把手的上沿和下沿則又與網格平行,讓畫面呈現出某種穩定。如此的處理效果與塞尚的靜物畫多有相似之處,“色彩的變化總是與平面的運動相呼應。”[3]但不同于塞尚的靜物畫的地方是,塞尚的作品帶給人的感覺是如大理石般無生命的物體,而李文珍的靜物卻能傳遞出某種情緒。因此,盡管二者的作品透視的方法多有相似,但李文珍更多是在追求精神而非科學,而塞尚則反之。而這也同樣可視為一種將中國藝術理念與西方繪畫相融合的表現。
在西畫創作的過程中,他對中國傳統繪畫的癡迷程度一直未減。60年代創作的戲裝人物畫,把戲曲藝術和水墨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李文珍曾學過小提琴,對舞臺上的“無”和“有”,與筆墨間“虛”和“實”之間的微妙關系,處理得非常巧妙。畫面中呈現出的中國畫的寫意性和西方繪畫的表現性,可以說是一次用西方藝術來表現中國畫的探索性嘗試。
經過三十年的探索和開拓,李文珍確立了自己的風格,畫面所呈現的色調更為多樣,且帶有中國寫意畫的特征:形服從神,追求強烈的形式感和藝術趣味。他所記錄的不僅是生活,還體現了從客觀世界無法看到的情感、趣味和千變萬化的藝術美。[4]真正地做到了把中國人的藝術理念與西方的繪畫技法相融合,呈現出既有濃郁后印象派風格,同時又不失中國人精神理念的藝術作品。
20世紀70年代,李文珍在授課之余,還在自家的客廳里辦了一個可以暢聊藝術的小“美術沙龍”。當時來此交流的不僅有他的學生,還有許多熱愛藝術的年輕人。在那個文化貧瘠而蒼白的年代,這樣一個小小的“沙龍”讓求知甚切的年輕人,如沐春風,耳目大開。70年代末,李文珍不再在耀華中學教課,但對登門看望和拜訪他的學生和熱愛藝術的年輕人,仍愿意談天說地,且不斷地鼓勵他們不要放棄藝術。這時期他的繪畫開始以刀代筆。以其80年代所作的《自畫像》來看,這時的筆觸更顯老辣,線條和輪廓已經退居次位,利用色彩的明暗對比等方法,表現出沉穩中不失活潑的效果。這一時期創作的油畫作品還有《墻子河》《青島遠眺》《美人蕉》《圓明園》等。相較于執教時期的作品又有改變,呈現出大寫意的效果,有些顏料是直接涂在畫布上的,使得畫面呈現出許多畫筆無法完成的充滿激情的線條。為油畫技法寫意式的即興表現,開拓了一條嶄新的境界。
1979年11月,各屆畢業生聯合發起了一次大型畫展——《李文珍暨學生畫展》,在天津群眾藝術館展廳展出,并應邀去塘沽、青島展覽。秦征在展覽前言中評價他:“在風驟雨復的境遇中,不問行市,不趕浪頭,不人云亦云。……用天真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嘴巴說出自己想要說的話……”1999年10月23日,李文珍先生辭世。2008年《本色人生——畫家、教育家李文珍》畫集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當時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讀書報、中國日報(英文版)、中國文化報和今晚報均有報道。同年,各界學生再次集聚在天津美術學院美術館舉辦了《李文珍繪畫作品展》。十年后,又在同一個地方展出了名為《現代主義的潛流——李文珍先生藝術與文獻展》,全面且集中地呈現了李文珍先生一生的藝術發展和教育理念。今天,當我們回看李文珍一生的藝術發展時,會發現他一直都在追求中西畫法的融合,也一直并貫徹著“藝術家不能僅僅畫你看得見的東西,不去畫你看不見的東西。”
李文珍先生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擔任教師以來,一直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他所繪畫的“風花雪夜”的主題,由于太過平淡,一開始在“主流”藝術圈子中并沒有任何影響,藝術家的才華就這樣被淹沒。但是,這也算是“幸事”,讓李先生可以在寂寥之中安于藝術創作,讓其藝術形式和內容更加純粹。
近代中國油畫藝術作為先進文化被傳入,它承載著先行者們的理想。如果我們不過分糾結中西藝術,不將“現代”與“傳統”對立,那么,在社會進入現代化進程后,我們國家確實需要外部的藝術文化來“刺激”,以此跟上時代的發展步伐。傳統美術缺少活力,急需一場“美術革命”來打破傳統,讓傳統美術順應時代的發展。要用西方嚴謹寫實的態度來改變人文畫造型,它不僅僅是“工具性”,最主要的是包含價值取向,積極向上、開放的文化態度,在文化交往中運用新概念進行思維刺激,從而通過時空進行知識遷移,然后再介入社會生活和意識形態等多個方面。在當今看來,那個時期的“美術革命”雖然有“科學主義”改造藝術的嫌疑,但是不得不承認,在當時確實是推動了文化的進步。
西方油畫藝術在中國傳播近百余年,李文珍先生的油畫意識在近代中國油畫發展歷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李文珍先生的油畫作品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望文生義的“寫意”油畫,它是藝術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繼承關系,李文珍先生保持了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獨立性,他沒有將藝術作為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同時,也沒有錯誤的展現出“表現主義”的形式和內容,它的藝術來源于“轉譯”的歐洲現代主義,有著同樣深厚的傳統,這種“轉譯”時的“有意誤讀”使之繼續延續下去。
中國油畫的發展是很多美術教育家共同努力的結晶,因此,中國油畫在此基礎上傳承和發展。首先,中國油畫會繼續蓬勃發展。雖然國人對油畫的理解和認識還比較淺薄,部分人會認為油畫為了能夠讓更多人接受和理解它,應該在藝術形式上進行創新,他們用北里傳統的方式去創新,這是錯誤的想法。中國油畫創新需要在文化傳承的基礎上進行,要在傳統文化上開辟新途徑,從而發展油畫藝術,正如李文珍先生對西方油畫的理解和創作,要秉承務實的精神,在積累的基礎上進行創作。
藝術文化的發展是否能夠傳統下去,要看它是否具有價值,經過百余年的發展,油畫在中國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中國社會的經濟水平在不斷地提高,人們對藝術的追求也在不斷地提升,這對于油畫市場和油畫技藝都產生了推動作用。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油畫藝術得到空前發展,經過一代代藝術家的努力,積累了豐富的藝術資源,從如今的創作和多樣風格來看,如今的油畫已經成為當之無愧的時代代表。
雖然油畫在中國得到良好的發展,但是發展道路還很長,尤其是進入了21世紀,中國油畫隊伍在不斷擴大,各種流派相繼登場,好的作品層出不窮,給中國油畫的發展增添了動力。與西方油畫對比,中國油畫在創作,尤其是在寫實油畫的技法上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是,新一代油畫作家在不斷的努力,在傳統油畫的基礎上,吸取了西方油畫的精粹,在此基礎上創作了帶有濃厚中國特色的、時代精神以及民族文化特色的油畫作品,并且充分展示了藝術家的個人風格和特色,這就是中國油畫在共性中尋求個性的發展道。李文珍先生對中國油畫的發展具有非常大的貢獻,因此,我們要傳承和發展李文珍先生對西方油畫的理解和創作,將具有特色的中國油畫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