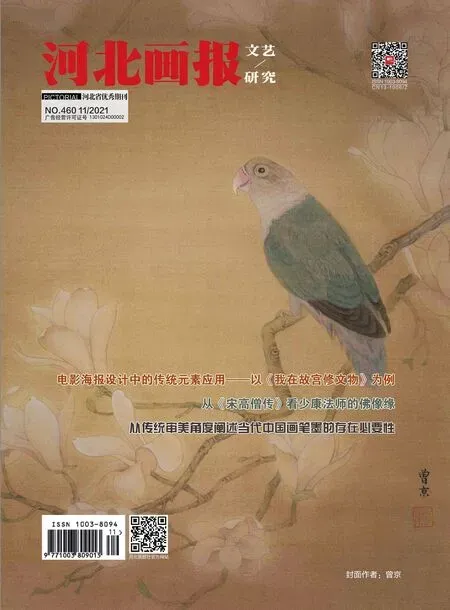從傳統審美角度闡述當代中國畫筆墨的存在必要性
霍書源
(作者單位:天津美術學院)
在中國畫寫意人物創作中,對當代水墨人物畫創作該如何保持傳統筆墨的精髓是我一直以來關心的問題,也是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問題。本文通過自己的一些粗淺理解,從傳統審美角度探索這一問題,在中國畫本質和中國畫的內在文化精神的基礎上談談如何保持筆墨的獨特性、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中國傳統繪畫的特點
縱觀歷史,中國繪畫是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成長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歷經數千年的漫長歷史,形成了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具備鮮明的民族特征,并被歷代畫家發揚光大。中國畫是中華民族悠久而又博大精深的歷史體現,也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氣質的象征,它以獨特的審美格調和藝術特色屹立于世界藝術之林,在數千年的發展中,中國畫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理論體系和筆墨程式,這種體系與中國哲學思想緊密相關,或者說中國畫不是簡單的畫種,而是中國文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中國繪畫藝術從一開始就不單純拘泥于繪畫對象的外表形似,而更強調神似。所謂“畫意不畫形”,形似只有外表的逼真,神似才能表現內在的本質精神。這也是中國畫最本質的特征,畫面中的物體不是真實存在的物體,只是借助大自然,借助景象來描繪畫家心中的想法,不受光影和空間的限制,只是參考對象,畫出的是作者本人的向往。清代畫論家笪重光說過,“妙在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景”虛實相生就像中國太極思想,陰柔并用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互生互動。黃賓虹的繪畫是表達中國古代易經思想道學理念最成功最集中最典型的杰作。筆墨的存在,讓中國畫有了獨特的審美效果,這種效果表面上是一種畫面呈現的視覺效果,實際上則是承載了中華民族深刻的民族精神。中國畫不應該命名為“水墨畫”,“水墨”的含義是為了與油畫,版畫,水分,水彩的命名方式趨近,同樣使用媒介來命名。讓人們更容易理解接受這一畫種,但究其根本,這種東西不是真實存在的物體。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的畫面構成,可以理解為一種表現語言,亦可稱為一種精神內涵。筆墨的形成,讓中國畫有了血肉,從古至今每一幅佳作,都透露著作者用筆墨情懷來向觀眾訴說著某種情緒。從吳道子的淡彩吳裝,李公麟的白描,到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戲,直到齊白石的紅花墨葉,通過呈現墨色的濃淡干濕微妙變化,用筆和墨的巧妙結合,相互映發來詮釋他們對畫面的感受,這些因素是中國畫的基本特點。中國傳統審美特征也是變化和發展的,所以中國畫也是變化和發展的,只是這種變化和發展并不如想象中那樣“觀念更新”,一下就來一個觀念的大更新。中國畫沒必要做改觀。中國的文化發展不像西方那樣要革命,要推翻上一個時代的全部,而是重視自然的傳承,不否定過去人留下的精華,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豐富和提煉,在文化上保留,在形式上改進。
二、筆墨的延續
眾所周知,幾千年來中國畫家一直在延續老祖宗的獨特的筆墨程式,如果現在就要一下拋棄是不可能的,必須找一個契合點,能夠恰當地將兩者融合,產生一個更有魅力的新的繪畫面貌。中國畫要想在世界藝術中有話語權,創作者就必須對上述狀況有一個認真的反思和審視,要隨時保持中國畫的獨特性,不可替代性,我們現在還沒有完成中國畫本該有的歷史使命,我想我們要保護它改進它,讓自己老祖宗的文化永遠流傳下去,遵循那些基本規則,但也不能死心眼,把外來的好的元素融合進去,讓它更完整更有內容。要知道筆墨是為了變現什么如同律詩的格律是一定的,只要是律詩都必須遵守,不能出一格。但詩與詩的內容不同,每一首都不可能相同,唐詩宋詞元詩各有特色,詩是發展變化的,如同畫也一樣。傳統的筆墨必須表現新的時代精神,才能產生更好的作品歷代優秀的作品都是如此。“筆墨當隨古代”其實是當隨傳統,但是是古代的傳統,而非現在的新傳統,筆墨如果一直都跟隨古代,那豈不是一成不變,千載一法了,中國畫藝術的生命不就終結了嗎?所以必須知道筆墨表現什么,知道了筆墨的目的就不會一直一樣。在西方藝術審美中,強調畫派之間的對抗,變革,面貌講求煥然一新,中國畫的復雜就在于把不同時代不同畫派的不同相互貫通,猶如將陰柔與陽剛糅合處之強調雙方的中和,沒有縫隙,沒有邊際,雖然在調和過程中或有偏勝但更主張由偏勝而入大勝,正因此,我們才能解釋中國藝術審美中“大巧若拙”,“大樸不雕”,“返璞歸真”等主張才能解釋中國畫為什么不圖真不圖像。縱觀中國美術史,會發現每一個朝代都在繼承以前時代的傳統,“傳統”這個詞幾乎被人談爛了,一說起來傳統感覺是假大空,是一個中國畫家經常掛在嘴邊的自言自語,但是仔細想想,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傳統遵循傳統,而又從傳統中走出來,做到了創新。為什么傳統這么重要?仿佛中國畫的發展是逆向發展,不是說越來越不好,而是每一位相對的后人都在努力繼承前人的成果,如果沒有董源巨然,就沒有后來的四王,他們的山水畫風格的形成,是某種程度的巔峰。在學習前人時,雖然與這些大師們沒有直接的師承關系,但他們的藝術讓我感受到了一種血緣般的親和力,我無意沾染大師們的光彩,可我無法回避他們在民族藝術土壤里的真情耕耘和早已播下我們今天藝術探索的種子。其次就說道師承,然后一幅畫如果想站得住腳,其中必然有傳統的脈絡可循,上文中提到,中國畫的發展注重傳承發展,一個新的面貌的出現,背后一定是有張舊面貌在支撐著他,也就是師法于哪里,不能憑空創造,唯有充分體現中國畫的深度和特色,才能找回民族藝術的精神,不論時代在如何發展,中國畫是存在于一個自己的時空軌跡中,不被外界所制約影響,生來是華夏身,身上流的血就不會變,這是骨子里的一種民族特性,凡是民族主義的東西一定含有復古主義的思想在里面。時代在發展,變化的是我們周遭的環境,是外在的現象,可是不變的是我們的民族信仰。中國畫不會因為時代的改變而從內在發生變化。現代人可能受很多世俗的影響,想法不再那么單純,伴隨著這個世俗的社會,作品也自然流露出來,所以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如何讓我們手中的中國畫出淤泥而不染,不被世俗所沾染,保持它的那份純潔,是我們每一個人應該思考的問題。
三、傳統與前衛
當今時代,中國畫將會如何發展是一個問題,歷史證明任何一種藝術的發展都是靠承與變得巧妙運作,不能總是把繼承當成模仿古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知古意的本意,也不知辯證以求進,結果就會反其道而行,變得華而不實,或繁而無章,或枯而無神,停留在臨摹和仿制,不能與當今社會所同步。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隨時存在著。當我們在創作作品時,除了考慮創新思維,畫面效果之外,必須在創作過程中無時無刻不提醒自己所完成的是一幅中國畫創作,每一處的處理都要體現筆墨的精髓,首先畫面氣息要保證是有筆墨涵養的,有深度的,有文化支撐的,而非一些簡單的用色平染,水彩式的表現手法,抑或是過于西化的表現手段。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畫,假設要用水墨去畫一位模特,結果必定與油畫不同,這其中的區別不在于表面的材料不同,而是要深刻體現毛筆宣紙之間的微妙關系,那種關系是任何其他材料不可替代的,也就是筆墨的獨特性要充分發揮。我認為中國畫的創作要緊緊圍繞筆墨構成,濃淡干濕,把握節奏韻律,用筆墨的特有美感與呈現中華文化的獨有審美理念,這也可能是中國畫的根本存在價值,才能時刻保持筆墨的獨立性和單純性。從自身角度看,我通過大量學習傳統和比對中西繪畫,古人的作品也罷,前時代的老先生也罷,或是當代的成功畫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始終在探尋中國畫的筆墨,探尋中國畫的精神,筆墨是種方式,但可能更是一種精神支撐,如果一幅中國畫沒有了筆墨,可能也就猶如假花假草一般沒有了生命,沒有了跳動的脈搏,沒有了畫家躍然紙上的激情。在學習前人時,雖然與這些大師們沒有直接的師承關系,但他們的藝術讓我感受到了一種血緣般的親和力,我無意沾染大師們的光彩,可我無法回避他們在民族藝術土壤里的真情耕耘和早已播下我們今天藝術探索的種子。古人的生活與現代人的生活必定不一樣,變化的是我們周遭的環境,是外在的現象,可是不變的是我們的民族信仰。中國畫不會因為時代的改變而從內在發生變化。現代人可能受很多世俗的影響,想法不再那么單純,伴隨著這個世俗的社會,作品也自然流露出來,所以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如何讓我們手中的中國畫出淤泥而不染,不被世俗所沾染,保持它的那份純潔,是我們每一個人應該思考的問題。從1960到1970年代初這段時間,中國出現了一批用西畫技法創作歌頌社會主義的作品,可能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寫實畫”比較恰當,那時的畫家開始把西方的素描光影融合到中國畫之中,這種變革可能是以前前所未有的,但是這種變革似乎又顯得很為合理,可能與時代背景的關系吧,但是我想不應該對此有成見,中國畫的發展走到這一步可能是必然,由于政治,教育,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影響,我們看到的東西愈來愈多,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豐富,所見也越多,科技的發展,人類的發展都在不斷刷新改變著我們的觀念,如何把現代產物用中國畫的形式表現出來是一個普遍問題。
傳統中國畫的題材多局限于山水、花鳥、界畫和古典人物,中國畫要融入時代的主流,至少在主題上要與現在的世情所吻合,不能遠離人群,可能中國畫無法像其他畫種廣納題材,但是筆墨的特色和獨立性永遠存在,只要不丟失筆墨,中國畫就永遠吸引著眼球,觸動著觀者。由于我是人物畫專業,在此就特以人物為中心來論述。外貌上,從長袍大褂變成了西裝革履,T恤牛仔褲,還有各類紛繁新奇的穿衣風格,面對這些于古代繪畫截然不同的對象,還能否在不丟掉傳統的情況下表現呢?我想著裝變了,但是繪畫思想不能變,盡管不能用古人的描寫形式來勾出長長的大袖袍,但是筆墨的多樣的化卻可以由我們盡情開發,不同材質不同款式,可以用不同的筆墨語言來塑造,卻不能顯得四不像,只是拿著毛筆用著墨,卻好像不是中國畫的口味。當代人物畫創作在畫面對象的表現上要有新意,一看就是“我們身邊的人”,要與同時代的觀眾有共鳴,表現手法上,在保持傳統筆墨的基礎上,可以吸收借鑒壁畫元素,甚至是西方的不同畫派特色。民間藝人與畫家的最大區別,就在于一個優秀的畫家最主要體現在精神層面上,體現在創造性上,而創造性則來自于對現存秩序的挑戰和反抗,這樣的老生常談衡量出了事物的質的區別。作為一個畫家,在精神層面上的追求一刻也不能停,那么在畫面中如何做到精神的體現,答案顯而易見,就是充分體現筆墨的活力,每一個人所表現出來的筆墨方式都不一樣,筆墨好像成了每一位畫者的情緒流露,這與好壞沒關系,筆墨好像會說話,畫家每一刻的喜怒哀樂都會通過筆墨表現在紙上。如果沒有筆墨,沒有情緒,就像圓珠筆在紙上死死劃過的痕跡,那么這張畫也毫無生命力可言。許多的中國畫看上去就是表面運用中國畫材料,只不過是作畫工具和材質的不同罷了,也許正是這種原因才把它劃為中國畫這一評審范圍的。用中國傳統的毛筆、墨、顏料在宣紙上繪制具有西方審美特點的作品是當代中國畫畫壇的一種普遍現象。可以說有不少國畫家試圖以這種方法強調自己的“創新精神”,以求與眾不同,標新立異。但是這種簡單粗暴,沒有思考的生搬硬套,可以說是對中國畫的踐踏和不尊重。缺乏中國畫本質筆墨的表現語言,脫離傳統,脫離民族審美,又怎么能使中國畫發展。新的當代水墨畫,要使得畫家和觀眾的審美意識和審美理想都有可能在多樣式的審美角度中得到體現和滿足,比如一種技法或表現形式讓觀眾得到了視覺享受,會感到是“極具傳統元素的新式中國畫”。傳統中國畫的畫面呈現樣式不再是唯一的、老舊的中國美術樣式,而只能是中國美術多樣式中的一種。現代中國畫的全新構成方式,也是中國傳統繪畫必然變革的必然結果。現在社會對當代水墨人物畫的爭論從未停止,每一位畫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對于傳統和外來都各自持有不同的觀點,每一個人的生活經歷不同,所處環境不同,所接受的教育不同都會造成繪畫面貌的繁雜,在這種生生不息,千變萬化的時間潮流之中,作為一個中國畫畫家,要時刻冷靜,時刻自省,不丟傳統,跟隨時代,才能無愧于心,創作出打動心靈并且合理存在于中國美術史的作品。
四、結語
從中國傳統的美學角度出發,我們會發現中國畫藝術的獨特鮮明的特點,作為一名中國畫家,我們要清醒認識到這一點,應該擁有更豐實的基礎可以深耕這塊文化田地,例如對傳統的理解與運用,對文化思想的熟悉與融入等等。在未來漫漫藝途中,一定要從中國畫思想層面切入,深入探討中國畫構成因素之間的相互牽引,思考是什么在如何影響中國畫發展,并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