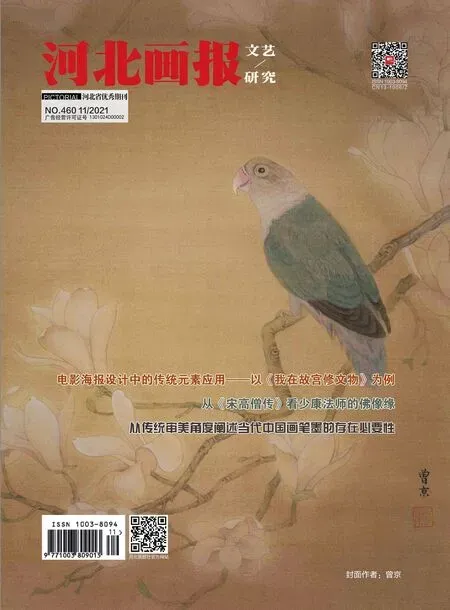基于IP視角下的婺劇藝術開發與傳承
董渤
(作者單位:浙江橫店影視職業學院)
婺劇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地方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單位,其藝術價值和人文資源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現代藝術和新的媒介環境下,正面臨巨大的競爭力和生存壓力。從婺劇的IP改編出發,一方面確立了對婺劇經典劇目的IP保護,另一方面是借力IP產業鏈思維,對婺劇這一傳統文化資源的開發。在婺劇走向市場、失去計劃經濟的暖房保護后,對婺劇的他類藝術形式的改編和創作,是傳統婺劇扎根現代市場的一劑良藥。最后,婺劇作為地方文化的重要內容,直接關涉地域文化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高度重視文化建設與市場經濟的內在關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實施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等一系列戰略舉措。婺劇的IP產業鏈構建、他類藝術作品創作是地方傳統文化資源開發、保護和傳承的重要舉措。
一、婺劇特性的宏觀考量
婺劇是金(金華)衢(衢州)一帶的地方性戲種,集合了高腔、昆腔、亂彈、徽戲、攤簧、時調六大聲腔,是周邊地區多種戲曲相互交匯、糅合的年輕劇種,發展歷程可以追溯到四百年前。區域性的文化空間和同一的認同感給婺劇打上了地方劇種的烙印,而流淌在婺劇血液里的基因是傳統戲種,諸如徽戲、昆曲等戲種的歷史積淀和本土文化的雜糅。
(一)地域魅力的薪火相傳
婺劇以金華官話為主要唱腔和道白,源起于明末清初,其發展承合我國戲曲花雅爭勝的歷史脈絡,有深厚文化積淀與歷史傳承,也帶有強烈的地方意識和區域化認同感。金華官話是融合了北方語系和本地方言的“地方通用語”,拓寬了婺劇的流布區域,不再局限于金衢一帶,還覆蓋到徽、贛、閩等區域,打破了吳語、徽語的方言片區阻礙。另一方面,金衢一帶及周邊地區獨特的歷史文化,是根植于婺劇藝術的基因和底色,成為他區別于其他劇種的根本特征。
(二)集大成的多聲腔劇種
婺劇是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多聲腔劇種,包括高腔、昆腔、亂彈、徽戲、攤簧、時調六種聲腔。六大聲腔均來自金衢一帶,各自獨立發展和演繹,同時又統一于婺劇,在長久的合班演出、相互融合過程中,程式化表演趨于統一,最終形成了婺劇本體多元一體的復雜格局。民間戲謔“候陽班的嗓子、昆腔班的步子、亂彈班的笛子、徽班的架子、攤簧班的娘子、時調班的婊子”,雖說表意粗糙,但從一定程度上形象概括了六大聲腔的特色。在六大聲腔中,高腔、亂彈粗獷肆意,是迎合鄉野庶民的“俗文化”,常見于鄉下廟會的婺劇表演;而昆腔則帶有以昆曲為代表的“雅部”基因,是服務于文人雅士的“雅文化”,這種相互沖擊、二元對立的多元性格為婺劇的發展平添了旺盛的自生力。田漢對婺劇給予了較高的認可,“金華戲傳統深厚,不是小傳統,而是大傳統”。 一方面,從婺劇發展的歷史淵源重拾了婺劇的地方戲地位,另一方面也精準凝結了婺劇的特點。
二、婺劇藝術資源開發的幾個抓手
婺劇藝術價值是淵源的中華傳統戲曲藝術的繼承和出新,是在穩固的金衢地方文化生態中發展流變的,跟隨著地方人民的意志而律動,在復雜多變的內外環境下動態的變遷。因而婺劇藝術資源的開發要看準“變量”與“恒量”,抓住“恒量”作為婺劇藝術價值開發的抓手。
(一)傳統積淀的血液流淌
婺劇是婺文化的沃土生長起來的地方性戲種,多聲腔唱法、儺戲的融入都是對其“小傳統”的體現。而地方劇種的生成與傳統戲曲的流變是分不開的,這就是婺劇的“大傳統”。所謂的“大傳統”就是婺劇流淌著的傳統文化精神、審美與內涵,這是所有傳統戲曲傳承與發展的“恒量”,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婺劇延承了傳統文藝作品對中華傳統倫理道德、處世哲學的精髓,并且對其進行了地方化演繹、改編,帶有本土化的解讀。比如《僧尼會》被多個地方戲種演繹,在婺劇的創作中提煉了反對封建神權和逃脫世俗藩籬、自由追逐愛情的主題,在程式化的表演上融合了多劇種藝術,呈現出一個活潑乖巧、古靈精怪的小和尚形象,以婺劇表演藝術家吳光煜的個性化演繹為代表。另一方面,婺劇是對綿延數千年的宗法制度的非典型表現。宗法制形成了嚴苛的社會等級和人際倫理,社會以家族為單位,宗族森嚴、尊卑有序。
(二)經典劇目的文化根底
婺劇的構成包括劇目劇情、唱腔、表演程式、服化道(行頭、臉譜、道具)、班社劇團等,其中劇目劇情首當其沖是婺劇的主要物質構成。婺劇劇目海海,共有一千零三十六個大小劇目,穿針引線、引經據典,是民間傳說、歷史經典、重大史事的民間演繹,蘊藏著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呈現出來,具有普遍的德育功能和教化意義。劇目劇情包羅萬象,上至上古神話、下至傳奇文學,比如高腔《耕歷山》就是舜耕歷山的上古傳說。徽戲《海瑞算糧》是明代海瑞擔任縣令時的故事。還有眾多出自民間文學傳奇的戲本,比如徽戲《過江殺相》描繪的是《水滸傳》中梁山泊英雄好漢被逼上梁山,與賊臣對抗的故事。婺劇在網羅劇目數量之繁之外,還保留了南戲傳統劇目的原生態,具有文獻價值。比如傳統徽戲在進京獻戲等擴大傳播過程中,劇目劇情發生了一定的改編,而在婺劇中的徽戲則更為原汁原味,比如《白兔記》《黃金印》等。
(三)民俗化演繹的熱烈奔放
婺劇是在金衢一帶及周邊地區生長起來的草莽戲曲,其“小傳統”的外在形式體現在藝術發展的民俗化。其一,婺劇演出不僅承載娛樂、教化職能,還與民間祭祀、民俗節慶牢靠地結合在一起。金華地區的迎神、祭祀、廟會等民俗節慶活動中,婺劇會加演類似于巫術表演形式的“踏八仙”,以《文武八仙》為例,來自儒、釋、道的不同宗教和時代的神仙同臺演繹,包括魁星、關公、孫悟空等,最后都以“三跳”為結束,而“三跳”正是中國古老儺戲的活化石。其二,“斗臺”的競演模式是傳統戲曲展演形式的革新。金華地區在五侯三佛的廟會舉行盛大的迎神活動,在迎神的過程中基本每個神廟前都有戲班演出,各個戲班爭相斗艷、使盡渾身解數招徠觀眾,哪家社臺的觀眾最多就能奪冠,此所謂“斗臺”。斗臺展演極富挑戰性和趣味性,開辟了廣闊的創作空間,班社為了招徠觀眾,引入了民間武術和雜技表演,“文戲武演,武戲文演”,甚至會即興邀請現場觀眾上臺表演。其三,婺劇凝聚了民間智慧。婺劇班社劇團的民間力量雄厚,業余農民愛好者組建的坐唱班、太子班、農村劇團是婺劇發展的重要力量。金衢一帶的地方音樂、舞蹈和傳統鄉村生活中的理想精神、處世哲學等也在新劇創作中得以凝練和融入,比如灘簧《僧尼會》、時調《小二過年》等都是婺劇文化影響下的民間智慧結晶。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存檔
婺劇榮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對業內人士來說是喜憂參半。可喜的是入選非遺能夠從制度、資源等層面提升婺劇保護與傳承的力度;可憂的是,不少人對非遺保護就是原生態歷史封存的偏激認知,認為婺劇被認定為非遺就是官方層面上的“活化石”,難以再進行產業化和市場化開發,婺劇的現代化進程會舉步維艱。辯證的看待問題,在非遺背景下探討婺劇的藝術資源保護與傳承,有定論也有問題。婺劇是在八婺地區特殊的文化生態下生長起來的民間藝術,金衢一帶民間的審美認知、婺劇的開放式表演形式、婺劇表演劇團的復雜構成等決定了婺劇不是一成不變的“活化石”,也沒有瀕臨滅絕,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市場基礎,并且戲劇界有“唱腔三十年一變”的說法,這是非遺背景下婺劇保護的定論。“文化傳統及其表征是婺劇展演所具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性格的核心內容” 。既然婺劇不可能是原生態的“活化石”,是在民間文化沃土上生長的藝術,那么如何在非遺范式下對婺劇進行有序保護和可持續性發展是問題所在。非遺語境下的婺劇保護與傳承不局限于婺劇的物質性構成的檔案式封存,更重要的在于對婺劇所呈現的文化遺產精神、品格、傳統積淀的再發展。
三、婺劇的IP產業鏈開發策略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是傳統知識產權在新的媒介環境的新概念,是媒介融合、產業融合的產物。強調的是知識產權(版權)跨媒介、跨領域、跨產業的衍生開發,最終達到IP一體化、也就是全IP產業鏈開發的運營模式。其中,IP產業鏈的上游是IP價值的源頭,是IP衍生開發的內核、依據,自身生命力強勁但變現能力弱,主要呈現形式為文學作品(傳統文學、網絡文學)、漫畫、音樂作品等。IP產業鏈的中游是IP原生產品的衍生體,也有一些IP直接以中流的形式出現,再衍生上游、下游產品,完整產業鏈條。常規意義上的中游呈現形式有電影、電視節目、戲劇(舞臺劇、實景演出等)、游戲等。中游在變現方面是IP產業鏈的中流砥柱,同時在產品力方面兼具了藝術性與商業性。下游距離IP源頭最遠,主要是帶有IP主題、元素、標簽的文娛衍生產品,包括主題樂園、娛樂項目、周邊文創商品等,比如迪士尼樂園和迪士尼貼標產品都屬于迪士尼IP產業鏈的下游產業。
傳統戲曲的IP資源開發由來已久,并已結出碩果。由傳統戲曲改編的影視作品在熒幕上大放異彩,地方戲曲的衍生產品戲曲服飾、玩具等暢銷不衰。在理論建設方面,第二屆中國(金華)李漁戲劇匯“戲曲與IP”高峰論壇肯定了傳統戲曲蘊含的豐渥IP資源,討論了地方戲曲IP打造的路徑與方向、地方戲曲文化生態圈與城市發展的關系、傳統戲曲與互聯網的融合發展、戲曲文創產品的創新與開發等重要內容 。而婺劇的IP產業鏈開發尚處于理論階段,要面對復雜的實踐邏輯和新舊審美認知反差的挑戰,道阻且長,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嘗試。
婺劇劇目浩繁,大小劇目達一千余種,其中既有積淀厚重的傳統大戲,也有帶有本土烙印的民創小戲,比如時調《小二過年》、灘簧《僧尼會》,還有金華戲曲理論大家李漁的《風箏誤》《奈何天》。林立的劇目都是IP改編的寶貴資源,可以衍生為影視作品、舞臺劇、實景演出等。比如傳統昆曲《牡丹亭》被改編為實景園林版的室外戲劇,課植園的實景園林+現代舞美技術讓觀眾變身戲中人,沉浸在山水之間,又保留了傳統昆曲的戲曲藝術內核。傳統戲曲《白蛇傳》被多次改編為電影、電視劇、動畫片甚至游戲,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超級IP。改編而來的粵劇電影《白蛇傳·情》以4K全景聲、CG視覺特效等技術塑造了中國寫意美學的視覺奇觀,原版粵劇的唱詞和唱腔也做了現代化修改,唱詞刪繁就簡凸顯敘事性,唱腔保留了經典唱段的同時融入了流行唱法,還加入了西洋管弦樂,在保留粵劇原滋味的同時兼顧了年輕觀眾的審美。取得了叫好又叫座的優越成績,一反傳統戲曲電影的頹勢。郭小男導演的江南民調新版《三笑》以越劇、評彈、無錫民歌等江南民調為基調,融入了歌劇、搖滾、RAP等多元表演方式,在文本上舍棄了“唐伯虎點秋香”的老套故事,解構為藝術家追求靈感、本真、自我和愛情的故事,這種對傳統曲目的大膽改編是迎合現代審美的年輕表達,是傳統戲曲IP的舞臺劇改編的勇敢嘗試。
四、結語
以婺劇的保護和傳承為目的、以IP產業鏈構建為手段,探討婺劇資源開發與傳統文化保護的方法路徑,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第一,在現代化和新媒體的雙重變奏下,婺劇面臨歷史發展的拐點,IP視角下的婺劇藝術資源開發有利于婺劇契合現代社會的審美趨勢和文化需求的“現代生存”;第二,在非遺文化保護、地域文化建設和文化旅游開發等多重意識倡導下,如何在保持婺劇藝術“原生態”個性的同時,積極拓展婺劇傳承發展的文化空間與現實路徑,成為實現婺劇傳承與發展的必然要求;第三,地方戲曲在經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短暫繁榮和申遺的政策性保護后陷入了發展低谷,藝術創作和市場呼喚亟待甘霖沐浴。將婺劇經典劇目作為他類文藝作品創作的母體,能夠延伸婺劇的市場占有量和藝術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