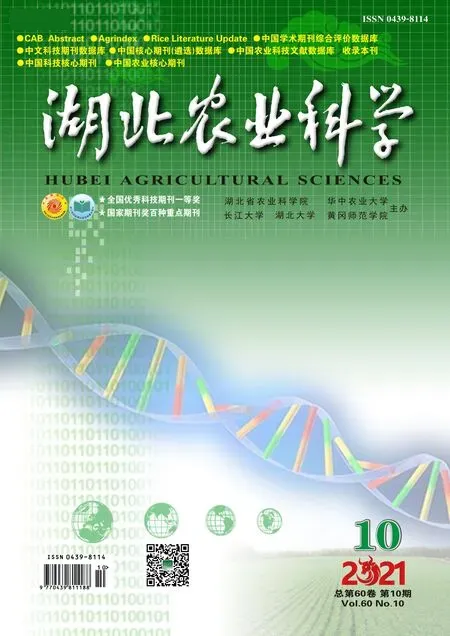國家公園體制下的自然保護地整合優化探討
——以三門峽市為例
石伊博,郭 悅,劉 暢,劉藝平,孔德政
(河南農業大學林學院,鄭州 450002)
自然保護地是指由國家依法劃定的陸域或海域區域,有保護價值的自然生態系統、自然景觀、自然遺跡以及其所承載的文化、歷史等。2019年6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標志著中國自然保護地體系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各地展開對自然保護地的勘界、調查、制訂總體布局和發展規劃等任務,并在2020年完成國家公園試點工作,設立一批國家公園。在中國自然保護地發展過程中,會出現一些保護不到位、不合理的情況,因此需要對自然保護地進行合理優化,以提高中國總體生態環境,加快生態文明建設。
1 研究背景
1.1 國家公園的起源
國家公園是指國家為保護具有典型特征的生態系統,同時為科學研究、生態教育和生態旅游提供場所而劃定的需要特定保護、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區域。這一概念起源于美國,成熟于美國。1870年的懷俄明州,一個19人的探險隊到達黃石荒野地帶開展探險,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在一大批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1872年3月頒布法令劃定一塊面積約8 100 km2的自然保護地,將其命名為黃石國家公園[1],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由此誕生。
1.2 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的重要性
中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建立于1956年,名為鼎湖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發展至今逐漸形成了以自然保護區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但在發展過程中也逐漸出現一些問題,致使自然保護地無法得到更為有效的保護。此類問題的出現背離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自然保護地生態效益的發展,中國也開始出臺相應措施對自然環境加以保護,截至目前中國共設立10個國家公園作為試點。
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并不是削弱自然保護區的地位和價值,國家公園范圍的劃定是在現有自然保護地的基礎上,以加強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完整性為基礎進行綜合評估,從本質上看是對自然保護地的強化。對個人來講,國家公園體制是國家所有、全民共享、百姓受益的,大力推進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十分必要。
1.3 中國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演變
自成立第一個自然保護地至今,中國的自然保護地數量已達約2.1萬處,自然保護地的種類已達10多類,其中國家級自然保護地的總數達約4 100處,陸域自然保護地的面積總和占中國陸地面積的18%以上[3]。在中國自然保護地發展的60余年里,逐漸形成了以自然保護區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自然保護地的種類也在不斷增加,有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海洋特別保護區、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地質公園、森林公園、濕地公園、海洋公園、沙漠公園、原生境保護點等10余種類型[4]。在此之前,由于中國的自然資源歸不同的部門管理,不僅會出現自然保護地區域劃分上的交叉重疊,而且也可能出現管理方面的沖突。國家公園體制的提出標志著中國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從以自然保護區為主體向以國家公園為主體轉變,這一系列改革措施再次表明了要消除自然保護地體系長期出現的各種沉疴頑疾的態度和決心,從而為生態文明建設打下堅實基礎。
2 中國現行自然保護地體系存在的問題
2.1 交叉重疊,多頭管理
在中國自然保護地發展的60余年里,自然保護地種類逐漸豐富,這對中國生態環境保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比國外,中國自然保護地的建立制度尚不成熟,部分區域未經過全面系統的規劃[5],在自然保護地的設立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在保護地空間區域規劃上的重疊,導致部門管理沖突和監管困難等問題頻發。本研究在對河南省三門峽市自然保護地的調查過程中發現,三門峽市涉及交叉重疊等問題的自然保護地較多且分布較零散,總面積約26 024.41 hm2,占原自然保護地總面積的17.20%。例如河南澠池韶山省級地質公園與韶山森林公園重疊,且重疊面積達548.78 hm2;同時這一地質公園又與河南黃河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重疊,重疊面積達724.60 hm2,僅一個自然保護地就可能與2個甚至3個其他類型的自然保護地在空間布局上重疊,此種情況在其他省份也屢有出現[6-9],能夠很明顯看出,無論是對省級自然保護地還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地來講,對自然保護地空間劃分的合理性亟待完善。
在此前中國對自然保護地的保護主要為各部門對其相關資源進行保護,同一自然保護地的管理職責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門,各部門又針對自身的保護職責制定相應的規范性文件,導致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和銜接,對產生的問題出現推諉扯皮的情況。與此同時,在對河南省三門峽市自然保護地進行資料收集時,由于當前自然保護地管理體系的問題,地方上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銜接,在技術溝通方面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這種多頭管理的情況難以形成合力,全面管理相對較為困難,這樣就會形成各部門之間利益沖突、職責模糊的情況,阻礙中國自然保護地的發展。
2.2 邊界不清,資料不全
雖然中國自然保護地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因早期的基礎經驗薄弱、管理不嚴格、操作不規范等問題,導致現有的自然保護地仍然沒有明確的邊界。在對河南省一些自然保護地的調查中,自然保護地批復面積與實際管轄面積不符合的情況較為常見,例如河南黃河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三門峽段)批復面積為6.8萬hm2,實際管轄面積為2.4萬hm2,此種原因的出現主要是由于后期各部門對自然保護地管理勘界時所用評定標準不同。對自然保護地的申報都是自下而上的,各部門相互之間缺乏有效的銜接與聯系,導致此類問題出現,這也強調了頂層設計的重要性。
在對自然保護地基礎資料收集的過程中,因自然保護地設立時間久遠、期間部門工作人員頻繁調動等,因此出現了相關基礎數據缺失、資料丟失等問題,例如三門峽市甘山森林公園設立于2000年,在資料收集時發現該區域內林場以及森林公園的邊界矢量圖均有部分缺失,僅能依據的是一張紙質地形圖上的邊界范圍,這就為后面對甘山森林公園進行整合優化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困難。
2.3 保護地碎片化、孤島化
導致自然保護地碎片化、孤島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點。第一,自然保護地逐漸受到商業化的影響;第二,相比發達國家,中國對自然保護地以及國家公園的意識形態較為落后,沒有形成科學、合理、統一的空間規劃體系;第三,自然保護地管理體系的不合理致使完整的生態系統被行政權限所分割。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在此過程中,中國自然保護地的開發和利用逐漸商業化起來,各地政府利用本地的自然資源優勢,大力開發旅游設施建設,旅游城市這一名詞也逐漸被人們所熟知。在城市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個別地區自然保護地的生態環境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使得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出現了偏頗,過于側重旅游區域的生態保護和修復而忽視非旅游區域的環境保護,因此在發展旅游產業時應對整個自然保護地的生態環境做到統籌兼顧[10]。一些地區對自然保護地的理解不夠深刻、透徹,僅對生態環境特別突出的區域加以保護,這種不夠科學的空間規劃也導致自然保護地的碎片化、孤島化。例如三門峽市澠池縣的自然保護地,該地區位于秦嶺余脈,地質資源較為豐富,由于空間劃分得不夠科學合理,其河南韶山省級地質公園被劃分為6個區域,生態系統完整性、連接性、原真性和協調性不夠,同時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的管理難度。
2.4 歷史遺留問題
在自然保護地形成的過程中,因規劃面積不規范[11]、部門之間管理職責不明確、產權不清晰等情況,致使自然保護地內存在大量基本農田、村鎮、開發區等歷史遺留問題,同時采礦活動也在自然保護地內進行。這些歷史遺留問題都給中國自然保護地的發展帶來了阻力,解決保護與發展之間的矛盾是目前面臨的實際問題。
3 自然保護地體系整合優化措施探討
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是一項意義重大的舉措,從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開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工作便緊鑼密鼓地展開,黨的十九大再次明確這一目標,這一系列的行動表明中國正加緊對自然保護地體系的重構。《指導意見》作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的頂層設計[12],在此基礎上對自然保護地的整合優化措施進行思考,以河南省部分自然保護地為例,探討自然保護地整合優化的實施路徑及其可行性。
3.1 自然保護地的歸并與整合
《指導意見》從最高層面解釋了對相鄰保護地歸并與整合的措施,但落實到地方還需要有相應的調整,使其更適合在本地實行。
歸并與整合建立在科學的自然價值評估基礎之上,相鄰的自然保護地要以生態角度為主,考慮是否可合并為一個自然保護地,再在合并后的基礎上進一步對自然保護地的范圍進行科學細致的劃分,打破行政界線的束縛,對同一生態類型的自然保護地做到應保盡保、應劃盡劃。因此,進一步研究自然保護地空缺區域與周邊森林公園之間的關系,將主要保護目標和保護對象一致、生態系統類型相似的區域補充并入自然保護地內,同時對邊界進行優化調整。在自然保護地范圍優化后,便需要以保護強度不降低、保護面積不減少、保護性質不改變和便于管理的原則,對自然保護地的功能分區進行科學合理的優化。
3.2 自然保護地內主要沖突調整規則
以河南省自然保護地的摸底調查為依據,并結合生態紅線、“綠盾行動”,自然保護地內的沖突主要可歸為六大類:永久基本農田、城鎮建成區、人工商品林、村鎮、開發區、礦業權,調整規則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永久基本農田:對成片分布且面積大于1 hm2以上的,可將其調整出自然保護地。原則上自然保護地內不能存在面積相對較大的永久基本農田,但在實際實施過程中,有些對自然保護地環境影響較小且調出過程相對困難的,可轉為一般農田不調出。
2)城鎮建成區:城鎮建成區內人口活動量大,對自然保護地內的生態環境有著不可控的影響。設置過渡期,并明確范圍和活動管控要求。
3)人工商品林:不牽扯河流源頭兩岸、水土流失嚴重區等區域以外均可考慮合理調出,同時對其他林木資源屬于個人或集體所有、成片分布、對生態功能不造成明顯影響的成片人工商品林宜調出。
4)村鎮:村鎮的調出實施路徑與城鎮建成區相似,適當結合農村移民搬遷的相關政策,科學合理地劃分調出區域。
5)開發區:對設立時間在自然保護地之后的開發區以及相關公共設施等,對生態環境影響程度較小且調整難度較大的,可留在自然保護地不調出,設立在自然保護地之前的可以調出。
6)礦業權:采礦權以及探礦權原則上都要退出自然保護地,但是具體實行起來涉及的經濟關系和法律關系較為復雜。在參考賀冰清等[13]對自然保護地內礦業權退出問題的探究后,可對開礦權設立在自然保護地之前的給予調出,設立在自然保護地之后的要逐步退出,且采礦證時間不允許延續。根據礦業權的合法性進行審核,科學評估后進行合理補償。對具有國家戰略性礦產資源的開采權允予保留,但不得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且生產規模不能擴大。
3.3 對接融入國土空間規劃
2019年5 月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中提到,將土地利用規劃、主體功能區規劃、城鄉規劃等空間規劃一同融合為國土空間規劃,科學布局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科學合理地劃定“三區三線”。從黨中央、國務院對生態文明建設與國土空間規劃的協同推進來看,國土空間規劃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自然保護地則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載體[14]。
在與生態紅線的對接上,目前要求為整合優化后的自然保護地全部納入生態紅線范圍內,再將生態紅線內的自然保護地劃分為“三區”,對自然保護地內的人為活動規范化、管控措施精細化。自然保護地的整合優化與生態紅線的劃定協同推進,同時以“國土三調”為依托,在工作過程中對問題解決方案、基礎數據獲取轉換等應進行更加緊密地聯系,積極探討協商,避免出現割裂情況。在整合優化自然保護地的“三區”規劃中,應妥善處理當地居民與核心區、一般控制區的對應關系問題,在科學合理的前提下適當地“開天窗”,對應退出的可逐步退出,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3.4 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
國家公園體制的建立標志著中國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步入法制化的新階段。目前,中國出臺的有關自然保護地的法規體系雖然十分充實,有關于森林公園、濕地保護區、地質公園、海洋以及沙漠等生態環境的相關法規,但是此類以生態要素為主體的多部門管理弊端在前文也已經提到,因此需要一個具有統領性的法規來對各自然保護地進行規范。
4 小結
自然保護地的整合優化工作是中國構建新時代自然保護地體系、加強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這是一項長期、龐大、系統的工作,從生態角度來看,自然保護地的整合優化是對各自然保護地生態環境進行更加全面的保護,并形成保護地生態鏈,使各自然保護地之間相關聯;從技術層面來看,自然保護地的整合優化為建設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提供了新的實施路徑和方法。自然保護地的整合優化是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的基礎,也是完善自然保護地生態系統的保障;國家公園體制為自然保護地的整合優化工作提供了現實意義,是整合優化成果的具體體現,二者互為依托,踐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理念。
自然保護地整合優化為今后國家公園范圍的劃定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創新自然保護地管理體制機制,同時完成各自然保護地的整合優化后,中國的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自然公園都將有良好的發展,此后設立新的國家公園時,擺脫了邊界不合理、管理不明確、職責不清晰、矛盾不解決等問題,方便了國家公園的設立。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最終目的是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為人類提供優質的自然資源,讓子孫后代也感受到大自然所給予的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