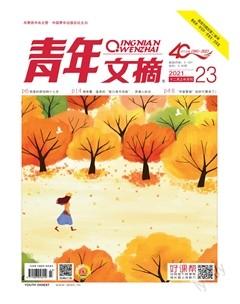孩子,不要對不起你奶奶
羅爾

2021 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本刊特開設《星辰大海,百年征途》專欄。
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讓我們回望那一個個艱難而又閃光的時刻,增添自信和力量,以信念為舵,以激情為帆,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一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這一年,李坤泰16 歲。她是大戶人家的小姐,家住宜賓白花鎮。李父早逝,大哥大嫂成了當家人。李坤泰想出外讀書,哥嫂不許,她就寫了一篇文章《被兄嫂剝奪求學權利的我》,文中說:“我自生長在這黑暗的家庭中,十數載以來,并沒見過絲毫的光亮……我極想挺身起來,實行解放,自去讀書。奈何家長哥哥專橫,不承認我們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讀書……請幫我設法,看我要如何才能脫離這地獄似的家庭,才達得到完全獨立?”李坤泰的大姐夫鄭佑之,是中國共產黨宜賓地方組織創始人之一。他偶然讀到李坤泰的文章,很是賞識,于是推薦發表在向警予主編的《婦女周報》上。
1926 年, 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形勢大好。
2 月,李坤泰在二姐李坤杰的幫助下,離家出走,憑一雙未裹過的大腳,疾走兩天兩夜,抵達宜賓,考上宜賓女中,改名李淑寧。在鄭佑之的介紹下,她加入中國共產黨。自從走出白花鎮,李淑寧就再也沒有回去過,且越走越遠。
10 月,李淑寧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成為黃埔軍校第六期213 名女學員之一,這是中國軍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學員。李淑寧又改了個更有力的名字——李一超。
1927 年, 北伐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之際,國共合作破裂;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的第一槍。
這年9 月, 李一超走得更遠,漂洋過海去蘇聯,入讀莫斯科中山大學。在前往蘇聯的海輪上,她嚴重暈船,吐得天昏地暗。同行者中有個叫陳達邦的湖南小伙,對她百般照應,讓她倍覺溫暖。到達莫斯科后,李一超和陳達邦的革命友誼上升為愛情,于1928 年4 月結婚。
1928 年,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革命形勢如火如荼。11 月,組織上需要李一超回國。此時,李一超已有身孕,本可以要求生完孩子再回國,但革命者的使命,永遠大于家事,李一超沒有猶豫,即刻啟程。陳達邦百般不忍,意欲與妻子一同回國,李一超拒絕了:大丈夫當以事業為重,豈可沉湎于兒女私情?陳達邦只好作罷,叮囑妻子,若一個人帶孩子有困難,就把孩子送到他堂兄陳岳云那兒去,又送給李一超一枚金戒指、一只懷表,揮淚作別。
這一別,夫妻倆再未見面。
二
1929 年,紅軍相繼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以此為中心,發展為中央革命根據地。
1 月,在宜昌地下交通站工作的李一超遭遇嚴重困難。她即將臨盆,還挺著大肚子,為傳遞情報東奔西走,且結交的人一個個神神秘秘,房東覺得她很可疑,就把她趕了出去。還有幾天就要過年了,孩子也快要出生了,李一超想起丈夫的話,想去找他的堂兄陳岳云。可宜昌地下交通站是她一手建立起來的,她一走,萬一組織上有事,聯系不上她,就可能造成重大損失。李一超不敢離開宜昌,只好在附近尋找新的房子,但沒有誰愿意讓一個來歷不明的女人把孩子生在自己家里,李一超一時找不到房子。
夜幕降臨,北風呼號,李一超徘徊街頭,瑟瑟發抖。她原租住房的隔壁,住著一對貧苦夫妻,他們不忍心看她流落街頭,便把她接到自己家里。
第二天,李一超的兒子提前來到人世。參加革命以來,李一超一直過著動蕩不安的生活,讓中國人民過上和平安寧的生活,是每一個革命者的理想,她便給兒子取名為寧兒。
但李一超注定不得安寧,還在月子里,男主人因打架被抓,李一超不能坐視不管,便拿出丈夫給自己的金戒指,幫女主人把男主人贖了出來。
不料,李一超的善舉讓警方對她起了疑心:這個神秘的外地女人,為什么會有金戒指?
李一超感覺不妙,抱著未滿月的寧兒,匆匆上了去上海的船。
此后的一年多,李一超一直在革命路上奔波,難得片刻安寧。
在上海,她遭遇過入室搶劫,劫匪把財物洗劫一空,連這對母子身上的衣服也不放過。在南昌,因為出了叛徒,300 多名革命者血濺刑場。當軍警從前門進來抓人時,李一超抱著寧兒,從后門逃離。她身上一分錢都沒有,只能賣掉丈夫給她的懷表,趕緊買船票回上海,向黨中央報告叛徒一事,以免造成更大的損失。在船上,李一超沒錢買吃的,母子倆靠好心的乘客給點饅頭分點粥,熬過了兩天兩夜的水路。
1930 年,毛澤東撰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初步確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革命路線。
革命之路道阻且長,李一超無所畏懼,但她怕兒子不能順利長大,也怕自己顧忌兒子而不能全心全意投入革命。于是,在即將接受更艱巨的任務前,她把兒子托付給了丈夫的堂兄陳岳云。
骨肉離別之際,李一超帶寧兒去拍了兩張合影,一張寄給丈夫陳達邦,照片背后寫著寧兒的生辰,一張寄給二姐李坤杰,給家里報個平安。
三
1950 年, 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講述革命英雄故事的電影《趙一曼》上映了。
趙一曼的故事感動全國,更震撼了一個叫陳掖賢的小伙子,他連看幾遍電影,潸然淚下。陳掖賢就是長大了的寧兒,他不知道,趙一曼就是他失蹤多年的媽媽李一超。
電影攝制者也不知道趙一曼就是李坤泰、李淑寧、李一超。當時的許多作家記者寫過趙一曼,但沒有人知道她來東北抗日之前,有過怎樣的經歷。
革命年代,許許多多的英雄,不知出處。
1953 年5 月, 李一超的二姐李坤杰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請求查找1930 年代在上海工作過的地下黨員李一超。周總理將此信批轉有關部門處理。
1955 年1 月2 日,李坤杰寫信給陳掖賢的姑媽陳琮英,告知:經過李一超的戰友和東北革命烈士紀念館確認,趙一曼就是陳達邦的妻子、寧兒的媽媽李一超。
得知自己的媽媽是英雄趙一曼,陳掖賢哭了。陳掖賢一直過得很清貧,但他從未領過國家發給烈士家屬的撫恤金,只去東北革命烈士紀念館抄了一份媽媽臨刑之前寫給自己的遺書。
寧兒:
母親對于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永遠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 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
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你的母親趙一曼于車中
1936 年8 月2 日
1982 年, 陳掖賢去世, 他給自己的孩子留下幾句話:“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過平民百姓的生活。自己的事自己辦,不要給國家添麻煩。記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則,就是對不起你奶奶。”
多年以后,一個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軍老兵,找到趙一曼的孫女陳紅,表示懺悔。日軍老兵想給陳紅一些錢,陳紅沒有要:“我爸爸連我奶奶的烈士撫恤金都沒要,我怎么能要你的錢?”
(摘自《女報》2021 年第5 期,知止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