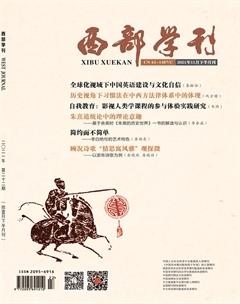荀子論“性”的多重含義及側(cè)重點
摘要:荀子言“人之性惡”并不是為了論證人的本性是惡,他所強調(diào)的重點是“化性起偽”,其最終目的是通過后天人為來引人向善。《荀子》一書中多次談到“性”,然而其中的“性”有不同的含義,既有人的天生質(zhì)具層面,即本能之性,也有順氣而言的才性和人生而具有的知性。荀子對于三種“性”有不同的態(tài)度和處理方法,如果不加以討論,則會認為荀子的人性論是有矛盾的。荀子的側(cè)重點是知性,知性具有奠基地位,使圣人制禮作樂成為可能。“知”是“心”的功能,“知”既指人的認知能力,也指人的智慧。同時,“知”也需要一個實現(xiàn)過程,荀子正是通過人的知性能力處理人的情感欲望,從而“化性起偽”,實現(xiàn)禮義化的人生。
關(guān)鍵詞:荀子;人性論;多重含義;知性
中圖分類號:B22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22-0153-04
引言
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作為稷下學宮的學術(shù)領(lǐng)袖,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思潮的影響下,其人性論思想也呈現(xiàn)出復雜性、豐富性的特點。當前學術(shù)界的主流看法認為荀子的人性觀是性惡論,并且歷史上多數(shù)儒家及現(xiàn)代研究學者對荀子持否定意見,認為荀子是孔子和孟子的歧出。牟宗三先生對荀子的人性思想即性惡論采取了貶低的態(tài)度,“荀子特順孔子外王之禮憲而發(fā)展,客觀精神彰著矣,而本原又不足,本原不足,則客觀精神即提不住而無根,禮儀之統(tǒng)不能拉進來植根于性善,則流于‘義外,而‘義外非客觀精神也”[1]。勞思光先生認為,荀子只能將價值根源歸于權(quán)威主義[2]。歐陽禎人認為荀子把人性改造的成功與否寄托在“知性”之上是本末倒置的,與他的理論預設(shè)相矛盾[3]。
但是,荀子的人性論思想能否僅用“性惡論”簡單概括?“性惡論”是否與荀子的其他思想相一致?“性惡論”的價值是否不高?這些問題應(yīng)該值得學術(shù)界密切關(guān)注,不能簡單地從字面上理解荀子的性惡論,認為其與孟子的性善論對立。近年來,不少學者重新重視荀子,通過探究荀子的“性”的內(nèi)涵對荀子的人性思想重新進行梳理,從而論證荀子人性論的重要性及價值。學界也紛紛從不同角度各持己說,有主張荀子是“性惡論”者;有主張荀子是“性樸論”者;也有主張荀子是“性惡心善”論者。基于以上學術(shù)背景,筆者通過文本首先探究出荀子論“性”的三重含義;其次認為荀子的側(cè)重點是人的知性,知性具有奠基地位;最后從“知”的過程和“知”的作用兩方面探究荀子對知性的看法。
目前,學術(shù)界對荀子的人性論思想及其與孔子和孟子的人性觀比較研究較多,提出荀子人性觀新解的也較多,但是對于荀子人性思想中作為“心”的功能——人的知性能力研究較少。同時,學術(shù)界的主流看法認為荀子人性論的主體是本能之性,且大多從荀子論“性”的一個方面展開研究,雖有道理但并不完備。因此,本文的價值在于全面地看荀子所論之“性”,提出并論證了荀子論“性”的側(cè)重點是“知性”這一觀點。筆者通過研究荀子“性”中的“知”來維護荀子“性惡論”的觀點,同時認為荀子的側(cè)重點不是證明“人之性惡”,其最終目的是通過人的知性能力強調(diào)“其善者偽也”,最后實現(xiàn)禮儀化的人生。
一、荀子論“性”的多重含義
《荀子》一書中關(guān)于“性”的描述散見在多篇,需要根據(jù)前后文不同的語境結(jié)合荀子的整體思想加以理解。荀子論“性”呈現(xiàn)出融匯百家的特色,他主要是站在批判孟子性善論的立場,認為孟子的性善論不切實際,但是二者殊途而同歸,最終立場都是為了引人向善。可以說,他們是在向內(nèi)、向外兩方面發(fā)展了孔子的人性思想。孟子將天生的仁義引進到儒家思想中,而荀子則將其從儒家思想中帶了出來。關(guān)于荀子論人性的內(nèi)涵,學術(shù)界分歧較大,牟宗三先生認為人性有雙重含義,上層的人性指創(chuàng)造之真幾,下層的人性指“類不同”的性。孔孟和《中庸》不從下層的人性立論,只有告子、荀子、王充的人性才涵有此義[4]。他認為:“荀子雖為儒家,但他的性惡說只觸及人性中的動物層,是偏至不中肯的學說。”[4]可見,牟宗三先生主要看到了荀子論“性”的一個層面,并將其貶低。筆者認為荀子的“性”有三重含義:第一,與生俱來的本能之性;第二,順氣而言、人人不同的才性;第三,人人本有的相同的知性能力。
(一)與生俱來的本能之性
首先,荀子從生理現(xiàn)象這一層面論人性。他第一次規(guī)定“性”是在《禮論》篇:“性者,本始材樸也。”人的天性是天然的質(zhì)具。荀子又說:“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荀子·正名》)這里的“性”具有生物性,是人生而具有,天然生成,純?nèi)翁烊坏模笾轮傅氖侨说亩康雀泄倌芰Α9受髯釉唬骸胺残哉撸熘鸵玻豢蓪W,不可事;禮儀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荀子·性惡》)這一層面的性是被給予的事實,它使人類生命成為如此,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據(jù)所在。荀子對孟子論點直接針鋒相對的一句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荀子·性惡》)荀子認為,這一生理層面的性,人人同是惡的,它包括了人類的原始欲望和追求欲望得到滿足的自然本能,如果順著這一本性,則會出現(xiàn)混亂的局面。再如“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惡》)。在荀子那里,情與性并沒有嚴格的區(qū)分,情屬于性,是性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這些也是人的生理欲望,是人們還沒有與外界接觸時就已經(jīng)具有的性狀,它本身并不能轉(zhuǎn)化。“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zhì)也;欲者,情之應(yīng)也。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荀子·正名》)荀子在這里區(qū)分了性、情、欲,順著欲望而追求它,這是人之常情,即人的本性如此。荀子認為,如果人的本能之性順著情欲發(fā)展則會趨向于惡,但是有智慧的人會有所為和有所不為,這正是實現(xiàn)后天道德行為的依據(jù)。
(二)順氣而言、人人不同的才性
荀子認為“氣”是世界運動的方式,“氣”即陰陽二氣,它推動了自然萬物的變化。“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yǎng)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荀子·天論》)“氣”不僅對萬物的自然運行來說如此重要,它也是人性生成的基礎(chǔ)。荀子說:“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yīng),不事而自然謂之性。”(《荀子·正名》)“和”指陰陽沖氣之和,“性”由之而生。可以說,荀子認為“氣”是構(gòu)成人性的材質(zhì),不同的人順著天生不同的“氣”,則會有不同的才性,這個層面的才性是人與生俱來、秉氣而生的,但卻因為人與人之間智力水平的差異和性情的差別而不同。
牟宗三先生認為“凡‘性有兩路:一是順氣而言;二是逆氣而言。順氣而言,則性為材質(zhì)之性,亦曰‘氣性(王充時有此詞),或曰‘才性,乃至‘質(zhì)性。”[5]荀子論“性”的含義之一即指才性,人生而具有不同的材質(zhì),人的氣秉、智力水平、性情都不同,則才性也不同。“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鱉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鱉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荀子·修身》)在這里,荀子承認人的才性雖然有所差異,但是卻可以通過后天去改變它,從而進行道德修養(yǎng),達到君子甚至圣人的境界。
(三)生而具有、人人相同的知性
“知”指人之心生來具有的認知能力,“知”這一字在《荀子》一書的多篇中多次出現(xiàn)。“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弊》)能夠認識事物,這是人的本性,可以被認識,這是物的自然之理。荀子認為對象可以為人所認識正是因為人天生具有認識能力,能夠產(chǎn)生關(guān)于對象的認識知識。荀子對于“知”的定義還有《正名》篇:“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能是人所特有的,這就叫“知”,如果這種本能與認識的對象相符合就叫“智”。荀子在《性惡》篇中,通過闡釋人具有“知仁義法正之質(zhì)”和“能仁義法正之具”來說明“涂之人可以為禹”。“‘涂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zhì),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荀子認為普通人都有能夠知道仁義法正的材質(zhì),都有能夠做仁義法正的條件,但是“可以做”并不等于“必然做”,這只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種潛在的能力,關(guān)鍵在于后天的選擇,這也正是君子和小人的區(qū)別。
二、知性的奠基地位
在荀子所論“性”的三重含義中,他重視知性的傾向和他的經(jīng)驗主義性格有關(guān)。荀子從人之性惡出發(fā)重視積學積德,強調(diào)圣人制禮作樂,最后通過一系列后天的禮法教化,落腳點是化性起偽。那么,知性為什么在荀子的經(jīng)驗論中具有奠基地位?筆者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論述:第一,“學”何以可能;第二,“圣人制禮作樂”何以可能;第三,荀子的最終目的:化性起偽。
(一)“學”何以可能
荀子認為,如果人之本性順著欲求發(fā)展而沒有節(jié)制的話會導致混亂的局面。欲求雖然不可消除,但是可以通過一系列過程來節(jié)制并且引導它,這一過程就是“學”,認識事物的過程就是“學”的過程。“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shù)則始乎誦經(jīng),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后止也。”(《荀子·勸學》)荀子認為,學習的方法應(yīng)該起于誦讀經(jīng)文,終于研究禮法,而就意義方面來說,學習從書生入手到成為圣人結(jié)束。成為圣人就需要真誠力行,并且長期積累,不斷學習,這一學習過程也是人性不斷完滿的過程。可見,荀子論“學”既包括知識層面的,也包括道德層面的。荀子認為圣人和普通人在本能之性上是相同的,最主要的區(qū)別在于學與不學,而“學”的基礎(chǔ)就在于人的知性能力。
《荀子·解弊》說:“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人運用天生具有的知性能力可以認識外在事物,所以人能夠“學”。同時,“知”與“學”是互相作用的,人通過“知”得以“學”,又通過“學”得以知“道”。萬事萬物本來就是可以認識的,人通過學而知“道”并實踐“道”,因而以通觀萬物,治理天地,實現(xiàn)人的價值[6]。
(二)“圣人制禮作樂”何以可能
典型的儒家思想是以先王的道德標準為規(guī)范,推崇堯舜之道。孔子認為周禮比夏商禮更完備,更加推崇先王之道,而荀子在法先王和法后王問題上和孔子有不同的看法,他比較講究實際,認為不能簡單泥古。但荀子和孔子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推崇圣人。從殷周開始,“圣人作樂”成了諸多圣賢的共識,凸現(xiàn)出“作樂”主體的重要性。荀子繼承了這一儒家傳統(tǒng),認為禮樂以及法律制度應(yīng)該由圣人制作。圣人在本能之性上與普通人相同,那么,“圣人制禮作樂”何以可能呢?正是因為“人生而有知”。通過“知”,圣人可以積學積德。“今使涂之人伏術(shù)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荀子·性惡》)荀子認為普通老百姓專心致志地學習、思慮,長久不息地積累善行,那么最終可以通于神明,與天地并列了,這也就是普通人通過“積”成為圣人的過程。
荀子認為,人的才性天生不同,圣人在才性上要高于普通人,具有比普通人更高的學習能力,但如果僅僅止步于先天才性的差異而無所作為的話,那么后天的教化也無法實施。故而荀子把關(guān)注點放在經(jīng)驗上來,通過心之“知”,強調(diào)人的認識能力。所以圣人通過“知”能積學積德,荀子認為只有對禮樂之治有更深的理解的人,才能更完美地發(fā)揮禮樂精神,才有資格教化眾人。所以圣人能“明禮儀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法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惡》,最終天下得到治理,天下歸善。
(三)荀子的最終目的:化性起偽
“化性”主要指的是后天學習和習染的過程,“起偽”指的則是教化最終的結(jié)果。在荀子的人性論中,知性是其主體,“知”具有重要的作用,正是因為人有“知”,即人有認識能力,所以圣人通過“知”從而“可以學”,圣人通過積學積德教化眾人。可見,正是通過人的知性,才使得化性起偽這一最終目的得以實現(xiàn)。通過“化性”從而“起偽”才可以達到圣人之境,如果人人的道德都達到這一境界,那么治國平天下的目標也就不難實現(xiàn)了。因此,知性在化性起偽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荀子的經(jīng)驗主義傾向正是建立在知性的基礎(chǔ)上。
孔孟那里也有知性傾向,孔子重智,認為通過學詩學禮可以下學而上達最終成就人的德性;而孟子輕智,更重視人的內(nèi)在道德的修養(yǎng),可以說他發(fā)展了孔子的內(nèi)圣路徑;而荀子立足于現(xiàn)實經(jīng)驗層面,強調(diào)“知”具有認識對象的能力,發(fā)展了孔子的外王路徑。但是有學者因此認為荀子的人性思想為性善論,認為荀子所論的人之心所與生俱來的認知能力具有使人向善的正面意義。劉又銘說:“除了情感、欲望外,‘知也在荀子所謂人性的范圍之內(nèi)。而且更重要的是,心所能知的對象,最重要的就是‘仁義法正……這是具有價值義涵需要價值判斷價值抉擇的東西,不是客觀的概念和知識;因此荀子所謂的心是不能簡單歸為認知心的……在荀子的思路中蘊涵著一個未曾明說并且通常被忽視的重要成分:人心先天具備了一份素樸的、有待培養(yǎng)的道德直覺。”[7]荀子論“知”有經(jīng)驗之知和德性之知兩類,但筆者認為,這一點不足以證明荀子的人性思想為性善論,因為荀子所論的人的認知能力并不是先天具有推動人向善的能力,性善論應(yīng)該指人之善是不假外力,自然而然就產(chǎn)生的,然而荀子所論的心之“知”不會自然呈現(xiàn)出善。
三、荀子對知性的看法
(一)“知”的過程
1.天官意物,心有征知
《正名》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凝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天官指人的五官:耳、目、鼻、口、形。荀子認為,要想發(fā)揮人的知性能力,獲得知識,必須先通過五官去接觸外物,從而別同異,這樣人們才能順利交流。但是僅靠感官去接觸外物所獲得的知識是零散片面而不成系統(tǒng)的,還需要心的“征知”的作用。“心有征知。征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將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后可也。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征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荀子·正名》)在荀子那里,知性主體是心,心具有重要的地位,心是一個人精神狀態(tài)的根源。《解弊》篇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是“天君”,“天君”的作用比“天官”更重要。“天官”指人的感性認識,而發(fā)揮“天君”的作用才使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而“制名以指實”。
2.虛壹而靜
“虛壹而靜”是荀子提出來的如何解去心之弊的方法,出自《解弊》篇:“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虛壹而靜”指虛心、專一、平靜,不因為已經(jīng)獲得的去妨礙要接受的,不因為對一事物的認識妨礙另一事物的認識,不因為夢的雜亂擾亂心智。只有這三者都做到了,才可以“知道”,進入認識的透徹以及無遮蔽的境界。“心”遵循“虛壹而靜”的原則而運作的過程,就是求道的過程[8]。“道”是判斷一切的準繩,荀子的主旨在于“知道”,認為這是成圣的途徑,這也可以看出荀子認為認識“道”的過程中,需要實踐工夫。
(二)“知”的作用
1.思慮并調(diào)節(jié)情欲
在荀子第一層面生理現(xiàn)象的“性”中,“性”是被給予的事實,不能為,不可化,人人同質(zhì)。而在荀子經(jīng)驗意義的“性”中,包括了人與外物接應(yīng)所產(chǎn)生的情和欲,情欲之性具有為惡的動機,但是欲望不能夠去除。正如《正名》篇云:“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然不能去欲,但是可以節(jié)制欲望,“欲雖不可去,求可節(jié)也”(《荀子·正名》),從而使得人們的欲望符合禮儀的要求。這一過程就需要發(fā)揮人的認知能力,認知能力是人天生美好品質(zhì)的基礎(chǔ),同時還要求賢師,擇良友。“人雖有性質(zhì)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荀子·性惡》)“性質(zhì)美”是人具有的“不事而成”“不學而能”的美好資質(zhì),須經(jīng)過努力,“知有所合”“化性起偽”才能達到去惡向善的目的[9]。第二層面“性”中的情欲接受知性的引導,這正是這一層面“性”可事、可為的表現(xiàn)。《正名》指出:“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這里的“可”是心之認知能力對情欲的認可,只有先認可了才能去養(yǎng)欲、引導并且調(diào)節(jié)情欲。
2.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形成道德主體
在孟子的心性學中,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意識,道德具有自足性,成就德性順其自然就成為可能。而在荀子那里,人不具有先天的道德意識,《性惡》中荀子反復強調(diào)“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那么,在荀子那里,后天的道德行為如何可能呢?荀子認為人沒有道德自足的可能性,需要主體的不斷努力,正是人心具有知性能力,人們才有成德之可能性。荀子賦予人主觀能動性,認為人在萬物中最為珍貴,因為人有氣、有生命、有知覺、有禮儀。“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荀子認為,道德主體的形成并不是與生俱來的,需要后天的努力,人具有其他事物所不具有的材質(zhì),需要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通過“知”和“義”明辨是非,知道什么應(yīng)該做而做,從而成就德性。
結(jié)語
綜上所述,荀子作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融合了諸子各家的思想精華,其思想自成體系,且獨具特色。對于其人性論研究,應(yīng)該綜觀他的思想全貌來考察。荀子對人性有復雜的理解,他論“性”也是從不同層面上根據(jù)不同語境和論說目的來闡述的。第一層面的“性”,是生理現(xiàn)象的“性”,此“性”是人人所同質(zhì)的既定事實,不可為、不可事,它作為人的天生質(zhì)具,可以說是中性的。第二層面的“性”是順氣而言、人人不同的材質(zhì)之性,即才性。第三層面的“性”是人與生俱來且人人相同的知性。筆者認為,第三層面的知性正是荀子論“性”的側(cè)重點。首先,“知”使得“學”成為可能,使得“圣人制禮作樂”成為可能,最終實現(xiàn)荀子“化性起偽”的目的。其次,“知”需要有兩個過程來實現(xiàn),分別是天官意物,心有征知和虛壹而靜。最后,“知”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它能對情欲做出思慮判斷并指導其表現(xiàn)和滿足,第二,它使人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從而追求道德動機形成道德主體。
荀子的人性論思想具有豐富的內(nèi)涵,“性”有多重含義,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僅看到荀子論“性”的單個含義是不完備的。一方面,荀子的性惡論并不能僅從字面上理解,否則就會認為荀子的禮儀教化只是外在的,在人性中沒有根據(jù),認為荀子的性惡論導致人的道德泯滅,人的道德主體性喪失。另一方面,也不能單純地把荀子的人性論理解為性善論,認為人心生而具有的認知能力具有推動人向善的正面意義,因為心之“知”在自然狀態(tài)下并不能自覺地使人向善, 反而出現(xiàn)向惡的傾向。孟子強調(diào)
性善意味著他注重人本身具有的善性,加以擴充即可成就德性人生;而荀子強調(diào)性惡意味著他更加重視外在的道德教化走知性成德之路。孟子和荀子分別從不同的方向發(fā)展了孔子的人性思想,但二者殊途同歸,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xiàn)禮儀化的人生。
參考文獻:
[1]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
[2]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M].臺北:三民書局,1984:338-339.
[3] 歐陽禎人.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431.
[4]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zh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8.
[5]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2.
[6] 夏超男.荀子“勸學”思想淺析[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11.
[7] 劉又銘.荀子的哲學典范及其在后代的變遷轉(zhuǎn)移[J].漢學研究集刊,2006(5).
[8] 劉亮.《荀子》“虛壹而靜”說續(xù)辨[J].齊魯學刊,2018(2).
[9] 張欣.荀子知性思想初探[J].邯鄲學院學報,2020(2).
作者簡介:皇甫夢華(1998—),女,漢族,河南焦作人,單位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專業(yè)。
(責任編輯:易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