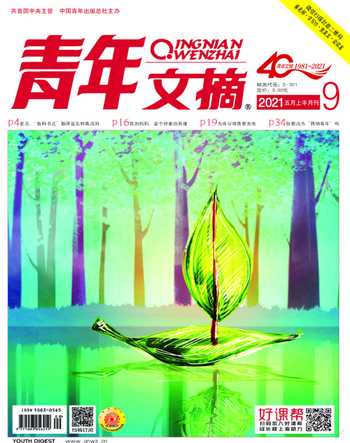春秋和戰國是兩種氣質
2021-12-12 18:05:23李冬君
青年文摘 2021年9期
李冬君

多年來,人們已經習慣用“春秋戰國”來統稱這段歷史,使它們的界限,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別變得模糊不清。其實,從春秋到戰國,變化之大,堪稱兩個時代、兩種氣質。
春秋時期的文化,是周代禮樂文化的下移和普及,禮樂不再為天子所壟斷;而戰國時期的文化,則是諸侯耕戰文化的崛起與擴張。春秋諸子爭鳴和諸侯爭霸,仍帶有相揖并存的封建氣質;而戰國諸子爭鳴和諸侯爭霸,則帶有徹底消滅對方的軍國作風。春秋與戰國,不僅理想不同,而且欲望迥異。
春秋爭霸,各國依然恪守周禮,比如,齊桓公“興滅繼絕”、晉文公“退避三舍”。春秋諸國會戰,開戰前要行禮,要等到一整套禮儀完成才開始交戰。戰爭進程中,天子還要派觀察員來對戰爭進行觀察,并根據周禮對結果進行仲裁,這樣的戰爭有點像體育競賽。
春秋時期,幾十輛戰車會戰,已是一場像模像樣的戰爭了。到了戰國時期,這樣的戰爭規模就是小菜一碟,動輒數十萬大軍廝殺,既不講禮儀,也不講禮義。
孟子說“春秋無義戰”,那是說給戰國人聽的。戰國人的戰爭,沒有文化,就用兵法,兵不厭詐。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殺。殺人盈城,滅他人之國,是一種嶄新的欲望。新生代王者不滿足于春秋霸業,認為只靠小打小鬧,戰爭永遠結束不了。要戰,就要“以戰去戰”“以殺去殺”,就要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一統天下。這種以滅國為目的的戰爭,奏響了戰國時代兼并戰爭的序曲。這是戰國的風尚和志向,其時代意義就是戰,而且是殲滅戰。
戰爭需要戰士,制勝依賴計謀,戰國是一個戰士和策士的時代。從吳越爭霸,到秦始皇統一六國,256 年間,戰士和策士成了時代的主角和戰爭的主力。
儒家“崇德”,是春秋的代表;法家“尚力”,更適應戰國的需求。
(田龍華摘自《深圳特區報》,張云開圖)
猜你喜歡
中國德育(2022年12期)2022-08-22 06:16:18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金橋(2022年1期)2022-02-12 01:37:04
陽光(2020年6期)2020-06-01 07:48:36
陽光(2020年5期)2020-05-06 13:29:18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
足球周刊(2016年14期)2016-11-02 10:56:23
足球周刊(2016年15期)2016-11-02 10:55:36
足球周刊(2016年10期)2016-10-08 10: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