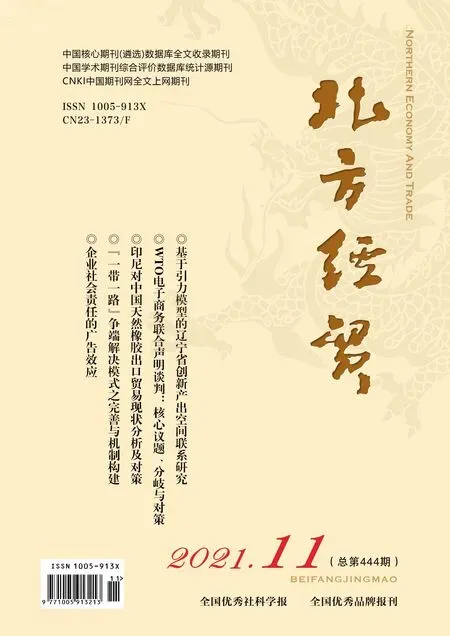基于流動性監管指標的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研究
席鵬飛,方佳麗,胡小虎
(武漢紡織大學經濟學院,武漢 430200)
一、引言
在黨中央提出建立經濟雙循環的大背景下,經濟內循環要求需求側的改革催生發展新動能。商業銀行作為服務國民經濟的重要金融機構,既面臨重大的發展機遇又存在眾多風險挑戰。特別是在大力推進普惠金融和利率市場化改革等政策的新形勢下,商業銀行需要積極應對政策和市場變化,調整流動性政策和信貸結構。這樣既有利于商業銀行的生存發展,也能夠更好地發揮對經濟轉型的促進作用。
2018 年,修訂頒布的《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提出加強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建立健全流動性風險管理體系,確保銀行體系穩定運行的目標。[1]《辦法》定義了流動性風險管理的治理結構、識別計量和監管指標等,并根據商業銀行資產規模進行分類監管。《辦法》頒布至今不足三年,監管要求的流動性指標因為監管資本披露提交的滯后性,目前尚不足以全面落地和整體把控。商業銀行對風險管理和信息披露能否嚴格執行,新的指標對流動性風險監管能否起到預警作用還有待觀察。但是,作為衡量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的重要工具,研究流動性監管指標對優化監管細節和做好長期持續監管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目前,我國關于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的學術成果較為豐富,現針對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進行了文獻整理。現有分析指標主要分為三種:監管監測指標、一般性財務數據和模型構建。監管監測指標主要源自如《辦法》等由監管機構提供的相關文件。一般性財務數據包括常見的流動性分析和資產負債缺口等。模型構建指標則是研究者根據研究內容制定的特殊指標。
在流動性風險研究中,進行流動性壓力測試是較為普遍的一種研究方法。王莎(2019)通過進行商業銀行流動性壓力測試,發現面對突發的流動性風險時,目前的流動性監管指標存在有效性不足等問題。[2]劉精山等(2019)引用商業銀行流動性錯配指數(LMI)進行壓力測試,發現商業銀行應對風險的能力存在顯著的異質性。[3]錢崇秀等(2020)研究不同時間段的合同期限錯配情況,發現商業銀行面對流動性風險時,在內部流動性調整和同業拆借上存在異質性。[4]王曉婷等(2017)將流動性風險資本視作期權,認為資本作為風險管理工具能有效提高抵御流動性風險的能力并減少帶來的損失。[5]
根據《辦法》對商業銀行進行的資產規模劃分以及學者研究,可以發現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存在明顯的主體差異。從理論和現實上都要求監管機構有針對性地制定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和監管要求。關晶奇(2019)認為,相比于國內大型商業銀行,中小銀行在風險管理的整體架構中有諸多共性問題。[6]尚航飛(2018)也提出流動性風險監管改革會使得中小型銀行面臨負債成本上升和同業規模縮減等挑戰。[7]因此,本研究通過收集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和財務數據,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的整體情況加以分析,為指標調整和政策補充提供參考。
三、流動性監管指標的計量標準概述
如表1 所示,根據《辦法》規定,對資產規模不小于2 000 億人民幣的商業銀行和資產規模小于2 000億人民幣的商業銀行采取不同的流動性監管指標。流動性覆蓋率和流動性資產充足率在計算上略有不同,但其核心目的均為確保商業銀行有足夠的高流動性資產,在壓力情景下能夠滿足未來30 天的流動性需求。流動性匹配率通過設置不同的折算率對資金來源和資金運用進行加權,充分考慮資產負債的期限結構,旨在防止商業銀行因為嚴重的期限錯配而帶來的流動性風險。凈穩定資金比例采取設置穩定資金系數的方式,將可用穩定資金和所需穩定資金通過資產負債項目的賬面價值以及表外風險敞口與相對應的穩定資金系數的乘積計算得出。
四、流動性風險管理現狀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樣本選取
根據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的具體要求,選取不同類型銀行的流動性風險數據。由于商業銀行信息披露情況不同,存在明顯的數據缺失和標準差異。在有限條件下選取62 家銀行作為研究樣本,包括全國性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和民營銀行2016-2019 年的年度數據。指標包括四年的流動性覆蓋率、流動性比例以及2019 年的凈穩定資金比例和流動性匹配率(數據源自wind 數據庫和各銀行官網年報)。
(二)描述性統計
根據《辦法》所列標準,分別對資產規模在2 000億上下的商業銀行各監管指標進行描述性統計。如表2 所示,資產規模不小于2 000 億人民幣的商業銀行相對于資產規模小于2 000 億人民幣的商業銀行,其資本充足率整體偏低,不良貸款率波動性較小。樣本范圍內的流動性比例整體超過監管標準的25%,符合監管要求。規模較小的商業銀行流動性比例平均值大于資產規模較大的商業銀行,同樣存在標準差偏大的情況。資產規模較大的商業銀行在貸存款比例上相對占優,平均值和最大值均相對較大。在本研究的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上,依據資產規模采取不同的監管標準。如表1 所示,資產規模不小于2 000 億人民幣的商業銀行,凈穩定資金比例和流動性覆蓋率整體大于100%,符合監管要求。資產規模小于2 000 億人民幣的商業銀行,其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和流動性匹配率存在低于監管要求100%的情況。根據《辦法》要求,商業銀行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要求于2018 年底前達到80%,2019 年6 月底前達到100%,流動性匹配率自2020 年1 月1 日起執行。現有披露信息屬于過渡期內要求,同時《辦法》鼓勵有條件的商業銀行提前達標。

表1 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體系表

表2 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描述性統計結果
圖1 為樣本內商業銀行的四項流動性指標在2016-2019 年四年內的變動情況,可知目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比例和貸存款比例呈增長趨勢,資本充足率和不良貸款率保持在合理區間。商業銀行流動性比例2016-2019 年由48.80%增長至70.99%,流動性得到充分釋放,商業銀行資產安全和短期償債能力逐漸提高。根據2015 年修訂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和《辦法》內容,取消對商業銀行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75%的規定,將商業銀行貸存款比例由監管指標調整為監測指標。因此,2016-2019 年的貸存款比例四年內由64.66%增長至74.72%,符合現行法規下的流動性要求。貸存款比例限制的取消,有利于減輕商業銀行負債成本和行政約束,一定程度上能夠促使商業銀行增加對“三農”貸款和小微企業貸款的規模。

圖1 2016-2019 年商業銀行流動性指標
在樣本數據中選取34 家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缺口進行分析,得到2016-2019 年各期限窗口下的資產負債期限錯配情況。由于不同商業銀行審計方式存在區別,數據整理存在一定障礙。本研究的流動性缺口為表內流動性缺口,對于表外事項和衍生金融工具現金流暫不做分析。[8]如圖2 所示,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缺口整體呈現收緊狀態,一年以上期限的流動性缺口為正,且即時償還、已逾期和無期限情況下的資產負債缺口逐年減少。同時,短期流動性缺口出現與整體相反的趨勢,特別是三個月至一年資產負債缺口,三年的跌幅為57.72%、159.91%和86.24%。這一情況表明,樣本內的銀行流動性缺口整體穩步向好,短期流動性風險仍然顯著。

圖2 商業銀行合同期限錯配缺口
五、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監管面臨的問題
第一,通過收集國內商業銀行流動性指標,可以發現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在信息披露上存在一定的監管漏洞。一是不同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披露程度不同,規模較小的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在年度報告和監管資本的披露上存在明顯的紕漏,資產規模較大的國有大型銀行、上市銀行和民營銀行的信息披露情況相對完整,信息可獲取性強。二是在審計數據上存在標準不統一的情況,如流動性風險缺口的期限窗口劃分,存在無期限、即時償還和已逾期的不同組合以及三個月內和一個月內的不同劃分。這些數據的披露差異一定程度上為商業銀行掩飾潛在風險提供了便利,對流動性風險監管造成阻礙。
第二,大型商業銀行的資本結構存在更大的風險隱患,對風險資產的偏好呈現擴大趨勢。本研究樣本數據顯示大型商業銀行存在較低的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比例以及較高的存貸款比例。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和結構得到充分調整,不良貸款和在險資產規模也隨之增加。一是由于“大而不能倒”的特性,大型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管理存在固有的風險偏好,對于穩定銀行流動性的問題不夠重視。二是金融科技和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催生大量非傳統的資金來源和使用途徑。商業銀行不僅會因為市場競爭而降低對流動性風險的預警閾值,而且在復雜的資金流動中也難以理清流動性風險管理的現狀。
第三,商業銀行短期流動性缺口出現擴大趨勢。在流動性風險監測方面,2016-2019 年的整體流動性風險缺口逐步收緊,但不可忽視短期流動性缺口一直存在,并出現擴大趨勢。商業銀行適度利用資產負債的期限錯配能夠增加更多的資金業務,促進長期信貸的發展。同樣的,商業銀行過度依賴短期現金流支持長期資金項目會引起短期流動性緊缺問題,不利于維持銀行存貸款業務的穩定,嚴重的會引發連鎖反應,造成系統性風險。
六、對流動性風險監管分析的結論和建議
第一,鑒于當前商業銀行在監管資本的信息披露上存在時間滯后和數據殘缺的情況,可規范信息披露標準,對需要按季度披露的信息嚴格規定提交內容和時間期限。資產規模小于2 000 億人民幣的商業銀行,在流動性風險監管的主體數量上占比高,信息披露要求相對放松。一方面,對大型銀行要求完善信息披露機制。另一方面,出臺針對小型銀行的風險監管和信息披露政策,并將其執行程度納入流動性供給和優惠政策的審核中,激勵商業銀行持續進行流動性風險監測和信息披露。
第二,資產規模不小于2 000 億人民幣的商業銀行資產充足率相對較小,其風險資產規模可能比重較高。在存貸款比例上也相對傾向于擴大信貸規模。因此,可對這一類銀行的資本結構和信貸結構要求作出進一步調整,如劃分出各級信貸資產的占比要求,在增加對小型銀行監管力度的同時,確保大型銀行維持穩定的風險偏好。同時,進一步加快商業銀行破產保險和資產管理改革,削弱大型銀行盲目擴大信貸規模的傾向。
第三,針對短期流動性缺口顯著的情況,監管機構可適當增加監管力度和即時監管。一是要求商業銀行對流動性缺口進行限制性管理,將銀行的資產規模、業務范圍、流動性偏好和發展計劃等因素作為設置限制性管理的依據,合理劃分流動性限額和短期流動性缺口規模。[9]二是對于商業銀行出現的資產負債結構變動和短期融資依賴情況,監管機構需要在季度報告以外增加日間信息統計和管理,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缺口實現及時了解和風險提示。三是加強表外流動性缺口和衍生金融工具現金流管理。衍生金融工具的結算方式分為凈額結算和總額結算,和表內流動性缺口的現金流不能直接計算分析。監管機構可以將衍生金融工具流動性的信息披露單獨囊括進流動性風險監管的要求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