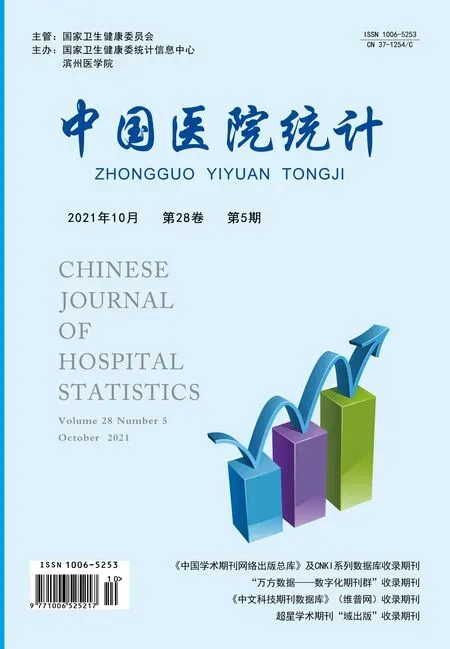癥狀監測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的應用進展
羅 純 彭愛宇 宗慧瑩 寧佩珊 嚴俊霞 鄧 靜 史靜 馮湘玲 黃 云 虞仁和 李杏莉 胡國清
1中南大學湘雅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系,410078湖南 長沙;2中南大學湘雅公共衛生學院中心實驗室,410078湖南 長沙;3中南大學湘雅公共衛生學院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系,410078湖南 長沙
癥狀監測又稱為癥候群監測,是通過對臨床診斷前的與健康相關數據進行系統且持續地收集、分析和解釋,及時發現特定疾病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異常聚集,來確定是否需要進行早期預警和快速反應的監測方法[1]。癥狀監測系統主要由4部分組成:數據收集、數據分析、結果報告、信號核實與響應(圖1)。癥狀監測與傳統疾病監測不同之處在于它并非基于實驗室確認的疾病診斷,而是基于非特異性健康指標,包括臨床癥狀和替代數據(如學生缺課、藥物銷售等),能夠在重大傳染病疫情發生早期起到識別和預警作用,對控制傳染病的傳播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作為一種新發的重大傳染病,目前尚不清楚癥狀監測在其防控中的應用情況。本文對癥狀監測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階段中的有效做法和不足進行總結,為未來有效地開展癥狀監測,以應對類似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提供參考。

圖1 癥狀監測系統實施流程
1 數據收集
1.1 目標監測癥狀
早期在對新冠肺炎病例的監測過程中發現88%的人出現了發燒癥狀,因此主要對體溫進行監測[3-6];其次為急性呼吸道感染癥狀,包括咳嗽、呼吸急促、喉嚨痛、鼻塞、流涕等[4,6-8];有地區對味覺或嗅覺喪失等特異性癥狀進行了監測[5,9-10];此外,頭痛、疲勞、腹瀉、厭食等非特異性癥狀和肺炎、胃腸炎等疾病也包括在監測范圍中[7,11]。除了對癥狀進行監測,利用GPS定位或郵政編碼以確定疑似新冠肺炎病例的地理位置,通過對疑似新冠肺炎病例的接觸者進行追蹤可以確定高危人群[3,12-13]。當前報告的癥狀多為非特異性癥狀,具有這些癥狀的人可能只是普通感冒或是流感患者等,因此可能存在大量虛假信號。
1.2 監測數據源
目前大多用于防控新冠肺炎的癥狀監測方案均收集自公民自我報告的數據,包括個人信息、主要癥狀、流行病學史和地理位置等信息;其次為在社區和醫院獲得的主要癥狀和檢查結果等信息。除醫院等常用數據源外,也可結合藥店、學校、車站、互聯網活動數據等信息用于癥狀監測[14-15],這些數據源在及時性和敏感性等方面有所不同。以往研究顯示,在各個數據庫顯示的一致性變異往往提示著傳染病的暴發[16]。通過對多個不同的數據源進行綜合整理相互印證可以提高癥狀監測的準確性,如湖北洪湖1個基于云系統的癥狀監測系統綜合了醫院、實驗室和自我報告等數據用于防控新冠肺炎。然而對多個數據源進行綜合需要建立新的信息平臺以進行數據的處理和分析,這需要多方面的協調與合作和大量資金。如上述湖北的癥狀監測系統的實施需要40多名專家的合作,并且1個月成本約為300萬人民幣,因此建立新系統需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3]。
1.3 信息采集方式
1.3.1 基于網絡的自我報告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網絡已經成為獲得海量數據的主要來源。目前已有許多國家和地區采用基于網絡的方式(包括微信、網頁、應用程序等)進行關于新冠肺炎癥狀的自我報告。如湖北武漢在微信小程序收集癥狀和個人接觸史等信息[3,13];湖北襄陽和日本東京則使用了掃描 “二維碼”的方式收集數據息[17-18];波多黎各開發了Survey123 for ArcGIS平臺;美國和英國開發了基于智能手機的新冠肺炎癥狀監測程序來收集參與者過去24 h的新冠肺炎相關癥狀、醫療就診結果和地理位置等信息[9-10,19]。然而這些需要網絡和(或)智能手機參與的癥狀監測方案依賴于用戶的參與意愿和網絡條件,另外還存在許多的隱私和安全問題。
1.3.2 基于電話的人群調查
基于電話的人群調查對通過網絡進行癥狀信息的收集起了一定的補充作用。如英國國民保健111服務的電話熱線通過每周審查各癥狀的呼叫數量來監測包括新冠肺炎在內的多種傳染病[8];孟加拉國通過配備交互式語音應答系統的熱線號碼來收集信息,并根據來電號碼進行地理定位[12];加拿大的民意調查論壇通過電話或短信方式調查居民們相關新冠肺炎的癥狀以及檢測結果[11]。
1.3.3 基于現有的信息系統
現有的信息系統由于多年的實踐經驗有一系列完整的分析、處理機制,對開展新冠肺炎癥狀監測能夠提供一定的基礎。如湖北洪湖創建的1個癥狀監測系統利用了當地9家醫院的電子病歷系統數據[3];澳大利亞利用衛生服務中已經建立的社區哨點定期、隨機地調查社區人員的急性呼吸道癥狀,并且對一些有較高風險的人員(如服務人員、送貨工人等)進行重點觀察[6];美國CDC的BioSence平臺實時接收來自急診的數據[20];英國癥狀監測系統則接收來自全科醫生日常活動、急診科和國際救護車調度等數據系統的信息[8]。
2 數據處理與分析
2.1 數據處理
隨著電子信息化的快速發展,許多機構可在移動端統一規范化地保存數據。然而,原始數據常出現缺失、錯誤或重復等情況,因此需要對數據進行預處理,提高其規范性以進行進一步分析。如湖北洪湖所建立的1個綜合性的癥狀監測系統根據ICD-10 CM分類方法對報告的新冠肺炎相關癥狀進行分類[3],新加坡醫院的基于電子病例系統的癥狀監測方案對相關癥狀采用了SNOMED進行編碼分類[7],另外還可根據新冠肺炎防控和診療方案對報告者進行分類[17]。由于性別、年齡等基線數據可能會對數據分析的結果造成影響,數據分析時需對其進行調整,如東京的COOPERA癥狀監測系統使用年齡-性別標準化發病率(EBSIR)對數據進行了預處理[18]。
2.2 數據分析
癥狀監測系統中常采用的數據分析預警模型包括時間預警模型、空間預警模型和時空預警模型3大類。由于時間預警模型和空間預警模型的局限性,大多用于發現新冠肺炎相關癥狀異常聚集群的監測方案均采用時空預警模型,如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開發的COVID control軟件和東京的COOPERA系統[10,21]。美國的癥狀監測項目在BioSence平臺上使用了差分自回歸移動平均模型(ARIMA)、指數加權移動平均法(EWMA)、累積和(CUSUM)法和時空掃描統計等方法來分析處理數據[22];而英國開發的1個新冠肺炎癥狀研究軟件使用的是自制的模型[9]。
3 結果報告
通過各模型所計算的結果需要根據提前設定的閾值以確定該結果是否進行報告,如新加坡在醫院建立的防控新冠肺炎的癥狀監測系統根據前2周的基線數據對異常聚類進行了明確定義,即大于基線數據的50%或2周的上升趨勢大于1個標準差[4]。異常信號應當及時有效地反映給相關部門以及時采取行動。分析結果的報告常以文本或圖表等方式發送給相關人員,如美國的Bioscience平臺以圖形或圖表進行展示某特定時間段和區域內的某癥候群的變化趨勢[20];另外還可應用地理信息系統軟件技術來表述空間信息,采用熱圖的形式呈現各地的異常水平,如美國的COV-ID-control軟件收集的數據按縣進行匯總后在軟件內使用癥狀分布圖和時間序列圖呈現給用戶,若某特定區域內或者是較近的時間內出現癥狀數量大于預設值時及時反映到州和地方政府[10];中國、孟加拉國和日本收集的數據匯總分析得到的異常結果常反映到公共衛生部門或國家衛生總局[12,17-18]。
4 信號核實與響應
通過數據分析得到的異常信號僅僅是基于統計學意義,并且癥狀監測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干擾(如季節效應、錯誤報告、漏報等)。因此,相關人員在接收到預警信號后,應當立即采取流行病學調查和實驗室檢查等措施進行核實驗證;同時結合其他監測系統來綜合判斷此異常是由于正常波動、其他原因(季節變化)或是真正的傳染病暴發。
5 主要用途
癥狀監測方案可以克服農村和偏遠地區的檢測能力有限和報告延誤問題,通過及時調整疫情防控措施,有效控制疫情的傳播。例如孟加拉國通過電話和網頁進行癥狀的報告,及時了解疾病的早期階段,通過探索建立新冠肺炎預測模型,有效地監測疫情的動態和流行趨勢[12,19]。識別引起新冠肺炎的潛在危險因素可以減少潛在感染和病例數量,另外,通過結合地理位置可以確定新冠肺炎檢測的優先區域以指導衛生規劃和資源分配決策,補充初級保健系統[7,10,13]。通過利用現有的電子病歷系統等可有效減少疫情監測和病例診斷之間的時間差,反過來還可指導醫院對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決策[7];通過發揮發熱門診作為醫療機構傳染病防控第一道防線的作用,能夠有效降低病例的交叉感染,結合掃描二維碼進行癥狀的自我報告方式能夠為政府下一步利用線上工具開展疫情的防控工作提供重要依據[17]。
隨著時代的發展,全球面臨著不斷出現的新的傳染病暴發和舊的傳染病復發威脅,癥狀監測能夠比傳統監測系統提前1~2星期發現病例提供預警信號[12,23],使在疫情早期能夠發現并迅速應對疫情,因此未來應該大力發展癥狀監測。目前已經有多個國家采用癥狀監測的方式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目前仍然存在非特異性癥狀敏感度較低、數據源單一、成本效益過低等問題。
基于上述分析,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強化新冠肺炎癥狀監測:(1)由國家專業技術機構制定統一監測方案,規范開展癥狀監測;(2)充分利用現有信息技術,開發適宜癥狀信息采集平臺,支持在緊急情況下針對類似新冠肺炎等重大傳染性疾病開展高質量的癥狀監測工作;(3)將癥狀監測信息與其他來源信息有機融合,提升及時發現疫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