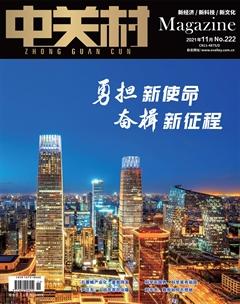“巨無霸”銀行如何才能臨危不倒?
張銳

結束了時長為一年零一個月的征求意見期,中國人民銀行會同銀保監會、財政部制定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總損失吸收能力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日前正式落地施行。《管理辦法》不僅明確了我國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總損失吸收能力的監管指標,同時劃出了提升總損失吸收能力的合格工具標準,從而為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與進一步增強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健康性加厚了較為牢靠的“風險緩沖墊”。
根據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發布的最新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榜單,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名列其中。基于“大而不能倒”的特殊地位,FSB制定的國際監管規則要求G-SIBs必須建立包含恢復計劃和處置計劃的風險處置制度,也就是所謂的“生前遺囑”,其中恢復計劃是指在持續經營能力可能或者已經出現問題等壓力情景下,G-SIBs可迅速補充資本和流動性,以恢復持續經營能力;而處置計劃則是指G-SIBs在無法持續經營并身處危機狀態時,自身具有足夠的總損失吸收能力可以調動,以避免借用納稅人資金進行“外部救助”。
所謂總損失吸收能力是指通過減記或轉為普通股等方式吸收損失的資本和債務工具的總和,說的直白一些就是G-SIBs進入處置階段后可以轉股與沖減和消除債務的能力,它由內部總損失吸收能力和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組成,前者指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處置實體向其重要附屬公司承諾和分配的損失吸收能力,后者是指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處置實體應當持有的損失吸收能力。雖然在處置階段內部總損失吸收能力同樣會表現出債務取消之類的積極結果,但同時也必然會帶來處置實體總資產的減記,由此實質性并不利于G-SIBs總處置活動的正常進行,因此,參考FSB的監管規則,《管理辦法》重點強調的是中資G-SIBs的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
在FSB看來,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比率包括風險加權比率和杠桿比率,《管理辦法》也完全吸收了這兩個監管指標,其中“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風險加權比率=(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扣除項)÷風險加權資產×100%;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杠桿比率=(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扣除項)÷調整后的表內外資產余額×100%”,由公式可以看出,如果G-SIBs手中可以調用的合格工具越多,其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即分母就大,反映在等式左邊意味著其相對于風險資產與杠桿的占比越高,因此,對于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來說,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風險加權比率和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杠桿比率當然越高越好,《管理辦法》確定的指標區間是,中資G-SIBs風險加權比率于2025年初達到16%,2028年初達到18%;杠桿比率于2025年初達到6%,2028年初達到6.75%,且兩個指標的上限區間與FSB的要求完全一致。
壯大中資G-SIBs的外部總吸收損失能力,必須有可以利用的合格工具,包括資本工具與非資本工具兩類。針對資本工具,《管理辦法》明確指出,符合資本監管規定的監管資本,在滿足剩余期限一年以上(或無到期日)的情況下,可全額計入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具體說來主要包括核心一級資本(如普通股、資本公積、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等)、其他一級資本(如永續債和優先股)、二級資本(如超額貸款損失準備)。值得注意的是,在不違反FSB監管框架之下,《管理辦法》運用了豁免規則,允許將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管理的存款保險基金計入中資G-SIBs的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按照風險加權比率上限分別在2025年初豁免2.5%和在2028年初豁免3.5%,也就是存款保險基金可計入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的規模分別為中資G-SIBs風險加權資產的2.5%和3.5%。
在非資本工具方面,包括實繳、無擔保、不適用破產抵銷或凈額結算等影響損失吸收能力的機制安排、剩余期限一年以上(或無到期日)、工具到期前投資者無權要求提前贖回以及由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處置實體直接發行等八類工具都可全額計入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只是《管理辦法》同時明確了各類工具的損失吸收順序,其中非資本債務工具應在二級資本工具之后吸收損失,而且只有二級資本工具全部減記或轉股后,方可視情啟動非資本債務工具的減記或轉股。
顯然,并不是所有的資本工具與非資本工具都可以用作充實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如用于滿足儲備資本、逆周期資本和附加資本等緩沖資本監管要求的核心一級資本、中資G-SIBs直接或間接持有本銀行發行的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非資本債務工具、中資G-SIBs之間相互持有的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非資本債務工具,以及由受保存款、活期存款、衍生品負債、結構性負債、非合同負債和難以核銷與減記或轉為普通股的負債組成的“除外負債”等不可計入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由此組成了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風險加權比率與杠桿比率公示中的扣除項。做出這樣規定,就是要防止中資G-SIBs在處置過程中挖東墻補西墻與以次充優,從而達到暫時性掩蓋危機事實的目的。
無疑,充實與備足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等于前瞻性地構建起了風險處置機制,對中資G-SIBs來說就是增厚了抵御與化解風險的緩沖墊,不僅利于提高穩健經營水平,而且能夠控制非理性擴張和系統性風險的積累,同時確保中資G-SIBs以優質的財務與信用形象參與全球化競爭。但是,對標相關要求,我國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面臨的壓力也的確不小。與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杠桿率目前基本達標不同,以2020年為基數,滿足2025年初16%的風險加權比率標準,剔除存款保險等豁免,中資G-SIBs將面臨約2.1萬億元的工具缺口,基于2028年初18%的標準,又尚存約3.6萬億元的缺口。不僅如此,增強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的同時,中資G-SIBs必須滿足2.50%的儲備資本、0-2.50%的逆周期資本以及1.00-3.50%的附加資本要求,補充資金缺口的壓力可見一般。
顯然,利用好接下來5-8年的過渡期,延伸內源性與外源性融資力度是中資G-SIBs篤定不二的策略。一方面,要剝離資本消耗高、盈利水平偏低的非核心資產,以降低風險加權資產增速,同時致力開拓財富管理業務等新的盈利增長點;另一方面須優化資本債務工具的類別、期限與成本等結構因素,提升境內資本市場融資效率,并盡快推出非資本類債務工具,以逐步替換金融債和商業票據等非合格債務工具;與此同時,中資G-SIBs應緊跟主要經濟體寬松貨幣政策不會大幅回撤與轉向的低成本窗口期,在倫敦、法蘭克福、中國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適時發行以美元、歐元計價的固定利率長期合格債券,拓展流動性的補充渠道。
政策層面更應該為中資G-SIBs提升外部總損失吸收能力保駕護航。首先,在確保不低于150%的最低監管要求前提下,允許中資G-SIBs將目前平均高達207.7%撥備率適當降低,同時階段性下調分紅率,以支持其通過有序釋放利潤拓展內源資本補充空間;其次,加快修訂《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有序釋放資本監管紅利,其中重點是放寬現行風險加權資產計量規則,在逐一核驗的前提下,可將中資G-SIBs內部評級法資本底線要求從目前不低于權重法的90%降至《巴塞爾協議》底線的72.5%。再者,適當擴大享受優惠風險權重安排的信貸資產類別,包括在有序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背景下適當降低綠色信貸的風險權重,在風險可控前提下推出針對中資G-SIBs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專項額度等;此外,還要在配套規則層面優化審批流程,推出儲架發行機制,允許中資G-SIBs在持續符合發行條件和監管指標前提下,靈活安排具體發行時間和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