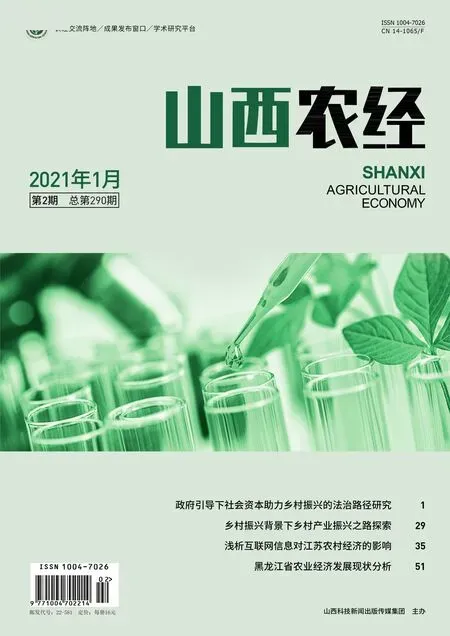我國精準扶貧政策過程文獻回顧與鄉村振興戰略展望
□周 通
(南通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江蘇 南通 226019)
1 精準扶貧思想萌發
我國扶貧工作開展已久,但扶貧思路還是以“大水漫灌”的模式為主,到了21 世紀才逐漸有學者關注到“提高扶貧精準度”的問題。文獻檢索發現,最早關于扶貧精準性的論述文獻是江毅等2006 年發表《提高扶貧精準度》。2007 年,吳睿鶇結合扶貧實踐,著重從精準識別的角度入手,提出提升扶貧工作質量的建議。同年,張興堂等從資金管理角度,提出應該規范扶貧資金監管工作,從精準識別角度提出了重點幫扶最需要資金的組織和個人。就規模、理論深度、資金支持而言,這個時期的研究沒有體現出對“提高扶貧精準度”問題的系統理解和足夠重視,但這部分研究還是起到了先發作用。
2 精準扶貧思想確立
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湖南花垣縣十八洞村時提出了“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分類指導、精準扶貧”十六字方針,被學界公認為是我國精準扶貧理念正式確立的標志。2014 年,國家各部委從頂層設計角度,詳細規制精準扶貧工作的推進模式。同年,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闡釋了精準扶貧理念,提出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精準扶貧迅速成為熱議的關鍵詞。
3 精準扶貧研究的階段性劃分
學界對于精準扶貧政策問題的討論和看法不一,但從總體分析路徑上看,已有研究對精準扶貧工作的分析大致可分兩個階段,即脫貧成效性研究與脫貧持續性研究。
3.1 脫貧成效性研究
最初,學者們的研究思路主要集中于響應號召,提升扶貧工作過程中的精準化程度,從而進一步提高脫貧成效性,可稱此階段為脫貧成效性研究階段。精準識別是精準扶貧過程的第一步,也是最為基礎性的工作。周常春等(2016)[1]發現,長期以來扶貧主要依靠各級政府的推動,組織、重點、手段、任務、管理機制都存在諸多問題,造成效率低下,目標經常發生偏離和轉換,并且這種依賴各級政府實施的扶貧強化了扶貧管理的科層制,導致農村治理“內卷化”。因此,需要建立扶貧瞄準機制,并賦予農民分配權利。張志偉和馮曉晴(2018)[2]在立法層面指出,扶貧立法要在地方立法實踐的基礎上,重點明確“扶持誰”的問題。扶貧對象識別是扶貧工作的基礎。國家要制定統一的扶貧標準,劃定扶貧對象的范圍,建立可參考性的扶貧對象識別辦法。以上學者在精準扶貧的政策執行層面和法律依據上為完善精準識別工作提出了建設性意見。明確具體扶貧對象,精準識別貧困程度,成為精準扶貧工作區別于過去扶貧工作的重要標志。
在精準幫扶角度,陳畢雪(2015)[3]認為應當繼續推進“六個到村到戶”方針政策,推動貧困人口持續有效增加收入,調動貧困群眾脫貧積極性,以實現穩定脫貧和全面小康。仲建國(2016)[4]認為實現農村居民“住有所居”的問題,是農村扶貧工作得以推進的保障,也是實現城鄉統籌的重點。以城市廉租房模式為借鑒的“巴山新居”工程,就是調整了農村危房改造的思路,通過實行農村廉租房政策,持續改善了農村貧困地區的住房條件和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總結來看,學者們對精準幫扶的研究落腳點都放在了“實”字上,要求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立場進行幫扶,要求幫扶的程序符合實際、落到實處。針對特定幫扶群體,蔡明祥等(2016)對三峽庫區興山縣峽口鎮普安村的農村移民為對象進行研究。鄧小海(2015)從旅游扶貧角度分析了相關主體旅游脫貧的過程。以上學者進一步突出了精準幫扶的“準”,提高了主體針對性、行為針對性和政策建議針對性。
在精準管理過程中,潘帥(2016)認為我國現行的扶貧機制不健全,其一是貧困狀況評價體系不精準,其二是缺乏對扶貧干部的正向考核激勵機制,其三是扶貧資源傳遞內耗過大。李菲等(2019)發現,府際網絡因爭奪資源歸屬秉持“策略主義”,忽視扶貧政策的實際產出;議題網絡影響力較弱,主體性地位喪失,致使扶貧政策執行精準力度有限。張愛瓊(2016)以云南省X 鄉的調研結果為依據,分析了精準管理存在問題的原因。趙祖斌等(2018)對湖北省Z 縣進行典型調查實證分析。以上都是以“解剖麻雀”的方式,由點及面,對精準管理的模式進行改善性分析。在這種趨勢下,我國精準扶貧機制也逐漸從“原則正義”邁向了“程序正義”,希冀切實阻斷返貧因子的運作路徑,進而實現脫貧效果的長期性和可持續性。
3.2 脫貧持續性研究
隨著精準扶貧實踐不斷推進和相關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們將精準扶貧過程進一步細化為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4 個維度,越來越多地引入對脫貧可持續性的思考,可將這個階段稱為脫貧持續性研究階段。
靳永翥等(2017)認為各級政府應當轉化自身的角色,積極發揮“能促型”角色的作用,尊重貧困者的主體性地位與訴求,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規范自身行為。近年來,以西峽縣石界河鎮“傳樹爭做”先模人物表彰暨“志智雙扶”巡回宣講為代表的一系列脫貧典型宣傳、以寶華鎮噶他村精準扶貧與貧困退出“回頭看”為代表的扶貧長效考核機制建立等事例,都旨在通過扎實開展“轉作風走基層遍訪貧困村貧困戶”“抓典型樹榜樣求帶動”的內生動力激勵活動,從思想、制度等方面徹底阻斷返貧因素運作路徑,強化扶貧責任落實,進而實現可持續性脫貧目標。
4 扶貧經驗總結與鄉村振興展望
一是適當減輕基層負擔,保障工作穩步開展。在民眾眼中,基層行政單位是具體政策發布的權威,也是個體需求未被滿足后進行申述上訪的首要責任人。這使得基層在發展實踐中經常面臨著“雙重壓力”。由于科層制、壓力制、行政發包制以及條塊管理的存在,多個方面的任務通過科層體系一級一級下放至基層,同時通過多項考核以壓力制形式監督基層執行。這種壓力體制又在倒逼基層形式主義的發生,最終導致各項安排難以達到預期成效。因此,應當積極營造關愛基層的工作氛圍,明確各級職責,簡化上報事宜,健全聯動管理,鼓勵綜合性考核,不斷夯實基層工作力量,提升基層干部素養,保障基層工作穩步開展。
二是尊重基層發展主體地位,客觀評估發展政策的科學性。結合扶貧實踐發現,某些地方為了避免村干部腐敗,將貧困認定權力賦予了縣一級,表面看排除了村干部“扶人唯親”的隱患,但由于評定工作量大、時間緊,縣級機關很難真正了解貧困群體的實際情況,只能單看表面,文件、數據代表一切,嚴重背離扶貧政策的科學化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扶貧是一個存在風險的舉措,許多地區發起產業扶貧沒有遵循市場規律,只是單純強調政府號召以及行政力量引導,而一旦產業形成虧空,往往是政府財政“買單”。因此,應當充分尊重基層的主體地位,由村干部結合本地實際情況開展工作。對于正在實施的發展措施,應當進行績效檢驗,及時調整被實踐證明無效的措施,避免資源浪費,將工作落到實處。應當進行綜合性考核。鄉村振興政策落實績效考核體系是一套綜合性的評價體系。鼓勵對基層工作展開多部門統一考核,明確考核綜合指標,減緩基層壓力,有效保障基層運作效率。
三是弱化民眾福利意識,激發內生動力。近年,在多地扶貧政策落實過程中,不少貧困群體產生了較強的特殊利益群體意識,對政府產生嚴重依賴性,甚至會因政府不滿足其不合理需求而產生怨念,阻礙扶貧工作正常穩定運行。因此,在鄉村振興實踐中,應該樹立民眾自身發展的責任意識,發揮主觀能動性,實現物質、精神的綜合發展。區分對象的異質性,有針對性地實施方案,調動民眾的主動性,保障措施有效實施。
四是促進脫貧指標多元化。此處所說的多元化,不僅是指標種類多樣,同時強調多元指標在達成脫貧目標結果判定上權重的均衡性。當前,在重視物質脫貧的基礎上,應當繼續提升人類發展指數和多維貧困指數的考察權重。增加在“素質脫貧”“教育脫貧”“信息脫貧”等方面的關注程度,進而激發脫貧主體的內在能力。在脫貧指標的確定上,應充分考慮到心理狀態、職業生存技能和家庭關愛等方面的改善,充分尊重貧困人口的理性選擇、能力運作、主觀感受等核心能力建設,實現全方位脫貧攻堅。
5 結束語
通過對精準扶貧政策過程的梳理和總結,形成了對鄉村振興戰略具有指導性意義的經驗。不少學者指出,鄉村振興戰略布局必將使精準扶貧進入新的階段,令新時代扶貧工作煥然一新,而從精準扶貧實踐中產生的寶貴經驗也必將在鄉村振興戰略布局之中迎來更大的應用契機,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城鄉統籌協調發展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