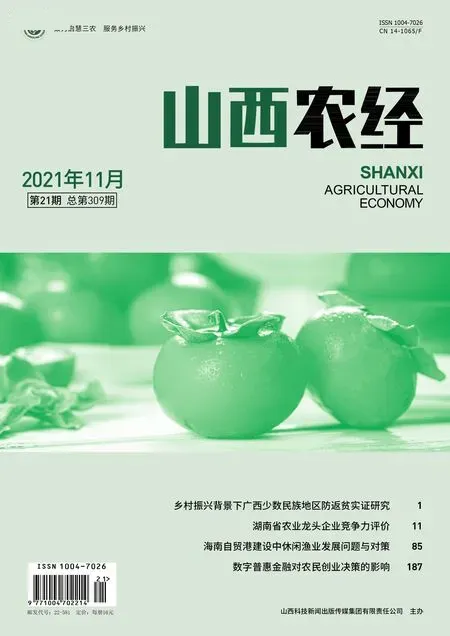貴州省農業生產責任制改革研究(1978—1980 年)
□陳麗娟
(安徽大學 安徽 合肥 230039)
貴州省地表破碎,巖石裸露,碎塊化土地分布在山上山下,農業生產條件差。由于長期的貧困,貴州省農民自稱為“干人”,即一無所有的人,他們一直盼望有個好政策,能填飽肚子,走上富裕的道路。
土地改革使貴州農村家家戶戶分到了屬于自己的土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增長。但人民公社化運動,使貴州省1960 年的糧食產量降到解放初期水平,農民遭受著饑餓的威脅。從20 世紀60 年代開始,貴州省一些偏僻邊遠地區開始長期秘密實行包產到戶的做法。無論上級提倡哪種形式的經營管理方式,當地都堅持著包產到戶,只不過是叫法隨著形勢不斷變化,“當上邊說是定額管理,他就是定額管理;上邊說是大寨工,他就是大寨工;上邊說是包產到組,他就是包產到組”[1]。當地人將這種把耕地分給各家各戶包種的形式稱為“包坨坨”,被山區農民視為擺脫饑餓、求得生存的辦法。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貴州省糧食產量從未超過500 萬t,“五年增產,六年減產”,平均每年只遞增1.4%[2]。糧食長期匱乏,基層干部管理不善,干部多吃多占,社員勞動“人情工分”“荷包賬”盛行,農村出現“生產無責任,你混我也混”的狀況。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貴州省的農村形勢并未好轉。“建立大寨縣”口號下盲目發起向生產大隊核算過渡,“以糧為綱”口號下的“三地代耕”制度仍在延續。到1979 年,全省人均口糧僅177.5 kg,比全國平均水平低31%,36.7%的生產隊人均口糧低于150 kg,僅30.5%的生產隊高于200.5 kg。人均分配收入46.41 元,位列全國倒數,低于全國水平81.4%[3]。
1 貴州省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復萌
面對貴州省窮困的形勢,1978 年3 月,貴州省召開了省、地、縣三級干部會議,討論修改農村經濟政策的提綱,提出只能以臨時作業組來組織生產,不能實行聯系產量責任制。因農村形勢并未好轉,同年10 月,貴州省委頒布《中共貴州省委關于進行農村若干政策問題調查的意見(修改稿)》(簡稱“省委十條”),進一步放寬農業政策。文件規定生產隊可以實行聯系產量的生產責任制,允許生產隊根據自身的規模和生產內容,合理組織勞動力,建立常年的、專業的、暫時的、季節性的作業組,為日后生產隊實行“五定一獎”責任制開了綠燈[4]。“省委十條”放松對聯系產量責任制的捆綁,使得實行聯產責任制取得了合法依據,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群眾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為“頂云經驗”的誕生創造了條件。
“省委十條”放開了實行聯產責任制的口子,同時1978 年11 月11 日,《貴州日報》公開報道了關嶺縣頂云公社因實行“定產到組,超產獎勵”增產的經驗,還以編者按的形式刊登了頂云公社部分干部座談會紀要。該報道公開肯定貴州農村實行的責任制,深入人心,被稱為“不是紅頭文件的‘11 號文件’”。報社編輯部還收到貴州各地寄來贊成頂云公社做法的信,反映了廣大農民的心聲。
但是,此時貴州省委并未明確表態支持《貴州日報》的報道,并表示出報社觀點不能代表省委觀點的態度。1978 年12 月底,在安順地區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議上,省委一位領導同志在聽到實行“定產到組”出現的一些問題后,便指示地方緊急剎車。這一意見傳到基層后,剛剛興起的多種形式責任制便面臨夭折,一些對實行“定產到組”思想不通的干部不再讓群眾實行“定產到組,超產獎勵”管理方法,部分地區則開展了對“定產到組”的批判,一些猶猶豫豫的干部則“把穩”起來,“不點頭,不搖頭,今天站得遠,明天跑得開,當起甩手掌柜”[5]。省委與基層群眾對“頂云經驗”的不同態度,為日后雙方“頂牛”埋下了隱患。
2 生產責任制的突破與農民“頂牛”
2.1 聯系產量責任制曲折發展的經歷
1978 年12 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用實事求是的精神鼓舞了全國各地的干部群眾。為支持農業發展,貴州省委貫徹學習中央兩個農業文件。尤其是中央兩個農業文件對實行聯系產量責任制的許可,以及《貴州日報》對于“頂云經驗”的報道,改變了貴州省農村生產隊經營管理的主要形式,使聯系產量責任制在貴州農村普遍實行。貴州省農村不再“藏著掖著”,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在貴州省蔓延開來,貴州省委內部對聯產責任制的責難在表面上慢慢平息下去。
1979 年初,原國家農委發布《關于農村工作問題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紀要》提出“允許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實行包產到戶”,貴州省委擔心引起連鎖反應,要求對這一指示暫緩執行,表現了省委對聯產責任制搖擺不定的態度。1979 年3 月中旬,《人民日報》刊登的“張浩來信”,表示要強行糾正“包產到組”的錯誤做法。貴州省委立即指示《貴州日報》全文轉載這篇報道,還通過電話布置各地縣委認真領會。而當《人民日報》在3 月底刊登安徽省農委的來信,肯定了“包工到組,聯系產量”的計酬方法,貴州省委卻只談“定產到組”引起的問題,給人留下要糾偏的印象。此時,貴州省委內部對于放開農業生產的認識并不統一,實行聯產責任制的生產隊與日俱增,而省委對此采取回避的態度,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對。直到十一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夕,貴州省委領導才在地委書記會議上承認聯系產量責任制的積極作用[6]。
2.2 “雙包”責任制的擴散
在貴州省委態度尚不明朗的同時,基層有些地方不滿足于實行“五定一獎懲”,而是更進一步,秘密搞起“包產到戶”,農村形勢發展開始不受省委控制。面對這種超出預期的突發狀態,為穩定生產隊統一經營,省委在1979 年5 月和7 月兩次省委會議上,強調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要求優化農業內部種植結構、培訓基層干部、推廣“烤煙加油菜”及調整農林牧比例關系,企圖通過以上方式來穩定生產隊統一經營的模式[7]。
1979 年9 月,貴州省委發布《關于執行中央兩個農業文件的情況和今冬明春農村工作安排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肯定了農村實行的“包工到組,聯產計酬,超產獎勵”,規定處于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經縣委批準后,可以實行包產到戶。《意見》又強調對一些滑向以組核算、分田單干的生產隊與不經過縣委同意而搞包產到戶的,要做通思想工作,爭取回到以隊為統一核算的形式[8]。
貴州省委發布的《意見》不再給包產到戶戴上“單干”“資本主義”的帽子,而是給包產到戶開了個口子,但實質上是“在同群眾‘拔河’中,先讓了一步,然后又堵上一道壩”[9]。省委的原意是希望以自身的退一步換取群眾的退讓,但是結果卻適得其反。
農民在嘗試到包產到戶帶來的巨大改變,生產飛增后,再退回原來的生產形式事實上已不可能。群眾不再滿足實行“定產到組”后組內仍存在“小呼隆”“二鍋飯”與個人責任不明確的現象。在省委下發《意見》后,反而成為群眾包產到戶的合法依據。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自1979 年秋收到1980 年春耕在貴州農村普遍實行,其蔓延方式達到了頂峰。
2.2.1 省委指示糾正包產到戶、包干到戶
面對農村自發推廣實行的包干到戶和包產到戶,貴州省委經過討論決定進行糾正。1979 年9 月貴州省委發布《關于認真搞好今年農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工作的意見》,強調要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制度下的統一核算與分配,要求在秋季分配中糾正夏季預分中以組分配的隊。要發動群眾把實行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生產隊糾正過來[10]。1979 年12 月,貴州省委發布了《中共貴州省委關于搞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決定》,給實行“雙包”責任制的生產隊作了明文規定,文件要求“不許以作業組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許分田分土單干,不許超出中央規定的界限搞包產到戶”,省委提出“三不許”的禁令來糾正生產隊的做法。面對貴州省委硬性的規定,“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引發的熱潮面臨被澆滅的可能。
1980 年1 月,省委轉發《貴州省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紀要》要求各地區盡快落實“三不許”規定,早日制止與糾正違反規定的生產隊。《紀要》再一次表明貴州省委“糾偏”的強硬態度,全省派出工作組到農村去糾偏,結果是工作組遭到了大部分農民的抵制,部分農村對省委強行糾偏的行為不滿,加劇了農村與省委的對抗形勢,出現了“頂牛”的局面[11]。
2.2.2 從“三不許”到“停止糾偏”,省委深入農村調查
貴州省委派工作組下去“糾偏”,結果卻是農民與工作組“頂牛”,導致工作組出現“糾而不正”“越糾越被動”的局面。有的生產隊舉辦生產隊長學習班,有的干部害怕搞“包產到戶”被批斗,對經營管理放任自流、不管不顧。一邊是上面要“糾偏”,堅持集體經濟,一邊是農民要分組、包產,省委與農民對包產到戶的對立態度導致了農村出現農民罷耕現象,秋種面積急劇縮小,棄種的“泡冬田”與棄耕的“板田”隨處可見。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為緩解農民與省委對抗的緊張局面,委派省委書記王朝文深入黔北農村,調查農村實際情況。王朝文在遵義調查21 d 后,還到川南考察農業生產,發現川南地區也在瞞著上面搞“包產到戶”。回到貴陽后,在1980 年3 月12 日池必卿主持的書記會上,王朝文介紹了遵義地區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情況,說明“雙包”責任制對農業的積極作用,認為“雙包”生產責任制正在農村快速蔓延,農民對于上面的“糾偏”是不支持的態度,如果硬要強行糾,只會導致生產下降,恐怕1980 年的春耕搞不上去。在允許農村搞包產到戶是否要請示上級而意見不一時,池必卿最終拍板決定,“不要請示,如果省委干錯了,由他自己負責”,最后,大家達成一致,立即停止“糾偏”[12]。
1980 年3 月17 日,貴州省委召開由王朝文主講的電話會議,宣布“承認現狀,停止糾偏”,要求不要強行同農民“頂牛”,號召各級黨委深入農村調查,為解決問題做下一步準備。從1980 年4 月上旬到5 月上旬,為統一省委思想認識,池必卿同志帶頭深入農村調查,常委也到各地區進行農村調查。
2.2.3 省委常委會的召開
在農村調研回來后,池必卿同志學習了中央下發的《鄧小平、趙紫陽、姚依林同志有關政策要放寬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姚依林在《講話》中說:“像甘肅、內蒙古、貴州、云南這些調入糧食多的省份可不可以考慮在政策上搞得寬一點,讓他們能做到糧食自給,減少國家糧食投入。對經濟落后、生活貧困的地區可以實行包產到戶。”鄧小平在講話中贊成姚依林同志的意見,提出對這些落后的省份,政策要放寬到使他們可以因地制宜,發展特點[13]。
中央領導人關于放寬農業的講話,尤其是點到了貴州,給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心里交了底。貴州省委立即召開常委會,由去農村調查的同志們以半天工作、半天匯報的形式輪流發言。池必卿在會上說:“省委應自覺地領導好這次貴州農業生產關系的調整,主動放寬政策,再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了’”[14]。會上,許多常委沖破思想束縛,要求擁護鄧小平、姚依林的講話,根據貴州省實際情況因地制宜發展有利于農業增長的生產責任制。提出生產隊規模可以劃小到10 戶,推廣定產到組、責任到勞的聯系產量責任制,各地負責人不強糾單干,爭取把單干的農戶引導成包產到戶[15]。會后正式發布《關于立即制止糾正包產到戶、分田分土單干的錯誤做法的通知》,要求在秋收前穩定生產隊實行的各種經營管理形式,允許農民自主選擇合適的生產責任制。
2.2.4 省委38 號文件的出臺
貴州省委常委會議后,省委專門組織了由池必卿領導、李菁主筆的起草小組,在1980 年7 月,制定并發布了省委38 號文件。省委38 號文件允許部分生產落后、生活窮困的生產隊可以實行包產到戶,特別是允許一些實行包產到戶有困難的社隊可進一步實行包干到戶[16]。省委38 號文件徹底打破了“三不許”禁令,還省去了“統一計劃”“統一分配”的形式。文件下發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迅速成為貴州農村主要實行的生產責任制。
放寬農業生產責任制以后,貴州省農村形勢變化巨大。1980 年11 月,全省98.1%的生產隊落實了責任制,各種責任制形式占比如下,包干到戶60.8%,包產到戶18.6%,定額管理10.8%,專業承包、聯產計酬9.2%[17]。
1980 年,貴州省糧食總產超過64.8 億kg,是建國以來第二個高產年。入倉1.45 億kg 油菜籽,出欄生豬460 余萬頭,均創歷史最高紀錄。相比于1979 年,農民人均占有糧食增長16.3%,達到282 kg,人均純收入增長123.1%,達到167 元[18]。
3 貴州省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特點與現實啟示
3.1 貴州省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的特點
貴州省農業生產長期受“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形的限制而發展緩慢,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改革改變了貴州省農村落后的面貌,使農民生活發生了轉變。貴州省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建立過程,有著鮮明的特點。
(1)起步早,發展快。《貴州日報》于1978 年11 月報道“頂云經驗”,帶動了全省農業生產責任制的轉變,使“包產到組”在農村普遍推廣開來,并進一步推動了包干到戶、包產到戶在貴州省的發展。
(2)輻射廣,包干面大。貴州省干旱、洪澇、低溫、冰雹、農林病蟲等各種災害幾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發生。貴州省群山林立,平地少,可耕地面積偏僻、分散,屬于開發較晚的多民族高原山區,生產水平低,農村人口貧困面大,集體經濟無法使分散的山區農民提高生活質量,農民對長期低產的集體勞動生活喪失了信心。因此,農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快速蔓延,是大勢所趨。
(3)群眾主動推動政策發展。長期的貧困使農民群眾偷偷實行包產到戶,經歷工作組“糾偏”后,農民以棄耕相對抗,與省委“頂牛”。農民為解決溫飽問題,需要實行有利于自己的生產形式,以過上更好的生活。如遵義市綏陽縣上坪公社底壩大隊沉底生產隊,自1979 年秋實行包干到戶后,出工“一條龍”的現象不再出現,干活“一窩蜂”的場景逐漸消失,因此計酬“一拉平”的方法不再適用,1979 年糧食總產82 600 kg,比1978 年增長18.3%,人均增產71.5 kg,超額完成國家統購派購任務[19]。包干到戶在提高社員生產積極性的同時還解決了溫飽問題,改變了社員們懶散的出工態度。
(4)領導積極制定政策,保障農業生產。以池必卿為代表的省委領導親自到基層進行調查研究,了解農民的真實生活狀況,推動省委制定出符合貴州省實際的方針政策。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與失誤,省委還進行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堅持走從實際出發的群眾路線。
3.2 啟示
考察貴州農業生產責任制實行的歷史,可得出深刻的啟示。
(1)生產關系要與生產力的發展相匹配。長期以來,農民對集體經營失去信心,為擺脫貧困,填飽肚子,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原因迫使農民選擇以包干到戶為主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包干到戶在貴州省普遍推廣符合現實,符合農村實際發展的趨勢。
(2)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農民群眾通過實踐認識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符合貴州省實際的,從允許實行“五定一獎懲”到“雙包”責任制的確立完善,都得力于各級黨委尊重和支持農民創造。深入實踐進行調查研究,不從政策層面單方面為農民作決定,是新時代農村改革尊重農民首創精神的必要前提。
(3)規章制度應該日臻完善,為政策的正確執行保駕護航。地域差異、城鄉差別的巨大,要求新農村建設必須切合實際。當前,中國農村與城市的差異大,農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空巢”化現象嚴重,新農村的建設決不能追求外觀形式的整齊劃一,還要建設農村產業化發展,吸引人才留在本地,探索本地優勢,合理規劃長期發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