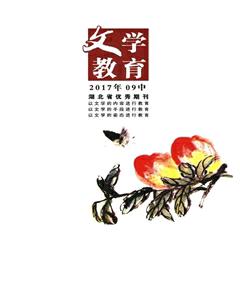中學生課外閱讀現狀探討與對策
李婷婷
內容摘要:隨著新課改的逐步實施,中學語文的教學體系也得到了很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人們忽視課外閱讀的問題,提高了語文教學質量和學生的綜合素質,但是在一些方面還是存在著問題,如課外閱讀意識薄弱、閱讀內容淺顯和方法單一,本文從以下方面提出了一些解決對策。
關健詞:中學生 課外閱讀 現狀 對策
對語文這門學科來講,需要不斷的積累來豐富自己的知識儲備量,而課外閱讀就是積累知識的重要手段。課外閱讀不但可以豐富學生的知識面,開闊學生的視野,活躍學生的思維,還可以對學生成長提供一定的指引作用。但是目前存在的現狀就是中學生在課外讀物的選擇上以及學習策略上都存在誤區,本文簡述了一下解決的對策。
一.課外閱讀的重要性
閱讀問題一直是學校教育的難點,并且隨著新課改的實施,對語文課程提出了新的標準,要求閱讀對學生在學習知識能力、學習方法、價值觀等方面都起到良好的提升作用,為了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課外閱讀的地位也得到了肯定。
課外閱讀是對課堂上知識的鞏固和延展,讓學生掌握基礎知識,并對學習的知識進行復習,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同時也是自我學習能力的培養,讓學生通過課外閱讀來鍛煉自我學習的能力,并開放自己的思維,形成固有的學習習慣。
二.初中生課外閱讀的現狀
1.課外閱讀時間少
在當下的應試教育背景下,中學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課后作業上了,導致沒有時間來進行課外閱讀,同時很多家長和老師深受固有的思想所影響,把考試分數當成衡量一個學生的主要指標,認為學生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升自己的考試成績,認為課外閱讀對提高學生考試分數沒有幫助,沒有必要花大量時間來進行課外閱讀,所以對課外閱讀不重視甚至排斥[1]。
2.沒有閱讀習慣
由于中學生在閱讀學習上缺乏一定的自主性和規劃性,導致學生在閱讀方面比較盲目,達不到提高閱讀能力的效果,并且由于家長和老師的不重視,學生也是漫無目的的看看而已,態度散漫和無所謂,使其閱讀徒有其表,并沒有對有用的知識進行摘抄和標注,導致沒有將書中的知識吸收轉化成自己所用的知識,也對閱讀沒有產生興趣和養成閱讀習慣。
3.盲目選擇課外閱讀書籍
課外閱讀應該按照學生的興趣愛好來進行選擇,但是考慮到中學生的年齡和認知水平的因素,導致在閱讀書籍的選擇上都比較盲目和片面,甚至大多數學生選擇一些娛樂雜志、言情小說作為課外閱讀書籍,不但起不到學習的效果,還會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和行為舉止[2]。
三.提高初中生課外閱讀的對策
1.樹立正確教育觀,鼓勵學生課外閱讀
首先家長和老師要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念,明白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分數,并樹立良好的閱讀觀,認識到課外閱讀對學生的重要性。減少一定量的課外作業,來為課外閱讀提供點時間,并鼓勵和監督學生進行課外閱讀,讓學生明白閱讀對自己的綜合素質和情感方面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并且可以組織一切具體的活動,來豐富課外閱讀且帶動學生課外閱讀的主動性。
2.培養良好的課外閱讀習慣
大多數的學生在課外閱讀時,往往都是流于表面,對書中的內容沒有進行認真的思考和學習,因為在課外閱讀時,需要老師在一旁指導,比如可以組織讀書征文競賽、手抄比賽等活動,來提高大家對閱讀的積極性,還可以結合網絡來全面的展示書籍的內容,增加學生對閱讀的興趣,還可以設置黑板報,讓大家寫下自己閱讀時最喜歡的語句來和大家分享,讓每個人都能參與其中,使其養成更好的閱讀習慣[3]。
3.選擇適合的課外閱讀書籍
老師需要考慮學生的年齡以及閱讀能力的因素,來為學生挑選適合的閱讀書籍,這樣才能起到提升學生綜合素質,形成健全的價值觀體系。比如老師可以推薦學生閱讀一些名著,豐富學生的人文素養,還可以結合教學內容來推薦書籍,兩者之間相互融合,使學生對所學習的知識有著更好的理解,并且要豐富閱讀書籍的選擇性,避免學生產生枯燥的心理,影響閱讀的效果。
課外閱讀在當代是越來越重要了,不但對學生的語文水平以及綜合素養起到提高的作用,還對提升語文教學質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需要采取相應的策略來解決課外閱讀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以此更好的讓課外閱讀發揮其應用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陳碧卿.中學生課外閱讀現狀分析與對策[J].中小學圖書情報世界,2006,06(10):11-15.
[2]趙彤.初中生課外閱讀現狀及其對策研究[J].亞太教育,2016,12(18):33.
[3]李蓓.淺談中學生課外閱讀的現狀及解決對策[J].亞太教育,2016,11(21):4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