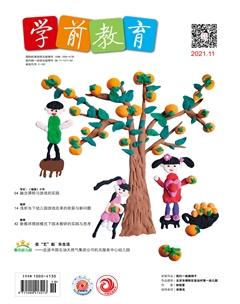淺析當下幼兒園游戲改革的收獲與新問題
王芳 曲寧
近些年來,隨著“深刻的兒童游戲革命”1——安吉游戲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各級游戲實驗區和游戲實驗園建立起來,幼兒園游戲改革進入到一個發展新階段。作為被卷入的“實踐者”,我們在幼兒園里深入踐行“真游戲”“自主游戲”理念,收獲成功的喜悅;作為理性的“研究者”,我們觀摩、學習、反思,冷靜直面新問題。
幼兒園游戲改革的收獲
幼兒園游戲改革的收獲是全方位的,既有理念上的轉變,又有實踐操作的創新。具體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尊重兒童、確保游戲的自主性成為主流觀念
游戲的“快樂”“自主”特質被廣泛認同,成為幼兒園判斷游戲質量高低的重要標準之一。反對“假游戲”倡導“真游戲”,尊重兒童對游戲主題、內容、同伴的選擇,要求教師盡可能放手、允許幼兒試誤、根據幼兒的建議和想法來推進游戲的做法在幼兒園里普遍可見,有力地改變了以往高權威、高控制、低情感的游戲格局。
游戲環境創設和材料提供煥然一新
幼兒園游戲環境安全,材料豐富且操作性強,給予幼兒更多體驗自我力量、合作、創新、提升學習品質的機會。這一點在戶外表現得尤為明顯。傳統游戲場、現代游戲場和挑戰性游戲場并存,各種類型的低結構材料(如滾筒、輪胎、積木等)靈活地和幼兒園的自然環境結合起來,促發了幼兒豐富多樣的游戲內容和形式。他們在水池里嬉水,在沙土地里和泥,在樹木上爬上爬下,能生火做飯,能采摘果實、飼養動物……忙得不亦樂乎,游戲真正地變成了他們的“工作”。
教師和幼兒的互動格局得以重塑
非對稱相倚是傳統師幼互動的主導形態2,即教師根據自己的計劃發出施動行為,幼兒跟隨做出反應。當前的游戲互動仍然是非對稱相倚,但施動方在大部分情況下已由教師轉向了幼兒。在“閉住嘴、管住手”后,教師和幼兒開始一起平等地探究、愉快地游戲。“幼兒在前,教師在后”已成為許多教師介入、指導幼兒游戲的基本原則,“我這樣干預合不合適”這個原本較少探討的內容成為許多教師反思的主題。
從關注教轉向關注學,重視幼兒的游戲經驗
幼兒在游戲中學到了什么?怎么才能知道幼兒的真實經驗?……為了更好地了解游戲的實際效果,教師們創生出許多行之有效的辦法。他們通過拍照、錄像記錄幼兒的游戲表現,借助游戲故事、游戲案例挖掘“哇”時刻和“尋常”時刻背后的意義,體現出身為“反思型實踐者”的專業素養。與之相匹配的是,如何進行游戲觀察,如何解讀幼兒的游戲行為,一直占據著幼兒園培訓、教研的中心位置。
幼兒園游戲改革面臨的新問題
在收獲上述進展的同時,幼兒園游戲改革也面臨著若干新問題。原因在于,影響游戲質量的因素多種多樣,具體到每個幼兒園都有所不同。如果不能將先進的游戲理念與幼兒園的具體實際有機結合,就會停留于改革表層而無法深入。
戶外游戲研究占據壓倒性優勢
近年來,幼兒園戶外游戲是各種現場展示、觀摩、交流的重點。戶外活動時間每日2小時,遇到不良天氣還會減少,更多的游戲應滲透在一日活動中,因為“一日活動即課程”。而目前幼兒園游戲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戶外游戲上,相對忽略了區域活動、生活活動、集體教學游戲的深入研究。同時,許多幼兒園在戶外劃分的區域眾多,但是大都是簡單的排列組合。每個區域要發展幼兒的哪些素養、各個區域之間如何相互配合、戶外區域的活動是否有層次、有變化,還缺乏深入的考慮。
室內區域游戲被忽略
與上述問題密切相關的是幼兒園對室內區域游戲的漠視。幼兒在室內生活的時間遠遠長于戶外,各類室內區域游戲具有獨特的價值,而且對區域游戲的研究本來就是以往許多幼兒園游戲研究的亮點所在。一些幼兒園只關注戶外,室內游戲環境、材料投放、教師指導和戶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有的干脆把室內區域全部機械地搬到戶外,走向另一個極端。
借鑒模仿他人過多,反躬自問過少
幼兒園的研究是以教育教學中遇到的問題為研究對象,以解決實際問題,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為目的的“行動研究”。幼兒園的游戲研究同樣如此。幼兒園游戲實踐中遇到的問題有些具有普遍性,有些則是本園特有的。借鑒他人經驗做法解決的是普遍性問題,要解決自己的特殊問題則需要全體教師發揮智慧共同創造。比如,“假游戲”可能是幼兒園游戲實踐中的普遍性問題,但它絕不是每個幼兒園的全部問題。退一步講,即使幼兒園普遍存在“假游戲”,但在一些幼兒園或許是主要問題,在另一些幼兒園可能只是小問題,因此沒有必要一窩蜂地去解決“假游戲”問題。
低頭做多,抬頭看少,缺乏批判性思考
任何行為背后都有理論的指導,無論是否被意識到,或者能否明確說出。很多幼兒園教師在游戲改革中做得很多,但受限于理論水平,批判性思考較少,即使心中有不少困惑,也不愿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大家比較熟悉的“幼兒在前,教師在后”這句話為例。
在兒童發展與教育的關系上,大致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觀點:(1)教學和發展是彼此獨立的,教育對發展不起作用;(2)教育要跟隨發展,不能超越幼兒的發展階段,這種立場的代表人物是皮亞杰,個人認為這也是“幼兒在前,教師在后”的主要理論來源;(3)教學要走在發展的前面,引領發展,這是由維果茨基提出的觀點。每種理論體系都有其適用范圍,單獨使用某一種理論是片面的。我們應該去探究游戲中的教師何時在前,何時在后,何時與幼兒并肩,而不是僅僅關注“幼兒在前,教師在后”而忽略了其他選擇。卓越的教師知道教師主導和兒童主導同樣重要;不管是兒童主導的活動,還是教師主導的教學,對兒童來說,只有能夠讓他們深度學習的活動才是最重要的教育活動3。在這方面,集合了皮亞杰、維果茨基、杜威、生態學等理論精華的瑞吉歐教育體系對教師的角色定位——“平等中的首席”可以給我們另外一種啟發。
“閉住嘴,管住手”同樣如此。什么時候該閉、該管?什么時候不該閉、不該管?不管的時候教師該做些什么?管住了之后教師應該做些什么?……不顧具體游戲情境而簡單地要求教師不說、不管,只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和行為上的懶惰,于游戲無益。
加拿大教育學者邁克·富蘭認為,“問題是我們的朋友”。面對這些問題,幼兒園最需要的是進一步明確本園游戲改革的起點(要解決幼兒游戲中的哪些問題)、愿景(想讓游戲和幼兒表現出什么狀態),進而在適宜理論的指導下找準自己的突破點,創新改革途徑。對實踐改進來說,這才是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程學琴.緣起與發展:一場深刻的兒童游戲革命[J].學前教育,2019(3).
2.劉晶波.社會學視野下的師幼互動行為研究[M].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216-226.
3.Carol Copple等主編,劉焱等譯.0-8歲兒童發展適宜性教育[M].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2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