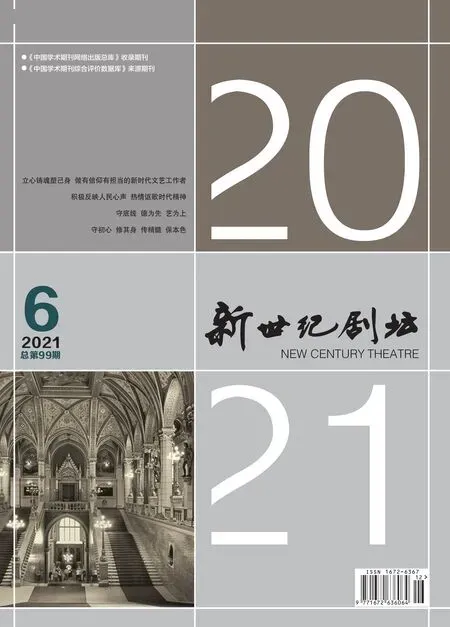你還有得選嗎?
——女性視角下的話劇《裁·縫》
文/王茸茸
93歲的老顧回望自己“廉價的一生”,囈語般地重復:我也不清楚我在說什么……其實,她婚姻里的雞飛狗跳一地雞毛,被歷史裹挾、被家庭操縱的無奈、她的隱忍不甘及為自己人生“第一次做出的自主選擇——離婚”,并以此為切入點鋪開的庸碌瑣屑的這些故事,大家都懂。生和死,苦難和蒼老,都蘊藏在每一個人的體內,總有一天我們會與之遭逢。
話劇《裁·縫》是適合成年人觀賞,特別是多數女性朋友樂于接受并極容易引起共鳴的小劇場話劇。
一
身為女性編導無疑想探討很多話題:婚姻、衰老、生死、自我價值等,雖努力克制“情緒化”的表達和聲討,但是戴著皮手套刷馬桶的老顧言語中充滿怨念的開頭,已經奠定了“女性化”視角的基調。編創團隊歷時一年半對100多對老人進行采訪,創作之初可能只是想客觀地呈現老年群體的生活和思想狀態,引發社會的關注,特別是年輕人(子女)的重視。我猜想,編導也許想要避免“女性創作”的標簽,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從開頭到結尾,我看到了熟悉的中國母親、妻子、奶奶和鄰居大嬸的縮影。其實,同樣身為女性的我也時常反感那種“女性”標簽,但是又總難以走出這種局限性。
女主是一位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某一個”中國女性。她前73年都是“被安排,被通知”,沒有人“問過我愿意嗎”,經歷并遺憾,充滿無奈和幽怨。“被通知”是眾多女性的生活境遇,尤其是步入婚姻家庭、身兼多重角色的大多數,“某一個”的女主在舞臺上替大多數“絮叨”著這樣被動的一生,明了對自己人生的束手無策。
為老吳“尿不直”刷馬桶刷了43年,忍受了43年尿臊味和煙味,坐在破舊的縫紉機旁的孤獨的夜晚,老顧突然想明白了:我要擺脫這種生活,我要離婚。“離婚是我這一輩子唯一自己能做主邁出的一步。”可是,然后呢?她為老吳租了就近的住所,瞞著孩子和鄰居,她坦言“我也不清楚為什么要這樣做”,可能是內心深處害怕被輿論指摘吧。此時,正在鬧離婚醉酒歸家的兒子小吳做出了明確的解答“我在外奔波養家糊口,她一家庭主婦,呆在家里帶帶孩子,還有什么不知足的?還要離婚?”……已經悄悄離婚的和處于離婚前奏的兩代人看似不同維度的對話,實則巧妙地直指婚姻與人性。這是男性視角的理解,也是男性看待家中妻子的普遍心態。
透過醉酒的小吳,我看到的不是男性們酒氣熏天的“自大”,而是已婚女性的濃濃恐慌與不安,還有對偶爾冒出“自我”追求的愧疚與壓制。“這么安穩,還有什么不知足的,還有什么挑剔的?”借男性之口說出了女性所想。社會上也存在眾多聲音:“為什么不結婚?不生孩子道德嗎?穿得花里胡哨是不是要去勾引男人啊?”……說到底,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一直都有,哪怕是高知女性的編創團隊也無法逃脫。越想平靜地表達,越想客觀地描述,越想擺脫“女性話語”的局限性標簽,反而刻意的痕跡更重,觀眾感受到了女性在臺上無法停止的絮叨和控訴。
二

話劇《裁·縫》劇照
宣傳冊子上寫的是“精致小戲”,精致應該是指極度還原年代感的舞臺陳設,而不是“小戲”的內容與表演。誠如一位觀眾這樣說:宣傳用了“精致”二字,其實不是的。拿吃飯來比喻吧,它更像離你家近,味道賊好,特便宜,從老板到服務員你都倍兒熟的一家小館子。想必這也是大家喜愛這部戲的原因之一吧。看這樣的小戲沒有思想包袱,好像不需要配合精致的妝容,也不需要提前做功課,觀眾坐在那里靜靜地聽和看就行了。可是,你又挪不開眼睛,生怕會錯過狹小的空間轉換中的任何一個細節,而實際上一直是平鋪直敘的,有點壓抑。觀眾在矛盾糾結中堅持著結尾的到來,還是全程平靜地看完,不得而知。你看,人生總是充滿兩難,不是嗎?
舞臺上演繹的人與事,是老顧的生活,也是你和我的生活。一方面,作為(主內的)女性,老顧想擁有自己的一番事業,卻又囿于家庭中瑣碎和略顯不堪的生活而不能實現理想。另一方面,當她鼓起勇氣提出離婚,試圖打破婚姻“枷鎖”及拋卻其一切附屬物后,卻發現自己仍不能如愿。她的縫紉機最終壞掉了,宣告了她“開裁縫小店”理想的徹底破滅,也意味著她青春與人生的完結。被時代無情“裁掉”的她,73歲時突然想要做回自己,極力想“縫補”千瘡百孔的生活。唯一一次自主的選擇,但是選擇過后,她的生活如何?她仍然沒辦法擺脫瑣碎的生活,仍然活在兒子和已經“被離婚”的老吳的復雜關系的牽絆下。這種細膩的心理活動與“習慣性”的細節較打動人,她以為的擺脫和抗拒,實則一直在順從。已經93的她還在不斷自問“我還有得選嗎”?
臺下的我們呢?這樣那樣的猝不及防,一步步邁向了與理想中截然不同的命運。我們極力想與生活的環境,與自身作斗爭,想逃離我們熟悉的有些臟亂的“小館子”,但是總是被牽絆著裹足不前。當有一瞬間真正離開了,以為要開始新的生活時,又放不下小館子的回憶和味道,怎樣選擇是所謂的正確?這樣的兩難,《裁·縫》也無解。也許,時刻想要擺脫充滿著年復一年擦不干凈的廁所味道和煙味的“小館子”,總歸會有些潦草和安于現狀吧。
生活充滿著殘缺,需要我們不斷地去“裁”和“縫”,去面對,去和解。“裁”還是“縫”,你有得選嗎?
三

話劇《裁·縫》劇照
舞臺上出現了很多具有年代感的道具和語匯,一方面驚嘆編導特有的女性細膩的鋪排,居然在一個半小時短暫的時間內傳達出那么多的信息,并涵蓋眾多的社會現象。可一方面又有所疑惑,“信息量很大的情況下具體的點就會被散掉”。不管什么東西,多了就顯得有些混亂,本該深入探討的話題容易局限于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而停留在表面,過于感性。就像一同觀演的同仁質疑:“馬桶、縫紉機、尿不直、充氣娃娃、撫養孩子、離婚、知足、養老院等大量的信息到底要傳達什么?很多點都觸及我們的生活現狀,但因生活瑣碎而生的積怨與分離,住房、擇校、戶口現實問題的引入,讓故事陷入情景劇一般的庸俗絮叨,多主題而少深度”。
有人說舞臺的形式沒有用好,寫意和寫實的結合不太到位。我倒覺得光影運用恰到好處。沒有出現的老吳始終投射著一雙眼睛在屋內,他在聽在看,在參與。早晨的陽光由暗到亮,透過窗欞灑在床鋪上,你來我往,熱鬧中有點點希望的意味;而夜晚路燈映射下的窗欞光影投射在屋內,愈顯孤獨清冷,適合人物的心靈獨白。光影變幻,日復一日。通過光影轉換梳理出人與人情感關系的分分合合、修補維系,十分契合“裁”與“縫”的標題。
不管這種光影形式在其他地方運用得多么泛濫,只要劇情需要,舞臺需要,只要用得巧妙、用得合理就是成功,適合的才是最好的。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也許沒得選也是一種選擇,管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