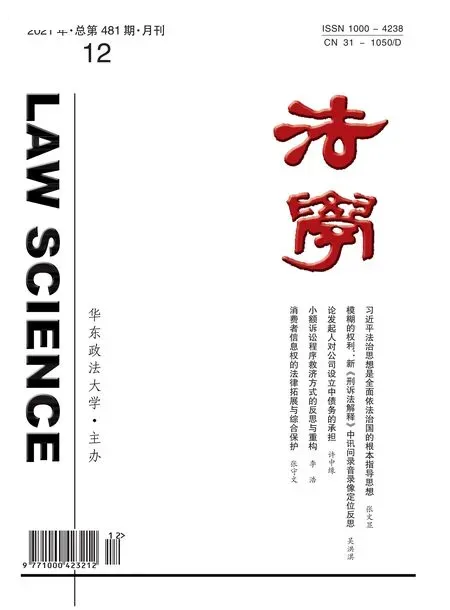論同案同判拘束力的性質
●泮偉江
一、問題的提出
同案同判的拘束力,指的是同案中前案對后案的拘束力。同案同判是否有拘束力,如果有,它的性質是什么,是法理學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多數法律實證主義者認為,只有實證法具有規范拘束力,而同案同判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只有道德上的說服力。〔1〕參見陳景輝:《同案同判:法律義務還是道德要求?》,載《中國法學》2013年第3期,第60頁。也有學者認為,同案同判是正確適用規則的自然效果,因此同案產生同判的拘束力,僅僅是一種認識上的假象。〔2〕例如,雷磊認為,“同案同判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依法裁判的另一種表達,或者說是其更為具象化的表達。”此種理解的核心論證思路是:依法裁判的核心含義是依規則裁判,而依規則裁判的具體效果,實際上就是“同案同判”,雷磊:《如何理解“同案同判”:誤解及其澄清》,載《政法論叢》2020年第5期,第34頁。
這兩種觀點都否認同案同判的拘束力,也就是認為,同案不可能產生同判的拘束力。這實際上就是在制度的意義上否定了同案同判的可能性。例如,按照依規則裁判論的邏輯,假如在客觀現象上確實存在著同案同判的事實或效果,那么這并非是“前案”與“后案”之間的某種“拘束”和“被拘束”的關系發揮了作用,而不過是兩個案子都各自依規則作出了正確的裁判,是規則的客觀普遍性帶來了同案同判的客觀效果。這是一種“重疊效果”,而非交互作用的結果。道德義務論的邏輯其實也與此類似,這種觀點認為,這是因為兩個案件中所涉及的內容的正確性本身保證了前案在道德上的說服力,從而啟發了后案作出道德上正確的判斷,保證了同案之間的“同判”效果。兩種觀點都強調“同案”之所以產生“同判”的結果,根本原因是前案與后案碰巧都“判對了”,是判決內容“本身的正確性”保證了判決結果的客觀一致性。只是前者強調的是法律上的正確性,而后者強調的是道德上的正確性。同時,兩種觀點也同時否定了同案之間存在某種獨立于內容的相互關聯性,尤其是否認了前案對后案存在某種獨立于內容的拘束力。
與這兩種觀點相反,本文試圖揭示和證明,同案同判的拘束力是真實存在的。這種同案同判的拘束力,并不以前案與后案判決在內容上的正確性為基礎和前提(無論這是法律意義上的還是道德意義上的),而僅僅是由于前案時間上的“在前”性質而形成的拘束力。
許多人雖然在事實上承認這種純粹基于時間“在前”地位而形成的“前案”拘束力,但很難在智識上接受它。尤其是如下這種可能性的存在,使得在智識上接受這一點顯得非常困難:假設前案是錯誤的,那么前案對后案的拘束力就會導致荒謬的結果。
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法律理論層面清晰地說明同案同判拘束力的性質。具體來說,就是在同案同判中,前案對后案的拘束力究竟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拘束力,此種拘束力為何是合理的,它的限度是什么。
二、依規則裁判與同案同判之間的復雜關系
從客觀效果的層面來看,同案同判與依規則裁判確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依規則裁判的字面含義,就是當規則不變時,統一適用規則的效果被假設為是一致的,這實際上就達到了同案同判的效果。但依規則裁判的含義遠比這一點復雜得多。
依規則裁判必然導致同案同判,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命題。因為規則在適用過程中存在著詮釋的空間和多種解釋的可能性,不同的法官在不同的情境下往往對規則作出不同的解釋和適用,有時候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這個時候很難說依規則裁判必然導致同案同判。現代法理學并不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一致的兩個裁判必然有一個是錯誤的,而是承認兩個具有既判力的裁判都是正確的裁判。中國案例指導制度產生的一個重要背景和初衷,就是要用“同案同判”的機制來解決法律解釋和適用過程中“不夠統一”的問題。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同案同判與依規則裁判都等同于形式正義,因此二者是同一的。但問題是,如果形式正義概念的內涵就是相同情況相同處理,不同情況不同處理,那么用形式正義的概念來論證同案同判的合理性,幾乎就是同義反復。尤其是,在現代法理學傳統中,法律與道德分離命題得到廣泛承認,正義本身也往往被當作一個“道德”要素而被從法律的“定義”中分離出來,不再與法律畫上等號。
依規則裁判并不必然帶來同案同判的效果。這是從客觀效果論,如果從機制的層次論,那么依規則裁判的內在邏輯,必然會排斥同案同判的機制發揮作用。這在本質上是由依規則進行推理的內在結構和邏輯決定的。
權威性法律觀認為,由于法律規則的核心特征是內容無涉的,因此法律規則是不透明的,對法律規則的適用就是對法律規則之淵源的適用,也就是對法律規則制定者“意志”之內涵的解釋和適用,而非對法律規則制定者之意志的正確性的評價。這使得法律推理與其他實踐推理形成了鮮明的區別。例如,閱讀一部小說(A)的理由是這是一部好小說(B),而這是一部好小說(B)的理由,是這部小說精彩和深刻(C),那么,這是一部精彩與深刻的小說(C),就是閱讀該小說的理由(A)。在這個推理過程中,理由之間是可以互相傳遞的。即,如果B能夠證成A,C能夠證成B,則C就能夠證成A。但在法律推理中,這種理由之間的可傳遞性消失了,法官在個案裁判中,依照法律規則推理就是依照立法者意志(B)進行推理,作出判決(A),但立法者依照何種理由(C)形成立法者意志(B),則在所不問。這個時候理由C并不能直接推出結果A。拉茲將這一點看作是證成中理由可傳遞性的缺乏。這一點之所以能成立,乃是由于法律規則具有雙重屬性:既是要求按照法律規則內容行動的直接理由,也是不根據其他理由進行與法律規則的規定相沖突的理由(排他性理由)。〔3〕See 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p.213-215.
在這樣一種法律權威觀中,法律的含義只能是權威性的法律規則。如果突破權威性法律規則的界限,將許多“法外因素”“價值判斷”都包含到“法律的界限”之內,那么,拉茲所強調的“依規則裁判”的含義就被模糊了。就此而言,依規則裁判論的核心含義,就是權威性成文法規則對法官的排他性約束。既然法律規則是一種法官裁判的排他性理由,那么法官當然就不能依據同案同判的理由來裁判案件。
當然,像德沃金那樣,借助于詮釋學的資源而對“依規則裁判”中的法律作更加實質性的理解,從而突破“依規則而裁判”所設置的界限,也是一種值得嘗試的選擇。這個時候,被哈特與拉茲等法律實證主義者當作“道德”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的內容,如道德判斷、價值判斷等,都可以被重新包含到法律的界限范圍之內,成為法律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同案同判也可以被作為一種有助于在復雜處境中確定此種實質性法律內涵的技術或者方法,而被看作至少是與依規則裁判不矛盾的,因此也被包含在“依規則裁判”的概念射程范圍之內。但這樣做,整個問題的最關鍵和實質部分也被扭曲和掩蓋了。因為在這個問題架構中,真正重要的是規范法理學和現實主義法學之間圍繞“依規則裁判”戰場所展開的立場之爭,任何其他的問題最后都服務于和服從于此種立場的分派和捍衛。而至于同案同判本身是什么,前案何以“拘束”后案,用“拘束”來描述前案與后案之間的關系是否合適,這些對于我們理解同案同判最為關鍵和根本的問題,就被輕輕放過,一筆勾銷了。
三、作為現代法律獨立且核心要素的同案同判
如果我們跳過立場之爭,用一種更加中性和客觀的詮釋學眼光看法律解釋和適用過程中的各種創造性因素,以及通過這些創造性因素呈現出來的立法與司法之間的關系,那么就可以看到,將“法律”的含義“實質化”和“寬泛化”,并不能真正維持“司法服從立法”意義的“依規則裁判論”。因為當我們將這些價值判斷因素和權衡因素納入法律的內涵之中時,對于“法律規則”含義是什么的最終決定權,恰恰是解釋和適用的法官,而非立法者。這個時候,對于“立法意圖”的具體含義是什么,司法掌握了主動權和最后的決定權。
如果我們要真正地理解同案同判拘束力的性質,就必須將自己從這種“依規則裁判”的適用視角中解放出來。這種視角的實質是以立法權威的視角來觀察和理解裁判者,而不是從裁判者本身的視角觀察和理解司法裁判本身。從歷史上看,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立法,但司法在任何人類社會的法律秩序中都不可或缺。司法可以脫離立法而存在,但立法必須依賴于司法,否則“法治”必然蛻化為“法制”。對法律人來說,司法裁判才是“法律思想和法律原則的中央寶庫”。〔4〕[英]阿蒂亞:《法律與現代社會》,范悅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立法與司法被緊密綁定在一起,形成互為條件的關系,這件事發生在法律大規模實證化之后。〔5〕參見[德]盧曼:《法社會學》,賓凱譯,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61-270頁。一直到19世紀中葉,白哲特在觀察英國憲制時,對此還有著非常明確的歷史記憶。在白哲特看來,英國議會的首要功能就是選舉出首相和內閣,在他列舉的議會功能中,立法是最后一項功能,甚至排在“表達功能”“教育功能”和“提供信息功能”之后。他用類似“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修辭,禮貌性地承認了英國議會立法功能的重要性。〔6〕參見[英]白哲特:《英國憲制》,李國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頁。
即便像拉茲那樣堅持強硬立法權威觀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裁判本身構成了某種獨立類型的機制與現象。在解釋為什么會存在“解釋”(Interpretation)的問題時,拉茲也不得不承認,在解釋中,規則的權威性(authority)與裁判的延續性(continuity)構成了兩種彼此獨立,但是同樣重要的價值。這意味著,延續性并非是權威性的某種副產品。當拉茲用延續性的概念時,其核心含義顯然就是同案同判。因為他用來證明延續性并非權威性的副產品所列舉的兩個理由中,第一個理由就是規則和先例同時具有約束力。如果我們注意到拉茲是在抽象和一般意義的一般法理學層次上,而非在特殊法理學的語境中(英美法)討論這個問題時,這一點尤其意味深長。拉茲所提供的第二個理由是,法教義學在法律中發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既構成了對立法權威的一定限制,同時又進一步強化了法律的延續性特征。此外,拉茲還提出了一個反證來證明延續性在法律體系中的獨立價值和地位:創立規則的權威會死亡或者失去權威,但法律體系仍然繼續存在,并且死去或者失去的法律權威所創立的規則,此后仍然繼續具有約束力。〔7〕同前注〔3〕,Joseph Raz書,第235頁。
同案同判與權威性這兩種法律體系內相互獨立的價值之間的具體關系究竟如何?拉茲并沒有給出一個非常清晰和明確的答案。他只是用價值(values)這個模糊概念來指稱二者。尤其是,如果規則具有排他性理由的特征,何以同案同判仍然存在,并構成性地對司法個案裁判發揮作用?
如果從系統論法學的視角看這個問題,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立法與司法之間并非是上/下的等級關系,而是法律系統內部分化出來的兩個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并且司法是法律系統的中心,而立法則是法律系統的邊緣。〔8〕See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Verlag, 1995, S. 321.
區分中心/邊緣關系的標準,并非是效力層級上的誰高誰低,而是“不可取消性”。對于法律系統來說,司法不可被取消,而立法可以被取消。例如,在立法過程中,由于各種利益團體的派系斗爭和對立,某一項立法可以無限期延后,或者直接被取消。這對法律系統并不構成“一刀致命”的效果。但對于司法來說,任何一個案件,只要符合起訴條件,法院就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予以審理。“禁止拒絕作出裁判”原理的確立導致了此種司法裁判的功能迫令。如果議會關門,法律系統并不會停擺。但是法院關門的話,法律系統就直接癱瘓了。因此,相對于立法,司法對法律系統而言更為重要和關鍵,具有“不可取消性”。司法才是法律系統的核心,至少在定義“法律是什么”的問題上,司法的重要性要超過立法的重要性。
立法的主要工作職責從“防止法律被改變”轉變成“大規模改變和創立法律”,這件事情只能是在從傳統的階層分化的社會向現代功能分化社會轉變實現之后才會發生。一方面,傳統的等級制的社會階層秩序解體了,隱含在這個秩序背后的本體論的宇宙論也坍塌了。自然法/實證法層級關系的坍塌與議會立法的廣泛出現幾乎是同步的過程。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社會的功能分化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復雜性的增加。由此出現了大量此前從未發生過的現象,如大規模的城市化,工業革命所造成的工業法等新興領域的出現,因此不得不通過大量的全新立法來應對這些新現象和新事物。〔9〕同前注〔5〕,盧曼書,第265頁。另一方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由于失去階層分化的社會現實的支撐,自然法失去了說服力,因此通過一個專門機構創造新法律,改變或取消舊法律這件事情在認識論上不再存在障礙。法律實證化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法律的可變性。
從功能分化的角度看,立法處于法律系統與政治系統結構耦合的機制之中。所謂的結構耦合,就是兩個功能系統之間比較穩定的相互影響的通道與機制。〔10〕參見泮偉江:《憲法的社會學啟蒙:論作為政治系統與法律系統結構耦合的憲法》,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第15頁。通過立法,政治系統可以穩定地對法律系統形成刺激。例如,通過各種政治商談、交易和妥協,將政治意志轉化成法律規范。同樣地,法律系統也通過結構耦合的機制對政治系統產生影響,例如,通過憲法的違憲審查機制判定某個具體的立法無效。
由此形成的一個洞見是,法律系統最核心的特征并非是“依規則裁判”,而是“合法/非法”的二值代碼。依規則裁判是可以被凌駕的,因為超越法律的現象,以及通過司法裁判判定立法無效的現象廣泛存在。但法律系統必定是合法/非法二值代碼的,因為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不能同時判定某個行為既合法又非法。
如果我們帶著這種關于立法與司法關系的新視角來觀察依規則裁判與同案同判的關系問題,就會形成對問題的全新理解。法律系統的核心特征就是“合法/非法”的二值代碼化運作,而立法在某種意義上,則是服從和服務于法律系統合法/非法的二值代碼化運作的某種輔助的設置。盧曼因此將立法看作是“補充性的”,是一種“綱要”,也就是被用來輔助合法/非法二值代碼化運作的“判準”。〔11〕同前注〔8〕,Niklas Luhmann書,S.190.換言之,之所以需要立法,乃是為了更好地展開司法裁判工作。〔12〕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強調司法要“以審判為中心”,相關分析可參見劉濤:《法院組織及其決策:司法職業保障的系統觀察》,載《北大法律評論》(第18卷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285頁。當我們對某項事物進行定義的時候,我們一定是根據該項事物的核心因素來思考定義問題,而不是根據邊緣因素來思考定義問題。比如說,對于教學活動來說,教師圍繞著本學科知識點的系統講授以及學生的系統學習是核心因素,而教室、黑板、粉筆、桌椅等都是輔助設施。這些輔助設施對教學活動當然是很重要的,沒有它們,我們會覺得教學活動非常不便。但一旦發生了傳染病疫情,教師和學生必須各自隔離,因此無法通過教室等教學設施開展教學活動,雖然有所不便,教師和學生還可以借助騰訊會議等在線視頻開展教學活動。無論輔助設施多么匱乏,但只要“教”和“學”的活動存在,教學活動就不會消失。無論這種教學活動是在曠野中,還是在相隔千里通過網絡和電話的片言只語的交流中。同樣地,對現代法律而言,立法這樣一種輔助措施,對司法裁判的合法/非法二值代碼化運作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它通過一般性的語句設定了某種“條件式綱要”,從而使司法更好地和更方便地批量化處理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司法裁判的工作。但我們也看到,在出現法律漏洞或者法律滯后的情況下,雖然無法實現依規則而裁判,但一個卓越的法官仍然可以運用各種各樣法教義學的工具和法律解釋的技術,作出同樣出色,甚至更為卓越的個案裁判。
四、同案同判中存在著大量的權衡和決策空間
如果說,在成文法規則與個案裁判之間存在著大量的權衡和決策的空間,那么,在同案同判結構中的“前案”與“后案”中也同樣存在著大量的權衡和決策的空間。這樣一幅司法裁判的圖景更加符合司法實踐的真相。反過來說,如果同案同判只能是一種比較空洞的弱主張,那么在同樣的意義下,依規則裁判也是一種幾乎同樣空洞的弱主張。
同案同判與依規則裁判作為司法個案裁判中兩個相對比較獨立的構成性機制,在具體個案裁判過程中,也許仍然存在著某種“先后”意義的優先順序,即,當兩者發生沖突時,依規則裁判在一般意義上仍然優先于同案同判。但反過來說,這并不意味著同案同判的結構就因此取消了。它仍然存在并發揮著作用。
確實,在個案裁判中究竟是作為具體判準的某個規則優先,還是同案同判優先,并非是這場爭論中最緊要之處。這場爭論中最緊要之處在于,在個案裁判中,規則和同案同判是否都作為某種基礎性機制發揮了構成性作用,抑或僅僅規則作為獨立于內容的權威發揮了這種基礎性的構成作用。
因此,我們就需要一種新理論,來對這幅更加真實的圖景作出解釋和說明。在這方面,盧曼通過引入社會系統論的組織理論對司法裁判所作的分析就非常有啟發意義。與法學方法論、法律論證理論和法教義學的觀察視角相比,社會系統論的組織理論對司法裁判的觀察視角并非是“正當的裁判如何可能”,而是從二階觀察的視角考察,作為一種特殊的決策類型,司法裁判如何可能作出,或者說,作出司法裁判的條件是什么。同時,社會系統論的組織理論的分析框架也意味著,個案裁判之間并非是彼此孤立和分離的,而是彼此緊密關聯在一起,形成了某種穩定地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過程和結構,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自創生社會系統,即組織。〔13〕參見賓凱:《從決策的觀點看司法裁判》,載《清華法學》2011年第6期,第94-108頁。
社會系統理論認為,組織的核心內容就是決策溝通,也就是圍繞著決策所展開的各種溝通。決策就是在多種替代可能性中選擇的一種可能性。不同決策之間的相互關聯和影響,就形成了作為自創生系統的組織。就此而言,司法裁判的本質就是決策,而司法就是由司法裁判之間的遞歸性關系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組織系統。法官、法院、司法行政等各種基礎設施和輔助設施,都是緊密圍繞著作為決策系統的司法而建立起來的,并且服務于一個個司法裁判的作出。
作為整體的司法組織當然并非是法律系統的全部,更不可能是社會的全部,而必然僅僅是其中的一個部分,這就意味著某種司法內部/司法外部之間的系統/環境關系。無論是司法的內部還是外部,許多因素事實上總是處于變化和不確定的狀態之中,如立法的變化,各種社會關系和事實的不斷演變,因此,這些不確定的因素不斷地刺激著司法對它們做出回應和調整。
正如阿蒂亞所指出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把法律更多地同法院、法官和治安法官聯系在一起。當我們談到法律的延誤,或抱怨法律過時時,我們往往想到的是法院和法律制度,而不是法律規則本身。”〔14〕同前注〔4〕,阿蒂亞書,第1頁。因此,當我們談論司法裁判時,我們往往會說,司法通過某個裁判,對某事的態度如何。這個時候,我們實際上談論的是司法作為一個整體對某事的態度。
在法律權威論的框架中,這一點反而是很可疑的,因為法律對某事的態度更多地體現在各種具體的規則中,體現在法律權威的意志中,而非個案裁判中。如果司法個案裁判之間并不存在某種內在和本質的聯系,并不呈現出某種穩定的秩序形式,并不呈現出一種內/外的結構,那么當前中國廣泛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現象或許是合理的,因為每個個案裁判都可以自稱是嚴格適用規則所產生的結果。個案裁判之間雖然不一致,但個案裁判的正確性并不以它為前提。
如果法律系統是作為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整體而存在,那么法律系統與它之外的所有社會事件之間存在著某種系統/環境之間的界限。顯然,這個界限并非是某種物理空間意義的線條,而是在時間面向通過法律系統內部運作形成的某種界限。〔15〕參見泮偉江:《法律是由規則組成的體系嗎?》,載《政治與法律》2018年第12期,第121頁。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客觀時間與系統內時間之間的差異。所謂客觀時間,也就是刻度意義的時間。〔16〕關于刻度意義的客觀中立時間的分析和闡述,可參見[英]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7頁,尤其是其中指出鐘表刻度意義的中立性時間所包含的時空分離和時空虛化的含義。在這種客觀時間的框架下,正發生的一切事件都同時發生,都在當下發生。這種所有事件發生的當下性確保了時間的客觀性。因此,所謂的時間穿越和時間旅行都是不可能的。當下的我不可能穿越這個客觀時間,提前進入當下之你的未來或者回到當下之你的過去。〔17〕Niklas Luhmann, Sinn als Grundbegriあ der Soziologie, in Jürgen Habermas/Niklas Lhuman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1.Aufl., 1971, S. 25.
這就意味著,在事件共同發生的一剎那,無論是系統的內部還是系統的外部,事件與事件之間是無法立刻相互做出回應的。因為,所發生的一切都同時發生。因此,司法必須通過內部的不斷遞歸式的循環運作,來對外部環境的變化作出有選擇性的調整:對其中的某些變化保持冷漠,對另外一些變化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回應能力。例如,一般來說,對于立法的變化,司法是相當敏感的,但同時司法也對社會環境的變化保持更具有選擇性和靈活的敏感度和回應性。
系統如果要回應系統外所發生的事件,就必須在系統內部建構出某種內部時間,也就是之前和之后的區分。因此,在我們觀察系統時,就不能僅僅觀察作為客觀時間的當下,而必須觀察系統在當下這一個客觀中立時間下所處的意義結構,也即系統對過去的“回憶”和未來的“預期”。〔18〕參見泮偉江:《超越錯誤法社會學——盧曼法社會學理論的貢獻與啟示》,載《中外法學》2019年第2期,第37頁。這就產生了客觀時間與系統的內時間的差異。就此而言,內置于不同系統的內時間與內時間之間的差異是存在的——它們并不客觀,而是存在著速度的差異。例如,政治系統中的內時間往往比法律系統中的內時間要快很多。但無論它們的速度有何差異,它們都是一種觀察的圖示,都是通過之前/之后的區分,并標示其中的一側,形成系統對外部環境的觀察,并進而制造出信息,吸收環境和系統中的各種不確定性。〔19〕Niklas Luhmann, Organization and Decision, translated by Rhodes Barre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47-180.
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系統中的每一個當下,其各自的過去和未來都是不同的。舉個簡單的例子,當我敲下這個字時,這個當下的過去,只能是這一刻之前所發生的一切。但是當讀者讀到這一行字時,那個“未來的當下”(künftigen Gegenwart)的“過去”,就同時也包含我敲下這一行字時發生的一切事件。〔20〕對此一個精練但非常精彩的闡述,See Elena Esposito, The Future of Futures: The Time of Money in Financial and Society,Edward Elgar, 2011, p. 19-27.所以,系統內部作為觀察圖示的這個時間結構的具體內容是不斷發生變化的。
五、同案同判拘束力性質的重新界定和理解
同案同判乃是司法系統內部運作時間約束性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在這個觀察視角下,與“前案決定后案”的通常觀點相比,同案同判的含義也發生了微妙但具有實質性的變化。在之前/之后的時間圖示下,當前(Gegenwart)的含義并非僅僅是一個客觀中立的時間點,同時也是之前/之后這個區分形式本身。同時,如果從未來看當下,則當下就是“未來之當下的過去”(Vergangenheit als einer künftigen Gegenwart)。就此而言,不但過去已經發生的“前案”對作為“后案”的當下裁判具有約束和限制,同時,作為“未來之當下的過去”,當前正在作出的裁決,也是未來可能作出之裁決的“前案”,因此,正在作出的裁決必然也要考慮,它對未來之后案所產生的“同案同判”的輻射力。就此而言,不但通常意義的“前案”對“后案”存在著某種約束和限制,同時,尚未出現的“后案”對作為它的“前案”的當下判決,也存在著某種重要的約束和限制。這種拘束,實質上就是決策時出現在決策者視野中的各種不同可能性的預期和類型。
用是否是法律義務為標準描述司法裁判中已經作出判決的“前案”與尚未出現的,但未來可能發生的“后案”對當下正在作出的判決的限制和約束,并不恰當。在此種模式下,司法對個案裁判的約束,并非是通過“決定”的方式來實現的,而是通過下述方式來實現的:為法官個案裁判事先設置某種范圍與空間,從而通過此種范圍和空間界限的劃定,排除了法官個案裁判活動的選擇范圍。這正如圖1所示。

圖1 已發生案件作為當前案件裁判的決策基礎
因此,法律系統的內時間不是純粹客觀中立的,而是擁有自身的特性,是一種特殊的觀察圖式。過去雖然總是已經過去的,因此是不可更改的,但未來總是開放的,總是蘊含著某些新鮮的視野和選擇。每一個決策都有一個專屬于自身的過去,也有一個專屬于自身的未來。對決策而言,這就意味著,只要是決策,總會帶來新鮮的內容,總會產生新的驚訝和信息。正如盧曼所指出的,“未來的不確定性是決策得以可能的一個不可取消的條件。”〔21〕同前注〔19〕,Niklas Luhmann書,第123頁。未來并不僅僅與過去不一樣,它還承諾新穎性。就此而言,個案裁判中存在的不確定性和模糊的空間,并非是一種必須被彌補的缺陷,同時也是法律系統最可貴的資源,它使想象力和創造性成為可能。〔22〕同前注〔20〕,Elena Esposito書,第25頁。
總之,同案同判其實是作為裁判組織的“記憶”和“預期”結構在個案裁判中發揮作用。〔23〕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許多社會學研究所揭示的,不但個體有記憶,社會也有自身的記憶,并且社會的記憶與個體的記憶往往是有差異的。例如,許多口述史的研究都揭示了這一點。因此,組織社會這種特殊類型的社會系統,也有專屬于自身的記憶,當然也有自身所特有的記憶結構和過程,并且這是區別于組織中個體的私人記憶。它是構成性,并非是因為它能夠“決定”,而是因為它作為“參照框架”和“決策條件”的不可或缺性。決策所需要的大部分必要信息,恰恰是通過這個“參照框架”和“決策條件”形成的。未來的決策必須通過這些條件來做出,或者更具體地說,未來決策必須通過與過去決策的比較才能夠被做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知道未來決策的變化究竟在哪里。這個過程和機制與其說是“決定性的”,倒不如說是“引導性的”(Orientierung)。
通過記憶機制,司法“記住”某些過去已經發生的決策,同時遺忘另外某些過去已經發生的決策。因為每一次決策,都發生在不同的“當下”,因此每一次決策的“過去”和“未來”都是彼此不同的。就此而言,記憶的本質就是選擇和建構。所謂的過去,并非是作為“純客觀事實”的過去,而是當下對“過去已發生之事實”的“建構”。這方面,陳丹青曾經舉的一個西方美術史上的例子特別具有說服力。打開任何一本西方美術史的教材,19世紀都是印象派群星璀璨的時代,從安格爾到德拉克洛瓦之后,經過簡略的過渡,就到了馬奈、莫奈、雷阿諾、畢沙羅、修拉為代表的印象派群星的時代。但如果你真正回到19世紀,你會發現這些印象派大師在當時都是邊緣人物,梅索尼埃、卡巴內爾、勒帕熱、庫退爾、鮑迪耶、德拉羅什、莫羅、布格羅、夏普馬丁、熱羅姆、佛朗德蘭、蓋蘭等這些學院派沙龍畫家才是當時的主流和典范。但如今,在紐約大都會美術館,馬奈、德加、塞尚、莫奈、雷諾阿等這些19世紀的失意者,每人都獨占一個展覽廳,而上述這些學院派的大師們的畫只能掛在走廊上,與其他人的畫擠在一起,也沒有幾個人記得他們的名字。這就是社會記憶建構和再選擇機制所形成的效果。〔24〕參見陳丹青:《我的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33頁。
對司法裁判組織而言,通過區分規則來確認前案與后案之間的同與異,其實就是這樣一種記憶過程。〔25〕在不同的歷史狀態和法律體系中,這種記憶建構和選擇的標準可以是不同的。例如,在德國,裁判要旨在此種記憶建構和選擇的過程中發揮了一種特殊的作用。對此可參見黃卉等編:《大陸法系判例:制度?方法——判例研讀沙龍Ⅰ》,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同案同判機制中的“前案”,往往指的是“最近”的前案。〔26〕參見泮偉江:《一個普通法的故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頁。同時,許多前案中的異議意見,通過這種記憶機制的建構和再選擇,反而成為最終被記住的“先例”。
對同案同判的這種理解也顯示出了與德沃金的整體性法律理論的微妙的區別。德沃金的整體性法律理論也同樣支持同案同判,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證立同案同判的一個重要理論。整體性法律理論的問題在于,它僅僅看到了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統一性,但卻沒有看到,“記住”同時也是“遺忘”,記憶結構同時也是遺忘結構。因此,整體性法律理論最終必然要求一個能力無窮的、永不知疲倦的、半神半人的赫拉克勒斯式的法官來承擔裁判的任務。對作為凡人的法官來說,裁判因此變成了一個過于沉重的負擔,赫拉克勒斯式的法官職責也成了一種對凡人法官過于嚴苛的要求。
“同案同判”的含義并非是指當下的判決是由過去的判決所決定,而是指,作為司法裁判組織中的一個具體決策,當下案件的判決,無論它是如何“新”與“不同”,都必須通過調用司法裁判組織之前的決策這樣一個“記憶”的過程才能夠做出。這意味著,同案同判的真正含義并非是一種強烈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而是一種決策學意義上的“結構”與“結構中的選擇”的關系。結構事先為發生在結構中的選擇劃定了范圍與空間,從而事先為此種選擇排除了某些標準和可能性。這種排除也不是絕對的,因為通過“推翻先例”,這種排除得以被排除。這就意味著,被排除的可能性并沒有真正消失,而是被當作被排除的可能性儲存起來,在未來它們仍然有被重新激活的可能性。但這同時也意味著,要重新激活這些被排除的可能性,就需要另外一個決策,即重新選擇被排除可能性的決策。
當前中國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的局面,其所帶來的最大后果也許并不是,至少不僅僅是倫理學意義上的形式正義的問題,而是難以形成司法的自我同一性的問題。這意味著,中國司法長期以來,在穩定社會預期方面一直不盡如人意,而這又與中國社會當前出現的種種所謂的“失范”現象有著緊密的關聯。〔27〕參見泮偉江:《當代中國法治的分析與建構》(修訂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142頁。
事實上,不光是同案同判是司法決策的“記憶”機制,成文法規則也構成了個案司法決策記憶機制的核心部分。由于成文法規則也無法決定個案裁判的具體內容,因此個案裁判的作出仍然需要依賴法官的創造性解釋和決斷。成文法規則實質上發揮的作用仍然不過是為個案裁判“預先排除”某些標準與選擇可能性的范圍。同案同判也并非是對作出個案裁判的法官提出的某種命令,而是法官可資利用,并且是不得不利用的一種進一步排除選擇標準和可能性范圍的機制。概括來說,它們都構成了這種決策情境的某種基礎性的條件。它們相互之間構成了某種“正交”的關系(orthogonal relation)。

圖2 依規則裁判與同案同判的正交關系
由此,包括同案同判和依規則裁判在內的這種記憶過程構成了個案裁判的決策前提。因為任何決策都是情境化決策,都必須以情境為前提和條件,而法律系統內部的這個記憶過程,顯然就是決策情境的一個基本條件。作為決策前提,它起到簡化決策的作用。如果沒有先例,決策就涉及對復雜決策情境的更為細致和繁重的分析,但通過先例和規則,尤其是通過先例所構成的判例鏈條,決策就被簡化為一種區分,即遵循還是偏離。〔28〕同前注〔19〕,Niklas Luhmann書,第182頁。決策前提作為冗余性發揮作用,減少對信息的依賴和探索。〔29〕參見劉濤:《冗余和遵循先例:系統論的考察及啟示》,載《交大法學》2017年第2期,第78-90頁。
依規則裁判論突出同案同判與依規則裁判之間的尖銳對立,這種表達背后隱藏的含義其實是,否認法律系統內部所建構的記憶過程的存在,也就是認為,法律系統內部所建構的此種過去狀態和未來預期,對法律系統當下的裁判而言,無關緊要,可有可無。此種視野下的法律系統,更類似于尼采筆下的動物,它們缺乏建構過去和展望未來的能力,因此永遠生活在一種沒有記憶的當下狀態之中。每一個行動都是當下的行動,并且每一個行動甚至都很難稱得上是決策,因為既不存在決策的各種條件和前提,也不存在決策的必要。每一個行動都類似于某種“本能驅動”下的條件反射。〔30〕參見[德]尼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陳濤、周輝榮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頁。
在這方面,哈特顯示出了一流理論家的深刻洞察力。一方面,哈特通過強調“初級規則+次級規則”作為法律系統之內在運作的重要性,暗示了法律系統/環境之區分的存在,這就進一步構成了法律與道德分離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在《法律的概念》中,哈特也非常明確地指出,不能將法律看作某種超越時間的純分析性的概念。哈特明確地描述了法律系統的生長、成熟和衰老問題。〔31〕參見[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許嘉馨、李冠宜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頁。就前者而言,法律系統區別于環境,從而具有某種內在的自我同一性,就后者而言,在法律系統內部存在著內時間意識。同時,哈特也承認了法律演化的可能性,因為他認為法律存在從簡單社會的法律向復雜社會的法律演化的過程。因此,從哈特的法律理論中,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推導出法律系統與社會環境之間互動和調整的關系。
當我們思考到這一步的時候,用獨立于內容的權威概念觀察法律的局限性就體現出來了。權威的概念既無法將法律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這種動態而復雜的關系呈現出來,也無法描述和呈現法律系統內部運作所具有的內時間機制。而恰恰在這一點上,同案同判的概念顯現出了優越性。如果我們進一步看清楚“代碼+綱要”的法律系統內在運作的雙層結構,同案同判在法律系統中的地位和性質就會更清晰地顯現出來:同案同判是法律系統的偶聯性公式,而不是指導個案裁判的具體判準。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法教義學層次的“體系性”,還是作為司法構成性規則的“同案同判”,都是法律系統在觀察層次對自我同一性的觀察,或者說,就是“在系統中再現系統的統一性”。〔32〕同前注〔8〕,Niklas Luhmann書,第221頁。
同案同判作為法律系統的偶聯性公式,而非政治系統、教育系統的偶聯性公式,是與法律系統承擔的社會功能相關的,同時也意味著,司法組織與其他類型的組織存在著實質性的差異。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無論是企業還是行政機關,它們對外部環境變化做出調整的最常規手段,其實是組織人事和職位的調整。但在司法組織中,由于法官獨立審判原則和制度(尤其是法官終身制)的存在,這個手段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當可以隨意通過人事和職位的調整來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時,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往往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容忍。此外,禁止拒絕作出裁判原則在司法中確立,也進一步強化了判準與決策之間所存在的詮釋性循環,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同案同判在司法組織中的基礎性地位。
六、結語
同案同判拘束力的性質問題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法理學問題。這個問題最困難的地方就在于,在客觀時間的認知框架下,人們往往把拘束力理解成是某種“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一旦我們接受對拘束力的此種決定論的理解,在智識上就很難理解“前案”對“后案”拘束力的合理性。但在現象和事實層面,同案同判的拘束力又是客觀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要么將同案同判的拘束力看作依規則裁判所帶來的一種自然效果,要么通過道德層面正確內容的說服力,或者形式正義等模糊的概念來論證和說明同案同判的合理性。在關于同案同判的這幾種理論中,同案同判要么失去了獨立的地位,變成依規則裁判的一種修辭學表達,要么就變成了一種道德準則,從而失去了對現代法律性質的解釋力,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邊緣概念。
本文挑戰了這種似是而非的認識論框架,通過區分客觀時間和系統的內時間兩種不同的時間觀,認為應該在系統的內時間觀的框架中認識和理解同案同判的拘束力問題,從而重新定義了同案同判拘束力的性質和內涵。
通過對客觀時間與系統的內時間這兩種時間觀的區分,我們澄清了,同案同判的拘束力并非是客觀時間自身形成拘束力,因為在客觀時間下,該發生的必然發生、確然發生,并無所謂拘束。同案同判的拘束力主要是指,通過法律系統的內時間,也即之前/之后的時間圖示,形成不同運作之間的聯系,從而使這些運作在此種時間圖示下形成一種互為條件、互相約束的關系。
同案同判內在于法律系統內的拘束力,與客觀時間架構下的“因果關系”拘束力,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并不是說,時間作為某種客觀中立的“某物”對當前的裁判產生一種因果關系意義的拘束力,而是說,作為不可更改的歷史的“前案”和作為選項的預期中的未來“后案”,作為當前案件之裁判的條件,對當前案件的裁判形成的拘束力。這就使當前裁判的個案仍然是不確定的,但并不是隨機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同案同判理解成一種機制,對任何一個當下作出的個案裁判而言,它都具有構成性的基礎地位。這種拘束力當然是有限度的,但它必然存在,并且有效。
通過對同案同判拘束力性質的重新界定和理解,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深化對現代法律系統性質的理解。當然,本文對同案同判概念的界定,與傳統和主流的理解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被多數人所接受和傳播。真正的理論創新都是在傳統的邊緣處思考,因此也往往與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范式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甚至沖突。理論研究的意義很可能就在于在傳統的邊緣提出另外一種看問題的眼光,提供另外一種事先意想不到,但其實又有巨大合理性的思考方向與可能性。就此而言,本文的嘗試也許仍然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