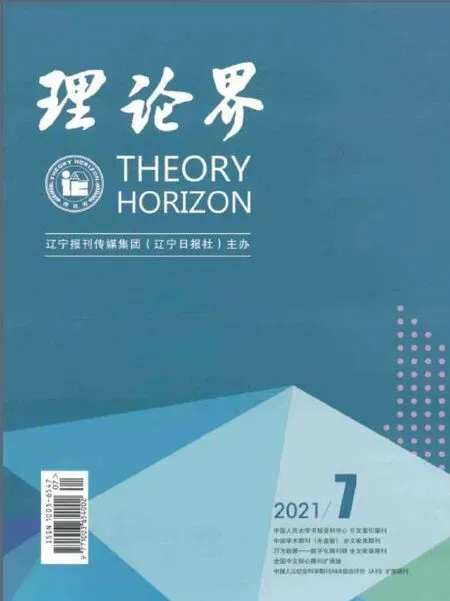作為真理的突出發(fā)生方式的藝術——論海德格爾的藝術概念
龐 聰
一、導言
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以下簡稱《本源》)中,海德格爾在存在論的意義上討論“藝術是什么”或者“藝術何以可能”的問題。至于這個問題的答案,海德格爾在文中將其概括為——“藝術是真理的一種生成和發(fā)生”。〔1〕所謂真理的發(fā)生是指對存在者是什么以及是如何的開啟或揭示。〔2〕對于真理在藝術作品中是怎樣發(fā)生的,學界已有不少相關研究。〔3〕〔4〕〔5〕〔6〕
然而,海德格爾的藝術概念仍有討論的空間。首先,海德格爾認為,“在藝術作品中,存在者的真理已被設置于其中了”。〔7〕但是,在這種說法中藝術和(藝術)作品實際上是相互規(guī)定的,藝術本身是什么仍舊是不明確的。這種不確定性緣于海德格爾在討論藝術概念時引入的解釋學循環(huán),它為我們討論藝術與真理的關系留下了余地。其次,海德格爾認為藝術只是真理的一種發(fā)生方式,除此之外,真理還有四種發(fā)生方式,即建立國家的活動、鄰近于最有存在特性的存在者、本質(zhì)性的犧牲和思想者的追問。〔8〕如果藝術只是真理發(fā)生的一種方式,那么藝術的方式如何區(qū)別于其他方式?為了作出這種區(qū)別,藝術是否除了從真理這里得到規(guī)定性,還需要從其他地方得到規(guī)定性?
以上問題的核心是海德格爾對藝術概念的界定或者說對藝術與真理關系的界定。對于這個問題,朱利安·楊(Julian Young)認為雖然對X的定義一般被理解為確定X的充分必要條件,但是海德格爾對藝術的定義并沒有因此失敗。在他看來,海德格爾通過擴展藝術概念,使之包含了真理的所有發(fā)生方式,從而使藝術能夠完全從真理的方面得到規(guī)定。〔9〕根據(jù)這種理解,難道海德格爾只是不滿足于一個過于狹窄的藝術領域(如音樂、繪畫、雕塑),他的意圖是將更多領域(如政治、宗教、哲學)納入目前的藝術領域嗎?
為了對楊的觀點進行評價,我們首先需要考察海德格爾是如何提出自己獨特的藝術概念的。筆者將他的工作概括為兩步:(1)借助古希臘人的技藝(τ?χνη)概念實現(xiàn)對當今流行的美學概念的顛覆(第二節(jié));(2)通過對技藝概念中沒有區(qū)分的藝術和手藝進行區(qū)分,提出自己獨特的藝術概念(第三節(jié))。基于上述考察,筆者最后將澄清海德格爾視角下藝術與真理的其他發(fā)生方式的關系(第四節(jié))。這種澄清對于考察海德格爾對藝術之謎的追問或者說對藝術概念的刻畫是否令人滿意,以及海德格爾對藝術在人類生活中獨特地位和重要作用的強調(diào)是否合理都是必要的。
二、作為“美學”的藝術與作為“技藝”的藝術
在海德格爾筆下,有兩個明顯不同的藝術概念:當今流行的藝術概念(美學)和海德格爾獨特的藝術概念。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批判前者而提出的,它與前者在關于真理和美的觀點方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筆者主張,海德格爾是憑借對古希臘人的技藝概念的借鑒做到這一點的,這也是他提出自己獨特的藝術概念的起點。
海德格爾認為,古希臘人沒有美學的概念,他們用“技藝”一詞既指藝術也指手藝,但值得注意的是,“技藝”這個詞對古希臘人而言并非指手工制作,而是指一種在知識的指導下把存在者作為存在者開啟出來的生產(chǎn)方式。〔10〕也就是說,藝術在古希臘人那里可以被看作一種生產(chǎn)方式,而它的本質(zhì)在于對存在者作為存在者的開啟或揭示。海德格爾在別處也提到這種將藝術作為一種廣義的生產(chǎn)能力的觀點。〔11〕
古希臘人的藝術概念(技藝)對當今流行的藝術概念(美學)有顛覆性作用。傳統(tǒng)上,人們一直認為“真”與思維相關,屬于邏輯學的范疇,而“美”與感情相關,屬于美學的范疇。人們希望在對藝術作品的感性知覺中達到一種被稱為“審美體驗”的情感狀態(tài),這種情感狀態(tài)被認為是由藝術作品所承載的“美”所激發(fā)的,因此,藝術無非就是美的藝術。這就是當今流行的作為美學的藝術概念,而海德格爾對此持有一種批評的態(tài)度。他認為,根據(jù)這種藝術概念,藝術最多具有一種生理性的功能,它的作用大致相當于胃液。〔12〕
上述藝術概念與美密切相關,而與真理毫無瓜葛;作為對比,海德格爾借助古希臘人的技藝概念將藝術與存在論意義上的真理關聯(lián)起來。他這樣做不僅重新定義了藝術,也重新定義了真理,甚至重新定義了美。具體而言,作為邏輯學的考察對象的真理意味著正確性,它指的是知識與事實的符合;〔13〕而在海德格爾這里,真理意味著存在者作為存在者的現(xiàn)身或者說無蔽狀態(tài)。相應地,真理在藝術作品中的閃耀就是美,用海德格爾的話說,“美是作為無蔽的真理的一種現(xiàn)身方式”。〔14〕
總之,海德格爾借助技藝概念成功地將藝術與真理關聯(lián)起來,從而實現(xiàn)了對作為美學的藝術概念的顛覆。但這樣做也遺留了一個問題。如果藝術唯有根據(jù)真理才能得到規(guī)定,而真理意味著存在者的開啟或揭示,那么理論上凡是能夠生產(chǎn)某種存在者的方式都可被稱為藝術。正如我們看到的,根據(jù)古希臘人的技藝概念,藝術和手藝無法得到區(qū)分。海德格爾也承認,按照這種理解方式,工匠、政治家和教育家“作為生產(chǎn)者都不外乎是藝術家”,〔15〕因為他們都通過各自的方式使某些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得以存在。將這種理解進行延伸,我們甚至可以將醫(yī)生、科學家、宗教人士等凡是能夠有所建樹的人都統(tǒng)稱為藝術家。顯然,該藝術概念過于寬泛。因此,海德格爾雖然保留了技藝概念中藝術與真理的關聯(lián),但他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將古希臘人未區(qū)分的藝術與手藝進行了區(qū)分。
三、“藝術”與“手藝”的區(qū)分
筆者主張,海德格爾并非通過在真理之外引入其他的規(guī)定性,而是通過從藝術與手藝各自同真理的關系入手對二者進行區(qū)分,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概念,而這一區(qū)分也將構成我們理解開頭提到的藝術與真理的其他四種發(fā)生方式的關系的關鍵。
從名稱上而言,海德格爾對古希臘人沒有區(qū)分的藝術與手藝進行了明確的區(qū)分。前者對應的活動是藝術創(chuàng)作(Schaffen),對應的產(chǎn)出是作品(Werk);后者對應的活動是手工制作(Anfertigen),對應的產(chǎn)出是器具(Zeug,也譯為“用具”)。本文接下來將追溯在這些不同的名稱背后,海德格爾對其含義的區(qū)分。卡斯頓·哈里斯(Karsten Harries)指出,在海德格爾的闡述中二者的區(qū)分實際上并不明顯,這是緣于海德格爾強調(diào)的重點始終是藝術使存在者存在的功能(生產(chǎn)功能),而手藝也具有這種功能。〔16〕但是,為了確立一個較為滿意的藝術概念,這種區(qū)分又是十分必要的。
上文提到,海德格爾認為藝術是真理發(fā)生的一種方式;作為對比,他認為器具的制作“絕非直接是對真理之發(fā)生的獲取”。〔17〕也就是說,海德格爾實際上認為器具的制作也是真理發(fā)生的一種方式,不過是一種間接的方式。如何理解該觀點?根據(jù)哈里斯的想法,器具中的真理不是初次建立的真理,而是已經(jīng)建立的真理,因為一般而言制作器具(比如鞋具)的工匠知道如何制作他要制作的那類東西,而那些使用工匠制作的器具(比如鞋具)的人也知道如何使用他要使用的那類東西。作為對比,藝術家面對的是未知,藝術創(chuàng)作要求的是原創(chuàng),因此,藝術作品中的真理是從頭(original)建立的真理。〔18〕那么,將哈里斯的理解進行延伸,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在為了實現(xiàn)鞋具的目的而設計和發(fā)明的意義上)最早制作鞋具的人是鞋具真理的開啟者,因為這個人創(chuàng)造了鞋具以及鞋具存在的意義,而此后所有模仿他制作鞋具的人則是鞋具的已被揭開的真理的繼承者,在此意義上,他們獲取的鞋具的真理是二手的、間接的?
這種理解可以有說服力地解釋一般的制作和原創(chuàng)性制作的區(qū)別。不可否認,人類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先人創(chuàng)造的結果,我們今天也依舊在大力提倡創(chuàng)造性思維。但是,這種理解依舊無法解釋原創(chuàng)性制作和藝術創(chuàng)作的區(qū)別,因為二者都要求原創(chuàng)性。具體來講,它無法解釋為何海德格爾會認為是凡·高的靜物油畫《農(nóng)鞋》揭開了“一雙農(nóng)鞋實際上是什么”,〔19〕畢竟凡·高既不是鞋具的設計者,也不是鞋具的發(fā)明者。創(chuàng)造一雙真的農(nóng)鞋難道還比不上僅僅畫出一雙農(nóng)鞋嗎?還有什么揭示存在者之存在的方式比從無到有的創(chuàng)造更徹底呢?由于海德格爾談論的“制作”似乎不包含“原創(chuàng)性制作”,我們實際上無法得知他認為原創(chuàng)性制作和藝術(在作為真理初次建立的方式的意義上)誰更重要,或者他是否會將原創(chuàng)性制作也算作藝術。但至少可以確定,海德格爾認為藝術作品(如凡·高的《農(nóng)鞋》)作為真理的一種發(fā)生方式有著獨特的地位,因為他說這些藝術作品“以自己的方式開啟存在者之存在”。〔20〕
凡·高的《農(nóng)鞋》究竟有何獨特之處?如果按照柏拉圖的觀點,鞋具的理念才是鞋具的真理,現(xiàn)實的鞋具是對該理念的模仿,相當于真理的影子,而畫家畫的鞋具又是對現(xiàn)實的鞋具的模仿,相當于影子的影子。但是,柏拉圖似乎無法回答,人們在欣賞凡·高的《農(nóng)鞋》時希望看到的只是一雙某處現(xiàn)存的農(nóng)鞋的外觀的復本嗎?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yōu)槭裁床桓纱嗳フ乙粡堔r(nóng)鞋的設計圖紙或者一張農(nóng)鞋的照片呢?筆者認為,在凡·高的油畫里確實有一雙農(nóng)鞋,但是那里并不只有一雙農(nóng)鞋,而是還有更加豐富的東西——一個農(nóng)鞋所屬的世界。海德格爾曾以自己的視角對《農(nóng)鞋》中的這個世界進行描繪:
凡·高的那幅油畫:一雙堅實的農(nóng)鞋,別無其他。這幅畫其實什么也沒有說出。但你立即就單獨與在此的東西一起在,就好像一個暮秋的傍晚,當最后一星烤土豆的火光熄滅,你跩著疲憊的步履,從田間向家里走去。〔21〕
我們在欣賞藝術作品時經(jīng)常有這種體驗,藝術作品帶著我們從現(xiàn)實的世界中離開而走進了作品的世界。人們一般把這種沉浸在作品世界中的浮想聯(lián)翩當作欣賞者主觀的任意想象,但是對海德格爾而言,想象可能正是我們把握存在者的本質(zhì)以及存在者所屬的那個世界的方式。海德格爾曾提出,世界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所有現(xiàn)成事物的集合,而應當被看作各種事物隨著主體的生存活動的展開而被關聯(lián)起來所組成的豐富的、動態(tài)的網(wǎng)絡。〔22〕世界的這種動態(tài)特性也被他稱為“世界世界化”。〔23〕反過來,這也意味著主體總是將具體的存在者把握為以某種方式對自身有意義并且相互之間關聯(lián)著的存在者。藝術作品的欣賞者正是通過類似的方式領悟著作品中呈現(xiàn)之物所提供的線索,在作品的世界流連著、回味著。比如,看到凡·高畫中的農(nóng)鞋,我們腦海中自然地浮現(xiàn)田野中的泥土、勞作的農(nóng)婦等畫面,于是我們就進入了農(nóng)婦所生活的世界,或者說農(nóng)鞋所屬的世界。〔24〕這個世界不能被理解為某個現(xiàn)實世界的再現(xiàn),而應被理解為一個只存在于作品中的世界。因此,在海德格爾那里,對于藝術作品的體驗不是為了帶來一種愉悅或新奇的情感享受,而是為了邂逅在作品中被開啟的那個包羅萬物的世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逗留于在作品中發(fā)生的真理那里”。〔25〕需要指出的是,對于作品中開啟的那個世界,每個真正的欣賞者都不僅是旁觀者。在進入作品的世界之時,我們原本的世界中某些東西會悄然失效或者生效,某些東西會重新排序,在這個意義上,藝術作品能夠“抑制我們的一般流行的行為和評價,認識和觀看”,〔26〕使我們的生活出現(xiàn)不同的可能性,海德格爾會說這是藝術作品中的真理在“起作用”(am Werk)。〔27〕
至此,我們終于可以回答,作為真理從頭建立的方式,藝術創(chuàng)作(相對于原創(chuàng)性制作)的特殊性何在。以《農(nóng)鞋》為例,該作品開啟了農(nóng)鞋所屬的豐富的、動態(tài)的世界,而農(nóng)鞋的本質(zhì)也在與那個世界的關聯(lián)中得到充分的彰顯。作為對比,第一個制作農(nóng)鞋的工匠雖然也值得贊賞,但他制作的農(nóng)鞋只是一雙農(nóng)鞋。按照海德格爾的思路,由于工匠制作這雙農(nóng)鞋是出于使用的目的(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將器具的本質(zhì)規(guī)定為“為了作……的東西”,〔28〕他在《本源》中也稱之為“有用性”),〔29〕這意味著農(nóng)鞋已經(jīng)以某種方式成為對主體有意義的存在者了,也就是說它必定已經(jīng)處于主體的世界中的某個特定位置而從屬于那個世界。由于這種從屬關系,農(nóng)鞋的存在需要依靠它背后的世界整體的存在才能顯現(xiàn)并維持下去。工匠在創(chuàng)造這雙農(nóng)鞋的時候雖然對農(nóng)鞋的具體樣式一無所知,但他顯然對使農(nóng)鞋得以存在的這個世界并非一無所知。在這個意義上,這雙農(nóng)鞋中發(fā)生的真理(“有用性”)是間接的。
相比之下,藝術作品不是為了任何其他目的而被創(chuàng)作的,用海德格爾的話說,藝術創(chuàng)作活動就是為了“特地帶來存在者之敞開性亦即真理”〔30〕,這同時也意味著藝術家無法指望憑借已知的世界來進行他的創(chuàng)作活動。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藝術家面對的是未知,而他的創(chuàng)作活動是一種比原創(chuàng)性制作更加徹底、更加原始的創(chuàng)造。正是緣于此,海德格爾才能把藝術創(chuàng)作看作真正從無到有的創(chuàng)造,才能強調(diào)藝術作為真理的突出發(fā)生方式的重要性。比如,他認為與作品的牽連是“真理本身得以在存在者中間存在的一種突出可能性”。〔31〕他還宣稱,在藝術作品中“存在者整體之真理,即無條件者、絕對者,向人類開啟出自身”,而這樣的藝術在本質(zhì)上是偉大的,因為它是一種“絕對需要”。〔32〕
以上筆者通過對兩對概念(制作和原創(chuàng)性制作,以及原創(chuàng)性制作和藝術創(chuàng)作)的辨析,闡明了海德格爾如何成功地對藝術(對應創(chuàng)作)和手藝(對應包含原創(chuàng)性制作在內(nèi)的制作)進行了區(qū)分,從而確立了自己獨特的藝術概念。
四、藝術與真理的其他發(fā)生方式
我們現(xiàn)在可以確定,根據(jù)海德格爾獨特的藝術概念,真正的藝術作品(在這樣的作品中,存在可以被稱為真理的突出發(fā)生方式的藝術)需要滿足兩個條件:(1)創(chuàng)造性地開啟一個使具體的存在者得以存在其中的世界;(2)它本身單純僅為了這種開啟而存在。一件制成品如果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就是一件藝術作品。其中,(2)隱含于(1)之中,因為根據(jù)上文的分析,如果一件制成品服務于其他目的,那么其中發(fā)生的真理就已經(jīng)不是原始的真理。
下面我們來分析根據(jù)海德格爾這種獨特的藝術概念,作為真理的突出發(fā)生方式的藝術與本文開頭所提到的真理的其他四種發(fā)生方式之間的關系。它們被表述為:
真理現(xiàn)身運作的另一種方式是建立國家的活動。真理獲得閃耀的又一種方式是鄰近于那種并非某個存在者而是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的東西。真理設立自身的再一種方式是本質(zhì)性的犧牲。真理生成的又一種方式是思想者的追問,這種作為存在之思的追問命名著大可追問的存在。〔33〕〔34〕
根據(jù)這段文字,可以明確的一點是,海德格爾將真理的這四種發(fā)生方式都看作藝術之外的方式[他的用詞是“其他的”(andere)],問題是他在何種意義上將這四種方式作為藝術之外的方式。
學者對這四種方式的具體含義進行了一些猜測。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認為,建立國家的活動可以指伯里克利在希波戰(zhàn)爭后的廢墟中重建雅典,或許也可以指希特勒所做的類似事情;鄰近于最有存在特性的存在者可以指摩西代表希伯來人完成與上帝的立約;本質(zhì)性的犧牲可以指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思想者的追問可以指哲學家通過引入新的詞語(比如主體/客體、自主)而進行思考,因此,思想者實際上也包括革命性的科學家,如伽利略和愛因斯坦。〔35〕哈里斯基本同意上述觀點,不過他認為本質(zhì)性的犧牲也可以指人的自我犧牲,如一戰(zhàn)士兵為自己的家園而犧牲。〔36〕根據(jù)這些解讀,真理的這四種發(fā)生方式可以被粗略地理解為政治的(對應建立國家的活動)、宗教的(對應鄰近最有存在特性的存在者和本質(zhì)性的犧牲)和哲學的(對應思想者的追問)。
海德格爾的相關論述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他經(jīng)常將藝術(尤其是詩歌)、建國、宗教和哲學相提并論,相應地,他也會將藝術家(尤其是詩人)、建國者、宗教領袖和哲學家相提并論。比如,海德格爾將詩歌、藝術、建國與宗教都看作精神的力量。〔37〕再比如,海德格爾還宣稱,詩人、思想家和建國者是“真正的創(chuàng)造者”,他們“真正創(chuàng)立并奠定了一個民族的歷史性此在”。〔38〕海德格爾有意無意地將藝術與其他幾者相提并論暗示它們作為真理的發(fā)生方式可能具有同等地位,特別是海德格爾的如下闡述:
這里所指的斗爭是原始的斗爭;因為它讓那些斗爭者首先如此產(chǎn)生。……斗爭首先籌劃和發(fā)展了未聽過的,以及迄今為止未說出的和未思考的東西。然后這個斗爭由創(chuàng)造者,由詩人、思想家、政治家承擔起來。他們向壓倒性的力量扔出作品作為抗衡,并且在作品中捕獲因此而打開的世界。〔39〕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海德格爾認為詩人、思想家、政治家(我們也可以將其擴展至宗教領袖)都可以通過作品(Werk)使存在者(即“斗爭者”)以及存在者所屬的那個世界通過類似于斗爭的方式被開啟,即滿足藝術作品的條件(1),這與他在《本源》中把藝術理解為作為世界與大地的爭執(zhí)被置入作品的真理的思路是一致的。另外,這種斗爭并不服務于任何其他目的,而只是單純?yōu)榱舜嬖诙M行的斗爭,因此,這種斗爭是“原始的斗爭”,海德格爾在《本源》中也稱之為“原始爭執(zhí)”(Urstreit)〔40〕即滿足藝術作品的條件(2)。
根據(jù)以上分析,既然真理的其他四種發(fā)生方式完全滿足海德格爾獨特的藝術概念所要求的兩個條件,海德格爾在何種意義上將這四種方式作為藝術之外的方式呢?筆者主張,海德格爾之所以談論藝術之外的真理的“其他”四種發(fā)生方式,是因為他要從當今流行的藝術概念框架下被作為藝術的東西和被作為政治、宗教、哲學的東西中提取在他獨特的藝術概念框架下可以被作為藝術的東西,簡單地說,他實際上涉及了兩個不同框架下的藝術概念。
根據(jù)當今流行的藝術概念,我們將繪畫、雕塑、詩歌等稱為藝術作品,而將真理的其他發(fā)生方式看作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總之是與藝術無關的。但是,根據(jù)海德格爾獨特的藝術概念,我們可以看出藝術與真理的其他發(fā)生方式實際上無法做出實質(zhì)性區(qū)分,凡是能夠創(chuàng)造性地開啟一個世界或者說有原始的真理在起作用的事物在海德格爾看來都是(藝術)作品。如此一來,海德格爾所謂的藝術作品既可以包含一般意義上的藝術作品,也可以包含某些我們一般不認為是藝術作品的作品,如建國者開創(chuàng)的國家,耶穌開創(chuàng)的基督教和哲學家的思想著作。
最后,讓我們來回應本文開頭提到的楊的觀點,即海德格爾擴展了藝術概念。〔9〕筆者主張,與其說海德格爾擴展了當今流行的藝術概念,不如說他從另外的角度重新確立了藝術概念。如果他沒有在當今流行的藝術概念框架下來討論藝術,也就不能認為他提出的藝術概念是對現(xiàn)有藝術概念的擴展。根據(jù)海德格爾獨特的藝術概念,真理單獨地規(guī)定著藝術的本質(zhì),真正的藝術作品必須造成使具體的存在者得以存在其中的世界的開啟。顯然,根據(jù)這種理解,并非所有在一般流行意義上藝術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活動都可以作為海德格爾意義上的藝術創(chuàng)作。聯(lián)系上文提到的德雷福斯和哈里斯對真理的其他發(fā)生方式的解讀,不論是伯里克利、摩西、耶穌,還是眾多思想家,他們都在某種意義上為特定人類群體(如一個民族)進入其歷史性此在開了先河(開啟了一個世界),而一般流行意義上的藝術作品中的某些(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偉大藝術作品)對人類產(chǎn)生的影響并不亞于上述事業(yè)。在海德格爾看來,恐怕只有這樣的作品才有資格被稱為藝術作品。至于德雷福斯提到的希特勒和哈里斯提到的“為家園而犧牲的一戰(zhàn)士兵”,〔41〕或許前者使海德格爾曾以為他將為德意志民族開創(chuàng)一個全新的世界,而后者為了家園而犧牲雖然也很偉大,但他們希望守護和維持的家園顯然屬于已知的世界。正是基于如此嚴格的標準,海德格爾才會(繼黑格爾之后)談論當今時代中藝術的死亡,但也要看到的一點是,藝術復興的希望也正在于此,而海德格爾在《本源》中意圖通過對藝術的正本清源來為此復興做好準備。
五、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首先討論了海德格爾如何通過對古希臘的技藝概念的借鑒和發(fā)展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概念。根據(jù)這種獨特的藝術概念,藝術作品能夠創(chuàng)造性地開啟一個世界,因此,藝術是真理的一種突出的發(fā)生方式。本文接著討論了從海德格爾的藝術概念框架出發(fā)如何看待在當今流行的藝術概念框架下的藝術作品和其他作品,從而徹底地澄清了在海德格爾那里藝術與真理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具體而言,無論一件作品是通過什么形式(比如繪畫、舞蹈、哲學思考、政治實踐和宗教儀式)表達的,只要該作品能夠使得一個全新的世界開啟和存在(或者說使得真理發(fā)生),它就是一件(好的)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