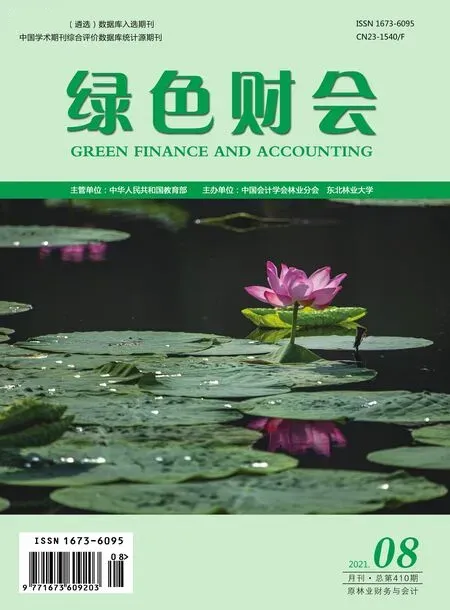實證檢驗資產價格泡沫*
○浙江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張文珂 張芳芳
新冠疫情以來,各國都實施了經濟刺激措施,各種資產價格飆漲,但生產、制造和消費仍處于極大的不確定中。資產價格與風險同時上升的疊加效應讓人們越來越多的質疑資產價格存在嚴重的泡沫。資產價格泡沫是經濟危機爆發前的典型現象,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帶來的危害遠遠超出實體經濟的承受能力。但是,在歷次經濟危機爆發前,學者們都沒有能夠準確的判別資產價格泡沫。如何實證檢驗資產價格泡沫是各國學者面臨的重要難題。
目前,同時采用“bubble”和“test”在美國經濟學會數據庫EconLit中進行標題搜索,能搜索到的實證檢驗文章有100多篇。除此之外,采用其它方法還能搜索到研究泡沫事件的一系列實證案例分析。相關的研究涉及到房地產泡沫、金融危機泡沫和網絡科技泡沫等方面,根據所研究的問題各不相同,采用的方法包括Chow檢驗、協整(共積)檢驗等一系列種類。美國《財務金融研究評論》雜志社舉辦了“關于2008年金融危機泡沫”的研討會,其中烏陶帕爾·巴塔查里亞和于曉筠(2008)[1]在他們的綜述中指出,投資者在事前對于泡沫的存在性不可能達成一致的看法,否則泡沫就不可能存在了,投資者頂多在事后發現泡沫確實存在。客觀上,泡沫的形成與崩潰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否則該泡沫不可能真正顯現出“原形”。崩潰是泡沫的必須動作,否則不能完整的觀測到泡沫現象。實證分析中,對于泡沫的分析都是典型的事后分析,對于泡沫檢驗的技巧也是智者見智。
一、房地產泡沫的檢驗與次貸危機
次貸危機被認為是由房地產泡沫造成的。次貸危機發生后,關于房地產泡沫的研究一直都是熱點。巴拉·阿賢帕里和威廉·納爾遜(2008)[2]運用時間序列協整(共積)關系檢驗的方法證實了美國在2000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三季度期間快速上升的房產價格存在價格泡沫的現象,協整(共積)關系檢驗充當了預警分析的作用。他們通過對美國全國房價指數的實證分析表明失業率指標對房價的影響并不穩定,在某一階段具有緊密的影響關系,而在另一些時段則不具備某種聯系。而且,他們發現房價與按揭利率也出現了協整(共積)關系不穩定的現象。相比之前學者對失業率、收入、按揭利率與房價具有某種協整(共積)關系的研究和檢驗,他們認為協整(共積)關系檢驗從反向思考的角度說明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前房價與某些關鍵指標之間已經脫離了一般正常的平行關系,這是危機到來的前奏。當房價脫離了對基礎價值起決定性作用的影響因素時,房價泡沫就形成了;維亞切斯拉夫·麥克德和彼得·冉姆希克(2009)[3]采用面板數據的單位根和協整(共積)方法檢驗了美國23個大都市在1978—2006年間可能存在的房價泡沫,通過檢驗房價與租金比率的平穩性得出在美國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及90年代末至金融危機以前存在房價泡沫現象,這種方法尤其適用于當房價和租金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情況下的分析。另外,通過對比房價指數與基礎價值即租金現金流的關系,他們認為,當房價非平穩。而租金現金流平穩時,也表明存在房價泡沫。
二、20世紀末網絡科技泡沫的檢驗
羅伯特·巴特利奧和保羅·舒爾茨(2006)[4]對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發生的網絡科技泡沫與期權的作用關系進行了研究,實證分析發現了與其他學者不相一致的研究結論,結果表明賣空約束限制并不是促使泡沫產生的原因。他們分別從賣空約束是否嚴重影響股票價格、投資者在泡沫期間的賣空成本是否可控開始分析,發現網絡科技股票的套利機會少的可憐,泡沫期間的賣空成本也非常低,最終認為科技泡沫是由于投資者對于網絡科技行業的增長預期過于樂觀造成的;馬庫斯·K.布倫納邁爾和斯蒂芬·納高(2004)[5]認為套保(對沖)基金在市場泡沫過程中的作用并沒有起到抑制泡沫形成的市場穩定作用,而是通過利用泡沫的形成與崩潰過程牟利,套保(對沖)基金在網絡科技類投資上的優異表現說明了這一點。作為理性投資者,套保(對沖)基金在泡沫形成與破滅過程中是順勢而為的積極參與者,并沒有起到傳統有效市場中假設的維護者作用;而尼尚特·達斯等(2008)[6]認為共同基金的激勵合約有助于減少基金經理人持有泡沫證券的羊群行為,研究結論的獨特之處在于,其認為激勵薪酬合約對于抑制資本市場中的泡沫現象具有積極的意義,激勵合約使得基金經理逆勢操作,避免動物行為;彼得C.B.菲利普斯等(2011)[7]采用了單位根檢驗和遞歸回歸方法分析了非理性繁榮引致的價格泡沫,應用于20世紀70年末至21世紀初的納斯達克綜合股價指數分析,檢驗了市場中存在的網絡科技泡沫現象。他們發現,1995—2000年間股價的ADF檢驗t統計量嚴重偏離股利的ADF檢驗t統計量,該股價和股利都是考慮通貨膨脹和取對數后的標準化數據,研究結果確定了泡沫發生和崩潰的具體時間,通過滾動回歸進行穩健性檢驗也得出了相一致的研究結論;湯姆·殷石底德和本特·尼耳森(2012)[8]運用增加隨機游走和共爆隨機項的方法擴展了向量自回歸模型,通過對均衡修正形式的重新參數化得到了二元共爆的向量自回歸檢驗方法。他們所設定的股價爆發項有助于檢驗真實市場中理性泡沫現象,對1974年后美國股市標準普爾指數達到谷底至千禧年網絡科技繁榮之間的資本市場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存在理性泡沫。
三、多樣化的檢驗方法與檢驗目的
一些學者通過多樣化的實證檢驗方法判定泡沫的存在性。奧利維爾·J.布蘭卡德和馬克·W.沃森(1982)刻畫了泡沫的形成條件、經濟后果,同時分析了泡沫實證檢驗的可能性[9]。他們設計了一個泡沫檢驗的實證方法,令原假設為不存在定價泡沫,如果統計量顯著則拒絕原假設表明可能存在泡沫。通過對泡沫之源的殘差項進行分析,目的在于觀察泡沫的新擾動項對于理性預期模型中所設想的方差邊界是否存在突破。方差邊界的突破除了可能存在的泡沫原因外,也可能是投資者非理性造成的。而事實上,投資者非理性也是泡沫產生的一個很重要原因。他們也認識到所設計的統計量其檢驗效力不足,方法還有待于改進,但他們通過設計統計量檢驗泡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啟迪性,這種啟迪性的檢驗思想后來被許多學者所采納。基思·布萊克本和馬丁·索拉(1996)采用馬爾科夫轉換機制及其擴展模型對泡沫進行檢驗,在剔除基礎價值因素的基礎上通過殘差項分析泡沫,該方法有助于股票市場價格中基礎價值與泡沫價格的區分,也有助于刻畫那些反復波動起伏的泡沫現象[10]。基思·布萊克本和馬丁·索拉(1996)以20世紀20年代德國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泡沫為例,通過對時間序列殘差進行一步向前Chow檢驗、基礎加泡沫方程的聯合估計、馬爾科夫轉換濾波等方法分析是否出現了泡沫形式的結構突破,統計結果表明接受泡沫存在的原假設。基于奧利維爾·J.布蘭卡德和馬克·W.沃森(1982)的研究模式,約爾格·布瑞敦和羅賓遜·克魯斯(2013)通過修正Chow檢驗得到最小LM-Chow統計量,與基思·布萊克本和馬丁·索拉(1996)的研究相類似檢驗了泡沫結構的突破,并以美國納斯達克100指數和香港恒生指數的例子為基礎進行了分析,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溫和爆發的自回歸過程存在顯著的結構突破[11]。烏利齊·霍姆和約爾格·布瑞堂(2012)認為結構突破的Chow檢驗在一系列檢驗理性投機泡沫的方法中最有效,在以美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海證券交易指數、香港恒生指數等為例的時間序列分析中都發現了泡沫現象。結構突破的檢驗方法本質上也是相對分析方法,是價格泡沫相對爆發時數據結構的相對改變,是相對非泡沫股價的隨機游走狀態具有自回歸參數的結構突破,這種結構突破對于泡沫的形成具有指標意義[12]。
肯尼思·D.韋斯特(1987)采用豪斯曼設定檢驗的方法來推斷投機泡沫的存在性。首先通過不同的途徑構建計算預期現值的模型進而得到兩組參數集,其中一個參數估計集來源于股價對于股利的回歸參數,另一個參數估計集通過對套利方程和ARIMA方程進行動態線性理性預期檢驗得到,然后采用豪斯曼設定檢驗比較兩組估計的參數結果是否一致,當兩組參數估計的結果存在較大差異時表明存在資產定價泡沫[13]。同時以標準普爾500指數和道瓊斯指數為對象進行了案例分析,豪斯曼設定檢驗拒絕了參數一致的原假設,驗證了投機泡沫的存在性。并指出其檢驗結果在使用固定折現率和時變折現率時會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結論,時變折現率下的研究結果變得更加模糊。可以簡單認為,采用時變折現率時,模型本身兼顧了預期收益受投資者過度反應等情緒影響的短期波動性,泡沫效應被相對客觀的厘清和限制,此時得出的結果即使否定了泡沫的存在性,也應當是更為穩健和保守的結論。他的研究從一個側面說明,采用更為復雜的時變參數模型和非線性模型更有利于得出一個客觀有效的結果,傳統的固定參數模型和線性模型由于不能夠很好的刻畫出市場行為而最終影響實證檢驗的效力。
喬治·W.埃文斯(1986)通過非參數方法驗證是否存在持續的非零超額投資收益,以1981—1984年間,按美元計價的英鎊匯率為例檢驗投機泡沫,結果表明英鎊匯率存在平均為負的異常超額收益,出現負投機泡沫的結果表明泡沫可以是正向爆發的形式也可以是負向爆發的形式[14]。后來,他又提出了爆發性泡沫檢驗中存在的問題,認為傳統時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協整(共積)檢驗等不能檢測出平穩的理性泡沫、周期破滅的泡沫[15]。而斯蒂芬G.霍爾等(1999)針對喬治·W.埃文斯(1991)所提出的問題給出了一套可行的實證檢驗辦法,他們建議采用基于馬爾科夫機制轉換的廣義ADF檢驗方法,并給出了具體的實證分析例子[16]。通過時間序列的檢驗和分析,斯蒂芬G.霍爾等(1999)將阿根廷1983—1989年間惡性通貨膨脹背景下的物價水平與貨幣供給量、匯率水平進行作圖對比分析,得出了發生于不同階段的物價水平泡沫、匯率泡沫等,甚至可以通過某些序列同時發生的泡沫現象解釋物價水平泡沫發生的原因。他們的研究不僅提供了傳統時間序列單位根檢驗中無法檢驗隨機泡沫的解決方法,更重要的是為爆發性理性泡沫的實證檢驗提供了一種相比較的圖形分析思路。這為本文從相對定價泡沫角度分析泡沫產生的原因或排除與所研究問題無關的基礎性泡沫因素提供了一種參考。
四、是理性泡沫還是非理性泡沫
關于泡沫危機中的理性與非理性行為也是研究的重點。彼得·特明和漢斯-約阿希姆·沃斯(2004)基于霍爾家族銀行在英國南海泡沫危機中的投資交易數據,通過案例研究分析了處于信息優勢地位的投資者在泡沫形成與崩潰中的角色和作用,發現信息優勢投資者并未采用賣空機制套利反而利用投機泡沫獲利[17]。他們得出了與其他學者不相一致的研究結論,認為并非賣空約束或者代理問題影響了信息優勢投資者的市場操作,也沒有證據表明廣大投資者相對于信息優勢投資者在泡沫是否高估方面存在判斷失誤,而在泡沫的形成與崩潰的過程中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投資者情緒,理性的投資者都具有合群傾向而不會有背離市場的羊群行為,因此泡沫的產生、發展直至崩潰都是和投資者群體的集體行動密切相關。對于英國南海泡沫的研究文獻中,也有學者著重分析泡沫危機中非理性的投機行為,如理查德·S.戴爾等(2005)采用協整(共積)、誤差修正模型的方法分析南海公司的股價與認購價格的關系,并對其它定量研究中認為南海泡沫是理性泡沫的研究結論提供了質疑的證據[18]。
克里斯·布魯克斯和阿波斯托洛斯·卡查利斯(2003)對倫敦證券交易所可能存在的理性投機泡沫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過程中采用了三類檢驗方法包括股利與價格之間的協整(共積)關系檢驗、波動性的方差界限檢驗和泡沫溢價的規格檢驗,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不存在泡沫的原假設不成立[19]。他們采用的方法與傳統的方法相比在動態描述折現率、股利增長率等方面具有一些優勢,而這些因素都直接決定著證券基礎價值大小。直接通過現金股利收益無法準確計算出股票的內在價值,注意到克里斯·布魯克斯和阿波斯托洛斯·卡查利斯(2003)所采用的現金股利收益率是經過股票收盤價調整計算的內在隱含的真實年度股利水平,作者巧妙的通過股票收盤價調整修正了計算缺陷。
五、關于否定價格泡沫的檢驗
也有一些學者通過統計檢驗方法否定了歷史上某些公認的泡沫現象。例如,哈希姆·杰日貝克希和阿斯利·德米爾-古克(1990)針對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的資本市場長期數據檢驗了投機泡沫的存在性,結果表明不存在泡沫的原假設成立[20]。R.格倫·唐納森和馬克·卡姆斯特拉(1996)對傳統的計算證券價值的股利增長模型進行了更為靈活的改變和調整,假設股利序列的增長率g和折現率t都是可測算的時變序列。他們認為證券基礎價值是股利變化因子λ連乘多項式的期望值,其中股利變化因子可以通過ARAR-ARCH-ANN模型和蒙特卡洛模擬計算得到[21]。在20世紀20年代經濟危機爆發之前,人們由于當時的信息條件所限只能給予證券基礎價值以較高的評價,當1929年接受到新的信息時人們自然調低基礎價值預期,股票價格伴隨基礎價值預期的下滑而陷入崩潰,據此得出了經濟大危機中不存在泡沫的結論。顯然,股利現值隨投資者的預期改變而改變是眾多同類證券基礎價值分析或泡沫分析模型的基礎,同時也是股利現值模型最大的缺陷。證券的基礎價值應當是客觀存在的并且可以估算的,而不是主觀設定的。從模型分析上,R.格倫·唐納森和馬克·卡姆斯特拉(1996)所運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結論都具有參考意義,但從理論意義上,他們的研究違背基本的現實邏輯,沒有解釋現實的經濟現象,僅將市場泡沫歸結于市場預期,缺乏客觀的物資基礎和理論支持。而沒有客觀的物資基礎就必然存在泡沫,這是R.格倫·唐納森和馬克·卡姆斯特拉(1996)文中所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上述分析中,對泡沫的實證檢驗一部分是基于對市場價格與預期現金流現值偏差的分析,另一部分是對市場價格及其收益率的時間序列進行分析。假設對于預期現金流的估計是準確的,那么對股票基礎價值大小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因素是折現率水平。該折現率水平又稱投資者必要報酬率,是市場中同等現金流水平涵蓋同等證券投資風險的投資者最低收益率水平。該折現率相當于均衡資產定價模型中股票的必要投資收益率水平。預期現金流現值與必要收益率是相匹配一致的,理論上對投資者獲得的超過投資者必要收益率水平的超額收益率進行分析檢驗與檢驗預期現金流現值的偏差是殊途同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