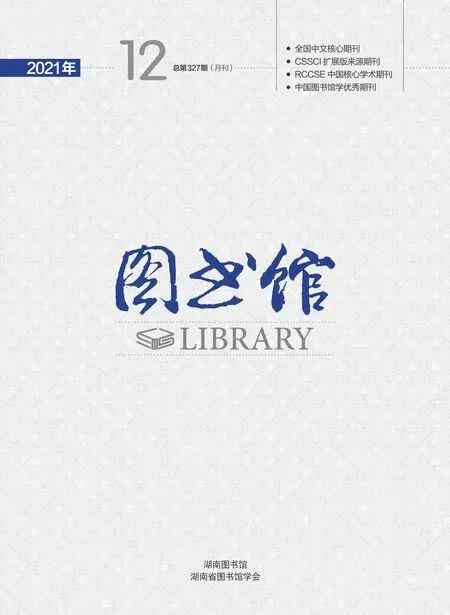國外組織信息文化研究進展及啟示
呂文婷
(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武漢 430062)
在信息社會,信息管理已成為組織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良好的信息管理可以提高組織效率,對于確保公共組織的透明度至關重要。為了加強信息管理,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公共機構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形成了一系列信息管理系統、標準、制度等。然而,即便如此,許多組織仍然認為信息管理極具挑戰性,很難實現高效的信息管理,這說明有其他潛在的隱性因素正影響著組織信息管理[1]。針對這一問題,相關學者的研究表明,“人”的因素對于信息管理的影響很大,組織成員對于信息和信息管理的認知、態度、觀念、行為也是影響信息管理的重要因素,這就涉及文化和哲學態度[2]66-94。因此,“文化”這一極具人文意味的概念進入了信息研究者的視野。
我國學者通過文獻調查指出,國外信息文化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蘇聯和美國,并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興盛,我國對信息文化的探究在20世紀90年代也得以逐步展開,但多數限于對企業信息文化的探索[3]109-126。國外的信息文化研究范圍較廣,涉及國家和社會層面[4]1-11,[5-6]、組織層面[7]93-106,[8]2-12以及個人層面[9-10],其中,組織層面的信息文化(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culture,以下簡稱OIC)是重點研究領域。筆者以“information culture”為主要檢索詞在Web of Science、LISA、Elsevier ScienceDirect、Emerald等數據庫中進行檢索(檢索日期:2020年12月30日),首先根據初步檢索結果對檢索詞進行調整和組配以進行擴檢,以了解信息文化相關研究的全貌,再逐一排查組織層面而非國家或個人層面的信息文化研究論文,剔除有關信息素養、信息文化教學等不相關文獻,最后得到文獻近百篇。根據檢索結果,最早的文獻發表于1985年,該文初步探討了各類企業中的信息文化[11],但未對后續研究產生重要影響。其他各時期具有代表性的OIC研究成果如表1所示。文章對國外組織信息文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回顧和分析,以期為我國信息文化和組織管理的相關研究和實踐提供思路。
1 信息文化定義及內涵
“文化”是一個極為復雜的概念,而“信息”的概念本身也具有多義性和延展性。時至今日,雖然國外信息學界對“信息文化”的定義始終沒有定論,但是從概念理解的變化過程可以窺見OIC研究范疇的演變趨勢。雖然多數研究中明確定義的是“信息文化”而非“組織信息文化”,但是由于這些研究都在某個或某類組織的范圍內展開,它們對“信息文化”這一概念的理解也體現了OIC的研究主題和范疇,同時也反映出OIC在信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
1.1 作為組織環境的信息文化
從檢索到的文獻來看,信息文化的概念最早源于組織管理研究。20世紀80年代,Schein[12]7-22首先提出組織文化的概念,他將組織文化定義為一個特定團體在其探究外部適應和內部整合問題時提出、發現或發展的一種基本的假設模式,該模式已經得到良好運作并認為是有效的,并因此被傳授給新成員,作為對這些問題的正確感知、思考和感受的方式[22]。文化理論家Alvesson將文化定義為“行為、社會事件、制度和過程發生與被理解的環境”,而組織文化應指“作為一種對文化及其象征性現象產生濃厚興趣的思維方式的總括概念”[23]。結合組織文化的相關研究成果來看,Ginman首先對組織內的信息文化展開了研究,并提出了信息文化的概念,即“智力資源的轉化與物質資源的轉化并存的一種環境”,“這種轉變的主要資源是各種各樣的知識和信息,所取得的成果是一種經過加工的智力產品,這是實踐活動發揮作用和積極發展所必需的”[7]93-106。Ginman通過對39位CEO的訪談進行分析,發現CEO的信息文化、企業生命周期以及對信息的興趣和使用之間存在著聯系,高度發達的信息文化與組織實踐有著積極的聯系,這些實踐促成了成功的經營效果[16]。信息文化可以被看作是個體的信息行為,它是由組織環境即文化所塑造的;信息文化是一個戰略目標,應該像改造物質資源一樣進行規劃。
1.2 信息文化與組織文化相互影響
Ginman的結論為后來的OIC研究奠定了基礎,21世紀以后,國外信息學界對信息文化開展了更為全面的討論。Widén-Wulff認為信息文化是整個組織文化的一部分,因為依附于信息的價值觀和態度取決于組織的情況,信息文化與正式信息系統(技術)、共同知識、個人信息系統(態度)和信息倫理有關[13]5。Curry和Moore認為,人們通過信息文化可以認識到信息在實現運營和戰略成功方面的價值和效用,在這種文化中,信息構成組織決策的基礎,信息技術被普遍應用,成為有效信息系統的促成因素[14]91-110,他們把組織文化作為研究的起點,因為信息文化不會存在于真空中,它需要一個先進的組織文化來培育,而且信息文化與組織文化的相互重塑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直持續到信息文化的實踐成為規范。Martin等使用信息文化方法來探索業務與IT之間的差距,認為信息文化是一種“意義共享的體系”,具體體現在“通過人員、流程和技術制定的正式和非正式信息體制中”[24]。這些定義都描述了信息文化與組織文化的關系,認為信息文化的發展與組織內信息制度、信息技術、信息倫理等因素的變化息息相關。
1.3 組織信息文化具有廣義性
Zheng所認為的信息文化具有更豐富的內涵,他指出信息文化是“在社會集體中訪問、理解和使用信息的一般能力、觀點、規范和行為規則”,隨后對概念進行了進一步解釋:一方面,他認為信息文化不能被創造或建立,它深深植根于歷史和社會環境,會隨著時間推移不斷發展,組織內的信息文化可以通過適當的管理和制度制定來培養、發展或塑造;另一方面,技術系統雖然可能對信息文化的分析十分重要,但它并不屬于信息文化的一部分,因為技術的使用方式不僅反映信息文化同時也受到信息文化的約束,而且,無論是否使用了信息技術,信息文化都將存在[4]1-11。Douglas通過定性研究和數據分析提出了信息文化的定義,認為它是一個能夠影響組織中信息使用方式的新興的價值、態度和行為的復雜系統,它存在于組織文化和更多元的環境中,并反過來受其影響[25]48-59。Oliver和Foscarini承認信息文化具有普遍性,認為它是與信息相關聯的行為和價值,特別是在組織環境中,但與具體的組織類型無關(因此包括工作場所和其他社群團體)[8]2-12。Oliver在其研究中還指出,賦予信息的價值觀和對信息的態度是組織環境中信息文化的指標……這些價值觀和態度很可能是由國家、職業和企業組織文化各個層面內部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26],反映出總體社會信息管理框架以及對信息的態度和價值觀。以上研究中提出的信息文化定義相比之前都更有深度,跳出了信息技術和組織層面的圈子,強調國家、社會和歷史因素的影響,更具包容性。
2 信息文化對組織管理的影響
這一研究主題主要討論了信息文化與組織管理的關系,即信息文化如何影響組織管理效果,從而實現良好的組織管理。其中一些研究對各類組織類型具有普適性,如Widén-Wulff等論證了信息文化與組織協作信息行為之間的關系[13]5,其他多數研究成果聚焦于某種具體的組織類型,早期成果多見于企業等商業性組織,后來也涉及政府等公共組織。
2.1 信息文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1995年,Grimshaw與大英圖書館研究與發展部合作進行了一項實證研究,旨在確定信息文化與商業發展之間是否存在相關性。研究結論指出,信息的質量和價值、來源、管理和交流對組織的發展至關重要,良好的信息管理能使組織具有更強的競爭優勢。該研究提出了組織文化的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反映了共同的價值觀,如重視金錢、創新或員工的幸福感;第二個層次則與群體的行為規范有關,如一個組織的行為模式或風格,組織中的人們交流互動或著裝的方式[27]。H?glund以一家制藥公司為案例,研究了信息文化、組織氛圍、信息服務質量和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他將信息文化定義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涉及信息和信息服務的價值評價,并認為強調信息問題和開放溝通環境的企業文化可以提升企業業績[28]。Widén-Wulff考察了15家芬蘭保險公司的信息文化,她關注組織內部的信息流動,探索多元的信息文化和有效的知識創造與企業績效相聯系的因素,具體包括信息環境、作為資源的信息、工作流程、創新能力等[13]5。Choo等認為信息文化是一種體現信息在組織中的重要性以及使用行為和價值的社會傳播模式,他們以加拿大的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為案例進行了研究,認為組織應該在忙于制定、實施策略和制度的同時重視信息文化,信息價值和信息文化將始終對人們共享和利用信息的方式產生決定性的影響[29]491-510。Liu等的研究指出,企業信息文化是企業工程成功運作的關鍵,良好的企業信息文化是企業工程運行的保障,而不良的企業信息文化則成為其運行的障礙,他們以企業工程為基礎,提出了基于組織學習、持續創新和知識共享的企業信息文化構建方案[30]。
2.2 信息文化對公共組織的影響
Orna通過英國貿易和工業部、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的英國畫廊、某合作銀行這三個案例研究得出結論:組織中的信息文化對信息產品(資源和服務)的管理方式及管理效果有著決定性的影響[31]。Douglas探討了西澳大利亞州政府部門對信息的價值觀、態度、信念和行為,她認為,盡管信息在所有政府部門中都很常見,但人們并不清楚這些部門與信息存在怎樣的關系、它們賦予信息什么價值,以及它們對信息有著怎樣的態度和行為。她厘清了信息文化與組織文化、信息管理和信息使用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指出信息文化是復雜的、系統的、自反的(reflexive)[25]48-59。Abrahamson指出組織的信息管理實踐及其人員的信息行為和價值觀對組織績效和具體信息使用成果的實現有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他的研究驗證了在其他領域對研究組織信息管理和信息文化理論模型的適用性,回歸分析表明,信息主動性和信息管理對信息使用效果的實現起著重要作用,并利用信息管理和五種信息行為進行的因素分析揭示了兩個新的因素:信息質量控制和主動協作[32]。
3 組織信息文化的類型與評價要素
國外OIC研究逐漸從企業不斷擴展到各種組織類型,深入探究信息文化的不同側面,找到組織中普遍存在的信息文化以及對其進行的評價,這類主題成為近年來OIC研究的重點內容。國外信息學家從不同研究側面總結了OIC類型,初步形成了OIC評價要素與標準,在參考和分析已有研究[3]109-126的基礎上,將代表性研究成果總結如表2所示。

表2 OIC類型與評價要素

?
4 信息文化與組織文件管理
文件(records,或根據不同語境譯為檔案)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信息,它與其他形式信息的區別在于,它直接形成于人類活動之中并被有意識地保存下來,記錄了人類活動的形成背景和過程。文件管理是指對文件的形成、接收、保管、利用和處置進行有效和系統的控制。文件的顯著特征不是其信息內容,而是其作為人類活動證據的憑證功能。從相關文獻來看,一些國外研究者已經認識到文化與文件管理實踐的相互影響,相關研究主題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4.1 組織信息承載信息文化
文件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它既是文化載體,又是文化產品。如Lubar認為,新技術給檔案管理者帶來了新的挑戰,因為它們不僅改變了檔案的物質性質,還改變了信息及其人們在文化中對其所處地位的理解。Lubar使用當代文化理論來思考檔案中信息、文化和技術的交集,認為元數據對于理解檔案信息至關重要。他指出,文獻檔案是產出文化的載體,文件和檔案可以反映出形成者和利用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將他們編織在一起的文化[38]。這里提到的“文化”實際上比信息文化的內涵要寬泛,簡單來說,是指在文件信息中記錄下來的隱含的文化,因此,組織文件管理也是對組織文化的管理。
4.2 組織信息文化影響文件管理實踐
信息文化對于文件管理實踐有重要作用。Sundqvist等在回顧文獻的基礎上探討了信息文化的學術話語及其與文件管理的關聯性,認為相關研究重點是如何使用、共享和傳播信息,而以文件管理為對象的研究卻很少。信息文化作為文件管理的一個分析框架,如果要充分發揮其作用,就需要一個更廣泛、更具包容性的概念,這也將豐富信息文化作為理論概念的內涵[39]。Sv?rd在她對瑞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政府組織通常有完備的信息系統和強大的法律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理解何為有效的文件管理,但他們仍然面臨著組織和文化上的巨大挑戰。Sv?rd進一步證實,不同類別的員工對彼此的態度給信息管理制造了障礙,如檔案管理員和IT人員由于被視為資源以外的障礙而被排除在外,在缺乏合作的情況下,文件無法發揮其全部潛力[40]。2007至2010年,英國諾森比亞大學開展了一項實證研究項目,提出了一套關于電子文件管理的證據體系,從三個角度設計了一個以組織為中心的架構:人,包括愿景、意識、文化、驅動力和障礙;工作實踐,包括過程、程序、政策和標準;技術方面的設計原則,以實現對文件的有效管理。調查結果證明,人的問題是最主要并具有挑戰性的。它涉及文化,哲學態度,對電子文件管理問題的認識、偏好、知識和能力,提出文件工作者必須改變工作態度,在文件管理問題上采取積極主動的做法[2]66-94。
4.3 信息文化框架
Oliver和Foscarini[8]2-12對信息文化與文件管理展開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她們基于前期的實證研究提出了信息文化框架(information culture framework,以下簡稱ICF),從文件管理的角度識別信息文化特征。信息文化框架共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深深根植于人類及其社會制度之中、極難改變的因素,包括文件的價值(人對文件的觀念和態度、文件管理基礎設施、電子文件管理系統帶來的挑戰)、信息偏好(文件中使用文字或圖片的偏好、信息共享偏好)、語言以及區域性科技基礎設施的影響;第二層是可以在工作場所獲取或拓展的信息管理知識和技能,包括信息相關技能(強調專業培訓的重要性)和環境感知要求(了解組織中的文件管理要求);第三層是最易被改變的兩個因素,IT治理和信任。ICF隨后被普遍應用于組織信息文化與文件管理的研究中,如Boamah根據ICF探討了居住在新西蘭的加納移民的信息文化,即影響加納移民信息識別、訪問、使用、共享和保存方式的價值觀、信念和行為[41]。Oliver等以澳大利亞兩所大學作為試點對ICF評價工具進行測試,認為信息文化分析在大型復雜組織中具有實用性,可以洞察行為和動機,促進組織參與者之間的反思和對話[21]175-186。
5 國外組織信息文化研究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的信息文化研究相對于國外發展稍晚,研究主題集中在社會視閾下的信息文化或信息技術影響下的信息文化,對信息文化這一概念的定義較為寬泛,具體到組織層面的信息文化研究,則以企業這一類型的機構居多,研究對象相對單一,未能認識到OIC的復雜性和多層次性。上述文獻梳理較為全面地展示了國外OIC研究的主題和內容,可為我國提供一定的借鑒和啟示。
5.1 承認OIC的復雜性
國外對信息文化定義的討論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發展過程。信息文化一詞最早在組織文化研究中被提出,研究信息文化的前提是承認信息作為一種資源或資產應受到組織的重視。最初,信息文化被理解成一種環境,這種環境塑造著組織內個體的信息行為。后來有研究認識到個體對信息的主觀感知,強調組織中“人”的因素對信息管理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人對信息的認知、觀念、態度、行為將影響其他信息管理因素的實現效果,信息文化與信息技術、信息制度、信息系統等因素一樣,都對組織信息管理產生重要影響。對OIC概念的認識由組織層面上升到國家、社會層面,有研究者指出國家歷史、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地區發展程度對OIC也會產生影響,因為任何組織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國家文化和社會文化下發展起來的,在分析OIC時不能忽略國家甚至跨國層面的因素。然而,由于研究背景和層次各不相同,即使一些研究給信息文化下了明確的定義,但至今為止,信息文化的概念仍然模糊,沒有一個學術界普遍承認的定義,它被用作通用概念,以解釋難以言明現象之間的關系,例如價值、規范、思想、行為等。但是從目前的定義來看,至少可以為我國研究拓展思路,為我國學者提供更多的研究切入點和可能性。
5.2 擴展信息文化領域研究范疇
承認OIC概念的復雜性意味著信息文化研究范疇也可以進一步擴展。從以上文獻梳理可知,信息文化與組織文化是相互交織的,信息文化既被視為整個組織文化的一部分,又受到組織文化的影響。國外學者認為,OIC是組織信息管理和績效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信息文化對信息管理實踐有著決定性影響,識別和了解組織中的信息文化以適應組織對信息服務的需求是十分必要的。他們通過不同方式提出了OIC的識別和評價要素。OIC在組織管理中的運用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可以將信息文化作為組織管理特征和績效的解釋性框架、分析和評價的工具、管理實踐的規范標準等,這對于提升組織績效、改善組織信息管理狀況、促進信息系統等新技術的應用都有積極作用。相比之下,我國OIC的研究范疇具有一定局限性,以筆者熟知的企業檔案管理領域為例,當前相關研究集中于討論如何開發利用檔案信息中的文化元素,以存留企業歷史、弘揚企業精神、激發員工歸屬感等,局限于提升企業軟實力方面的討論,而未能真正認識信息文化對提升組織硬實力的重要作用。我國學者可以將信息文化作為組織信息管理的工具開展研究,首先對我國某類型的組織展開深入調查,明確組織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其次以信息文化的多個層次為切入點進行分析,開發適用于我國OIC的評價要素和模型;最后提出可行的對策建議。
5.3 使用跨學科理論與實證研究方法
作為一個涉及“人”的研究領域,OIC研究大部分都離不開來自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跨學科理論知識。如Oliver和Foscarini在開發信息文化框架時就借鑒了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認為社會處于一種不斷變化的狀態,由于組織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他們所處的環境也隨之變化,新環境又反過來繼續影響組織的結構,因此組織與環境的相互影響是循環往復的,在分析信息偏好時,她還引入人類學家Geert Hofstede的文化維度理論作為分析的要素[8]2-12。信息文化研究要求相關學者擁有更豐富的知識結構和更敏銳的洞察力,僅從信息管理學科的角度研究這一問題不足以得到進一步的結論,必須借鑒和使用跨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另外,雖然國外OIC研究既有定性又有定量的研究方法,但利用豐富的案例進行定量分析和實證研究是主流,而我國相關研究以組織現狀描述的分析方法為主,研究結果可能帶有研究者的先驗性預設和主觀認識,且容易泛泛而談,因此,研究者應重視對定量分析及實證研究方法的使用。
6 結語
近年來國外OIC研究可為我國開展相關研究提供理論借鑒和研究動力,從多層面理解信息文化研究的影響和作用。在信息化不斷發展的今天,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多元文化世界之中,無論是組織還是個人,在行為規范、價值觀、心態等方面都呈現出巨大的差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并沒有標準和規范可遵循,這給不同文化環境下各方的理解和交流帶來極大挑戰。OIC研究為揭示組織層面上信息文化的差異提供了可行途徑,能夠幫助人們理解文化問題掩蓋下的信息管理問題,從而為組織管理者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建議。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中,我國的各類組織必然具有區別于西方組織的信息文化,因此,這一議題還有許多可供探討的空間。例如,在信息文化的視角下,組織內值得共享的信息、應該被封閉保存的信息、職能部門的協同合作、知識信息的管理、信息管理的其他軟硬件設施規劃、信息文化評價要素作用的挖掘等,這些問題將有助于豐富信息文化的概念并拓展其研究范圍,為我國信息文化和組織管理開辟新的研究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