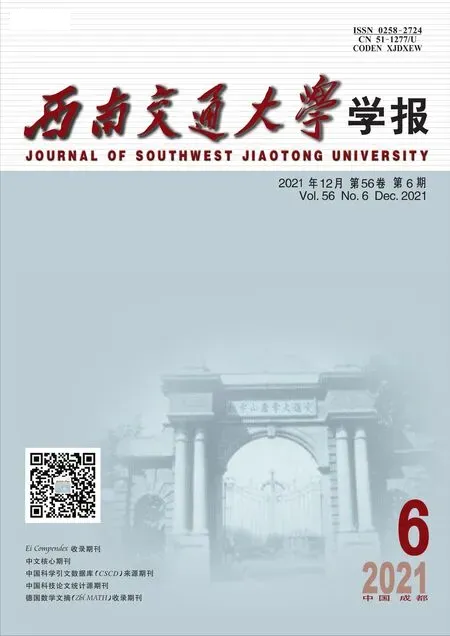深埋式樁板結構橋-隧過渡段動力響應特征分析
李雙龍 ,魏麗敏 ,2,何 群 ,2,何重陽
(1. 中南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湖南 長沙 410075;2. 中南大學高速鐵路建造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湖南 長沙410075;3. 中鐵第四勘察設計院集團有限公司,湖北 武漢 430063)
樁板結構路基通過軌道結構下鋪設的承載板與群樁基礎能夠將上部荷載傳遞至深部地基,從而達到降低路基永久沉降的目的[1-2]. 按照承載板的埋置深度進行分類,樁板結構路基可分為非埋式、淺埋式及深埋式[3]:承載板與軌道結構直接連接為非埋式;承載板上部通過基床表層與軌道結構相連為淺埋式;樁板結構埋置在路堤基底(承載板上部為填方路基)為深埋式. 詹永祥等[4]開展了非埋式樁板結構路基模型試驗,試驗表明樁基的存在加深了路基動力影響范圍;蘇謙等[5]對鄭西線某非埋式樁板結構路基的應力與沉降變形進行觀測,數據表明測點最大累計沉降僅為1.0 mm;還有其他學者[6-7]建立有限元模型對非埋式樁板結構路基的動力特性進行研究,獲得了路基動力響應(動應力、動加速度等)的空間分布;蘇謙等[8]考慮淺埋式樁板結構溫度效應,建立了溫度作用下樁板結構溫度力的計算模型.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非埋式與淺埋式樁板結構路基,而有關深埋式樁板結構路基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特別是當深埋式樁板結構路基用作過渡段時,相關報道更是少見. 上海-昆明高速鐵路江西段某工點針對橋梁與隧道之間因距離短而無法設置常規過渡段(如倒梯形過渡段)[9]的情況,首次將深埋式樁板結構路基用作該工點橋梁-隧道過渡段[10],作為一種新型過渡段,其過渡效果及動力特性值得進一步研究.
為此,本文針對該工點橋-隧過渡區(包含隧道口、過渡段及橋臺)展開現場動力響應測試,研究過渡區在列車激勵下的動力響應分布規律,并且建立考慮車輛-軌道-路基耦合振動數值模型,研究樁板結構過渡段的豎向動應力分布及過渡區列車行車平穩性,進而對過渡區線路平順性作出評價.
1 現場試驗
1.1 過渡段結構組成
所研究過渡區總長約39.2 m,過渡段長度約26.0 m,兩端分別與隧道及橋梁相連,見圖1(a),圖中:B0、S1、S2、S3 和T0 為橫向測試斷面. 過渡區地表土層為第四系全新統殘坡積(Q4el+dl)粉質黏土,最大厚度約為20.0 m,下伏二疊系下統茅口組(P1m)灰巖.
過渡段基床表層厚度0.4 m,為級配碎石填料;基床底層厚度2.3 m,為級配碎石混合5%水泥填料;基床底層以下為兩聯樁板結構,由承載板和鉆孔灌注樁組成,見圖1(b). 承載板為鋼筋混凝土結構,鉆孔灌注樁與承載板剛性連接,靠近隧道一聯采用等樁長設計,靠近橋臺一聯采用不等樁長設計,結構尺寸見圖2.

圖1 橋-隧過渡區結構概況(單位:m)Fig. 1 Schematic profile of the transition zone (unit: m)

圖2 樁板結構尺寸(單位:m)Fig. 2 Pile-plank structure (unit: m)
1.2 監測布置及數據采集
過渡區共設置5 個橫向測試斷面(B0、S1、S2、S3 和T0),里程DK722+522.8~DK722+562.0. 每個斷面測點的位置分布在上行線和下行線底座板的內外兩側、線路中心線路基表面以及路基兩側邊坡位置,見圖3,T0-2:T0 代表監測斷面,2 代表測點編號,其余同理. 測試列車包含CRH380B、CRH2、CRH380A-001、 CRH380A-6158、 CRH380AM 及DF11共6 種車型,對應列車軸重分別為16、13、14、14、15、22 t. 建立了行車自動觸發的數據采集及無線傳輸測試系統,采用891-Ⅱ型拾振器監測振動信號,891-Ⅱ型拾振器包含加速度和速度兩種檔位,加速度檔位最大量程為40 m/s2,靈敏度為0.1 V?s2/m;速度檔最大量程0.5 m/s,靈敏度為30.0 V?s/m. 利用INV3060D 型采集儀對振動信號進行采集,采樣頻率為256 Hz. 采用DASP(V10)軟件對振動速度信號進行全程一次積分可獲取動位移.

圖3 監測布置Fig. 3 Layout of monitoring instruments
2 試驗結果與分析
2.1 信號數據處理
采用阻斷頻率為120 Hz 的低通濾波和頻帶為49~51 Hz 的帶阻濾波對振動信號進行過濾[11]. 提取濾波后振動有效值進行分析,振動有效值采用式(1)計算[12].

式中:xrms為振動信號有效值;T為振動周期;x(t)為振動信號瞬時值;t為時間.
為了減小試驗人為或系統誤差,采用區間估計法統計振動信號有效值的置信區間,置信水平為95%. 然后提取上限值作為數據樣本分析不同因素對過渡區動力響應的影響.
2.2 車型對過渡區動力響應的影響
圖4 分別給出了不同車型列車在下行線行車工況下底座板測點T0-3、S3-3、S2-3、S1-3 及B0-3 振動加速度和動位移有效值的縱向與橫向分布.
由圖4 可知:相比其他車型,CRH380A-001 型列車引起過渡區的振動加速度有效值整體上更大,這是因為CRH380A-001 列車平均行車速度相比其他車型更大,所引發的路基動力放大效應更明顯. 從縱向分布來看,斷面T0 及S1 的振動加速度要比斷面S2、S3 及B0 的更大. 已有研究表明[13],列車經過軌道剛度突變區域會引發附加動力荷載,使列車及軌道路基振動更加劇烈. 由此推斷,列車下行線行車經過橋臺至過渡段的連接區域時,列車在該區域產生了附加動力荷載,進而引發斷面S1 的振動加強.


圖4 不同車型振動加速度和動位移有效值對比Fig. 4 Comparison of effective values of acceleration and displacement under different train types
DF11 車型引起的動位移有效值比其他車型更大,原因在于該車型相比其他車型軸重更大. 在橫向上,兩側底座板測點離列車荷載作用位置最近,因而其動位移都要比路基中心及兩側邊坡測點的更大.
從以上試驗結果來看,不同車型由于軸距、軸重及編組形式等不同,引起過渡區振動響應也不同,但豎向振動加速度及動位移有效值都很小,振動加速度及動位移有效值的最大值分別為0.85 m/s2、0.034 mm,表明在不同車型列車激勵下深埋式樁板結構過渡區振動水平較低.
2.3 車速對過渡區動力響應的影響
CRH380A-001 型列車以12 種車速在上行線行車. 圖5 分別給出了上行線底座板測點T0-5、S2-5 及B0-5 的豎向加速度和豎向位移有效值隨車速的變化情況.
從圖5 中可以看出:隨著行車速度的增大,隧道、過渡段及橋臺測點的振動加速度及動位移有效值也增大,表明過渡區振動水平與車速大小密切相關;由于過渡段填料相比隧道與橋臺來說,具有低剛度、高阻尼的特性,使得過渡段的振動響應與隧道或橋臺存在明顯差異,而車速的增大使得這種差異加劇,進而在縱向上過渡區的振動響應呈現如圖5 中的“V”字形分布.

圖5 不同車速列車激勵振動響應對比Fig. 5 Comparison of dynamic responses under different train speeds.
2.4 行車方向對過渡區動力響應的影響
已有研究表明[14],不同行車方向的過渡段動力響應存在明顯差別. 測試過程中,CRH380A-001 型列車在下行線分別以橋至隧、隧至橋兩個方向行車.圖6 給出了兩個方向行車條件下下行線底座板測點T0-3、S3-3、S2-3、S1-3 及B0-3 的振動響應對比.
由圖6 可知:在兩個行車方向上測點S3-3 及S2-3 的豎向加速度有效值相差不大,但測點S1-3 和B0-3 相差較大. 當方向為橋至隧時,列車由高剛度橋臺駛向低剛度過渡段過程中,引起列車對軌道及路基結構的沖擊荷載,造成低剛度區域(如斷面S1)振動加強;當方向為隧至橋時,由低剛度過渡段駛向高剛度橋臺,在橋臺附近(如斷面B0)會造成振動加強. 兩個方向上各個測點的豎向動位移有效值相差不大,主要原因為試驗車輛軸重一定,故而行車方向對豎向動位移的影響不大.

圖6 不同行車方向動力響應對比Fig. 6 Comparison of dynamic responses in two driving directions
2.5 豎向加速度變化率評價模型
振動加速度是軌道路基動力響應的重要控制指標. 本文嘗試采用豎向加速度在過渡區單位長度上的變化率η來反映過渡區振動響應沿縱向分布的變化幅度,如式(2).

式中:Δa為相鄰測試斷面間豎向加速度差值;Δl為斷面間距離.
采用豎向加速度置信水平為95%的置信區間上限值進行分析. 以下行線行車軌道板內側測點(即測點T0-3、S3-3、S2-3、S1-3 及B0-3)振動響應數據為樣本,圖7 分別給出了相鄰測試斷面間的豎向加速度(a1、a2、a3、a4、a5)差值及其變化率范圍.

圖7 相鄰測試斷面間的加速度變化Fig. 7 Acceleration changes between adjacent test sections
從圖7 中可以看出:過渡段斷面S3 至S2、S2 至S1 間的豎向加速度差值及其變化率較接近,并且都很小,表明過渡段內動力響應的分布較為均勻. 對比a1-a2與a4-a5可知,斷面T0 至S3 的豎向加速度差值及其變化率顯著大于斷面S1 至B0,表明橋臺至過渡段的平順性要優于過渡段至隧道的平順性.
3 數值分析
3.1 數值模型建立
為了更全面地揭示深埋式樁板結構過渡段的動力行為,采用ABAQUS 軟件建立考慮車輛-軌道-路基耦合作用的三維有限元模型進行分析. 整體模型由隧道段、過渡段、橋梁段組成,采用C3D8R 實體單元對軌道結構、路堤及地基進行網格劃分. LI 等[15]認為為了盡可能消除邊界效應,模型縱向邊界與輪對作用點距離應大于18 倍的軌枕間距,本計算模型在滿足該要求的前提下,同時考慮工作站性能,計算模型在x方向取42.0 m,y方向取80.0 m,z方向取31.5 m,各結構尺寸見圖1(b)和圖8(a). 樁板結構采用實體單元模擬(圖8(b)),其與土層的所有界面設置面-面接觸. 橋臺與過渡段連接處的動力響應是重點關注部位,因而建立了橋臺和簡化的單跨簡支梁模型,簡支梁縱向長度32.7 m,橋面板寬度13.6 m.

圖8 數值模型建立(單位:m)Fig. 8 Establishment of numerical model (unit:m)
采用線性彈簧-阻尼單元沿縱向按間距0.65 m(扣件縱向間距)連接鋼軌與軌道板來模擬扣件系統.應用赫茲非線性接觸理論描述輪軌法向行為,以輪對環形踏面為主面,鋼軌軌面為縱面建立接觸,采用“罰”函數考慮輪軌切向行為,摩擦系數取0.2. 計算模型不考慮軌道幾何不規則性,將軌道考慮為理想化的水平軌道. 以CRH380AM 型號列車的2 節車廂進行模擬計算以考慮相鄰轉向架引起的動力響應疊加效應,行車速度300 km/h,車廂結構尺寸見圖8(c).列車模型由車體、轉向架和輪對結構組成,設置為剛體. 本文重點關注輪軌-路基垂向的動力響應,忽略車體的橫向作用,采用簡化車軌耦合作用模型[16]. 應用賦予線性彈性-阻尼屬性的連接單元來模擬列車的二系懸掛系統,相關車輛參數見表1.

表1 車輛參數與扣件參數Tab. 1 Vehicle parameters and fastener parameters
模型四周邊界設置黏彈性人工邊界單元以防止動應力波在邊界處的反射,設置阻尼比為1.0[17],地基土層及路基層采用基于摩爾庫倫屈服準則的彈塑性本構模型,其他結構層或土層均采用線彈性本構模型,計算材料參數見表2,部分參數參考文獻[18-19]進行取值. 設置最大計算時步為2.5 ms,采用動力隱式積分法進行計算.

表2 過渡區各結構層材料屬性Tab. 2 Material properties of components in the transition zone
3.2 模型驗證
圖9 為測點S2-3 的振動響應曲線對比. 表3 給出了底座板內側測點與路基中心測點振動加速度與速度實測值與模擬值的對比. 綜合圖9 和表3 可以看出,數值模擬得到的振動峰值時間點與實測結果基本對應,并且大部分測點振動響應峰值的計算值與實測值比較接近,相對誤差基本小于30%. 不過,仍然有部分測點差別較大,如:T0 斷面底座板測點的加速度計算值與實測值相差45.6%,振動速度相差34.5%. 分析認為:隧道口測試斷面實測值可能受行車過程空氣動力影響較大,而數值分析過程中不能體現這種作用,導致二者出現偏差. 整體上,模擬結果的幅值和分布與現場監測數據較接近,說明數值分析模型的建模方法和計算參數合理可靠.

表3 模擬值與實測值對比Tab. 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umerical results and the field measurements

圖9 模擬值與實測值對比(測點S2-3)Fig. 9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umerical results and the field measurements (Point S2-3)
3.3 過渡段基床及地基動應力分布
采用驗證后的數值模型對過渡段基床及地基動應力分布進行分析,結果如圖10.
由圖10 可知:列車由橋臺駛向隧道過程中,鄰近雙轉向架引起測點的動應力比單轉向架的值要大,并且鋼軌正下方測點動應力值要比軌道中心線測點動應力值大約17.7%;結合圖10(b)可知:行車荷載在路基表面引起的豎向動應力主要分布在轉向架的正下方,大致呈“矩形”,并向軌道中心及路基兩側衰減;當輪對位于斷面S1 時,最大豎向動應力達到31.23 kPa,而位于斷面S3 時為29.14 kPa,由此可以推斷,列車由橋臺駛向過渡段時,列車對橋臺與過渡段連接處及其附近區域的軌道施加了附加荷載,造成斷面S1 動應力相比其他斷面要大,這也可能是下行線實測值中斷面S1 振動水平相比過渡段其他斷面要大的原因.

圖10 基床豎向動應力分布Fig. 10 Vertical dynamic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subgrade
為了揭示深埋式樁板結構路基及地基的荷載傳遞規律,圖11 給出了斷面S3 鋼軌正下方基床及地基土體的動應力沿深度分布規律.
從圖11 中可以看出:基床層動應力隨深度的增大而逐漸衰減,由基床表層頂面29.14 kPa 衰減至基床底層底面6.22 kPa;由于樁板結構的存在,列車荷載主要由樁體承擔,造成承載板以下的樁間土體應力很小,僅有1.93 kPa,相應動應力衰減系數僅為0.07,對比一般樁筏加固路基,相同地基深度下動應力衰減系數一般為0.10~0.20[20-21],可見樁板結構的存在能夠使淺部地基土體承受的動力作用降低,這也證實了詹永祥等[4-5]的研究結論;在樁端附近,上部荷載通過樁身擴散至樁端底部附近土體,進而引起深部土體應力增大.

圖11 基床及地基豎向動應力沿深度分布Fig. 11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dynamic stress along the depth of subgrade and foundation
3.4 過渡區線路平順性分析與評價
為了進一步揭示過渡區軌道等效剛度分布情況,采用式(3)[22]計算豎向軌道等效剛度.

式中:K為豎向軌道等效剛度;Q為列車單輪荷載,本文取值為75 kN;Z為鋼軌豎向振動位移幅值.
圖12 繪制了鋼軌豎向振動位移幅值、軌道等效剛度分布曲線. 由圖可知:最大剛度在橋臺位置,為94.7 kN/mm,最小剛度在靠近過渡段路基中心的位置,為75.6 kN/mm. 陳小平等[23]認為我國無砟軌道整體剛度在60.0~85.0 kN/mm,該過渡段路基剛度與其結論基本符合. 蔡成標等[24]認為要保證過渡區軌道具有良好的動力學性能,η(鋼軌動撓度曲線的斜率)應控制在0.300 mm/m 以內. 由圖可以計算出過渡區最大鋼軌撓度變化率約為0.149 mm/m. 可見,采用深埋式樁板結構過渡段能夠實現橋臺-隧道剛度的平順過渡.

圖12 過渡區鋼軌位移和等效剛度分布Fig. 12 Distribution of the rail displacement and equivalent stiffness in the transition zone
圖13 分別給出了列車在過渡區行車過程中車體、轉向架和輪軸的豎向振動加速度響應. 由圖可知:當列車以速度300 km/h 從橋臺駛向隧道時,由于輪-軌的動態接觸作用,輪軸振動豎向加速度變化相比轉向架和車體來說更加劇烈;受車體內部懸掛系統的減震作用,轉向架及車體振動頻率大幅降低,量值也大幅減小;由于過渡段與橋臺(或者隧道)的連接處存在剛度差異,輪軸、轉向架及車體豎向加速度在該區域出現加速度增大現象,其中過渡段與隧道連接處輪軸加速度最大,為11.77 m/s2,車體最大值0.74 m/s2. 《鐵道機車動力學性能試驗鑒定方法及評定標準》[25]規定具有優良等級舒適度的車體最大豎向加速度不應大于2.45 m/s2. 從模擬結果來看,以300 km/h 車速經過該過渡區時列車舒適度達到了優良等級,表明過渡區線路平順性良好.

圖13 列車經過過渡區時的豎向加速度分布Fig. 13 Vertical accelera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train passi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 zone
4 結 論
1) 不同車型列車激勵下深埋式樁板結構過渡區振動水平較低,過渡區振動加速度及動位移有效值的最大值分別為0.85 m/s2、0.034 mm. 受列車動力附加荷載作用,過渡段與橋臺連接區域振動水平比過渡段內其他位置振動水平更高.
2) 過渡區動力響應有效值隨車速的增大而增大,過渡段動力響應的增大幅度要比隧道與橋臺的更小. 行車方向對過渡段與橋臺連接區域的動力響應影響較大,對其他斷面影響微弱.
3) 由過渡區相鄰斷面加速度差值及其變化率可知,深埋式樁板結構過渡段動力響應沿線路縱向分布較為均勻,并且橋臺至過渡段的平順性要優于過渡段至隧道的平順性.
4) 樁板結構的存在使列車荷載能夠傳遞至深部地基,降低了基床或淺部地基土體承受的動力作用.
5) 列車以300 km/h 車速經過該過渡區時,過渡區內鋼軌撓度最大變化率小于控制值,乘客舒適度達到優良等級,表明深埋式樁板結構路基用作該橋臺-隧道過渡段時過渡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