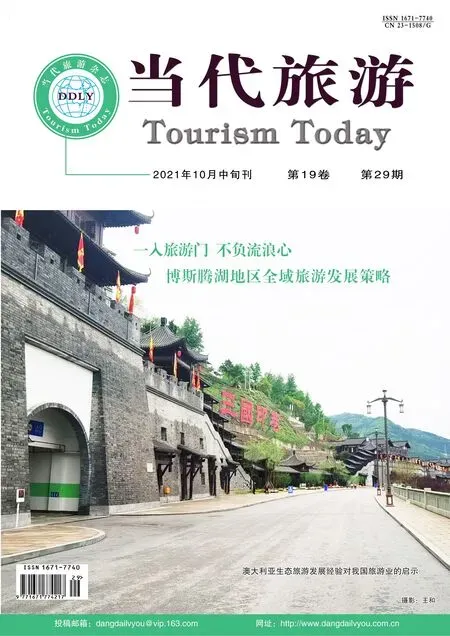基于認知地圖的鄉村旅游空間意象分析
朱妙園 彭婭婕
云南師范大學,云南昆明 650092
引言
在新型城鎮化、美麗中國的政策推動下,我國鄉村旅游得到空前發展。在發展過程中,不容忽視鄉村空間風貌發生了劇烈重構,空間更新受阻、鄉村資源衰退[1]、村民地方感喪失和鄉土情結淡漠等現象。古村落是極富“可識別性”和“可印象性” 的[2]。鄉村空間風貌不僅包含著看得見的空間景觀(建筑形式、色彩、山水格局、綠化等),還蘊含著鄉村的神韻氣質、地方的村民精神與風俗文化[3]。
一 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
問卷主要涉及個人基本信息、鄉村空間意象感知問題、鄉村空間意象認知地圖的繪制,采用頻數分析法統計并分析結果。被調查者基本信息為游客67%、村民33%;性別比例:男46%,女54%;年齡比例:18歲以下20%、18-35歲60%、35歲以上20%;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20%、高中20%、大學及以上60%;本地居民居住時長:6-12年10%、12年以上27%;出行方式:步行47%、自行車13%、電動車27%、私家車13%。
(二)認知地圖
認知地圖是對環境形象的感知和體驗,能幫助人們在記憶中對環境布局加以組織, 所具有的認知地圖越完整對行為進行選擇的余地也就越大。比較清晰完整的認知地圖,可以幫助人更加充分有效地體驗環境,使環境更加富有意義,從而為人們提供了更強的安定感和控制感[4]。調查采用分區域采集村落認知地圖樣本,選取海晏村古碼頭為中心,其半徑1km內的區域作為調查范圍,參與調查的村民和游客自主繪制其空間認知草圖。
二 海晏村概況
海晏村是云南省昆明市呈貢區大漁街道下轄村落,距昆明城區中心約30公里[5]。緯度位置為102°76′E,24°80′N。該村隔滇池與西山相望,東外側有環湖東路連接周邊多個村落及濕地[6]。國土面積為4.83平方公里,因其是緊鄰滇池的村落中保存較完整的古漁村,自2016年以來政府對古村落的保護與開發過程中被劃為昆明市的第一個歷史村落[5]。
三 海晏村空間意象因子分析
(一)空間意象因子提取
空間意象一般可分為物質意象及精神文化意象。物質意象因子提取采用凱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文中提出的五個主要元素:道路、邊界、節點、區域、標志物[7]。精神文化意象因子提取參照熊凱在《鄉村意象與鄉村旅游開發芻議》一文中提出的鄉村空間意象的內涵主要包括鄉土建筑、鄉村勞作形式、鄉風民俗、和天人合一的意象[8-9],本文主要提取建筑文化、生產文化以及宗教風俗。
(二)鄉村空間意象因子頻數分析
通過在問卷調查的方式提取海晏村各意象因子,并進行頻數分析得出以下數據。
1 區域因子
根據區域的屬性大致將海晏村的主要區域分為4個,分別是外圍農田區域、中部住宅區域、南側梅家山區域(包含陵園)以及西側滇池區域,由參與者在幾個區域中選擇印象最為深刻的區域,對其進行方位描述或指出該區域的一些標志物。最終結果顯示游客對中部住宅區域及西側滇池區域認知度比較高,對外圍農田區域及南側梅家山區域認知較低。而村民對四個區域認知度都較高,尤其對日常從事生產生活的農田及住宅區域認知度高(表1)。
2 海晏村標志物因子
該意象因子的調查依據為對問卷提供的海晏村相關標志物圖片進行辨認,并說出大致方位或名稱。其中游客和村民對古碼頭的空間意象性都最強,其次是對石板路和村口石碑的意象性較強,游客對小吃店的意象性較高,村民對標志物因子認知中石龍寺和呂祖閣的認知度最低(表1)。

表1 部分意象因子認知調查
3 道路和節點因子
該意象因子的調查依據為能指出海晏村內印象最深的道路的大致方位和其周圍的節點。村民對石板路和湖畔砂石路認知度最高,其村民頻數和比例為5和100%,而對其他巷道認知度稍低,但都居于60%~80%;游客對于湖畔砂石路認知度最高,游客頻數和比例為10和100%,其次是對石板路和入村水泥路的認知度較高,頻數及比例分別為9和90%,8和80%,而對村內其他巷道認知度最低,比例只達到10%~20%左右。村民多對多個節點認知度都比較高;游客僅對個別節點認知度高,其中對碼頭認知度最高,頻數及比例為5和100%。
4 邊界因子
該意象因子的調查依據為問卷所提供的邊界(滇池湖畔、農田邊緣、外側道路、山體邊緣)選項中選擇其所認為的村落邊界。結果顯示村民和游客對邊界的認知大都以滇池湖畔和外側道路為主。
5 文化因素
調查是否了解海晏村宗族文化、宗教信仰、祭祀文化、建筑文化或農耕文化,其結果顯示大部分居民對本村宗族和宗教、建筑以及農耕文化都比較了解,而游客僅能通過一些現象大概了解村落文化。
(三)鄉村空間意象因子重要度分析
對以上景觀進行重要度分析,選取認知比例>90%和<20%的空間意象因子,結果見圖2。其中,村民對于本村宗族、農耕、滇池、住宅及一些典型標志物的有極高的空間意象性,對小吃店及呂祖閣意象性較低(見封三圖1);游客僅對可觀光的區域及這些區域內的一些標志物有較強意象性,對村落精神文化、農田意象認知度低(見封三圖2)。

圖1 游客認知重要度

圖2 村民認知重要度
四 認知地圖分析
(一) 認知結構分析
對回收的9份認知地圖進行整理分析,刪除無效的一份樣本后,對剩余的8份草圖進行因子提取和分析。如圖1,該參與者所繪制的草圖、圖文都較清晰,在此圖中有19個因子,個別因子有圖無文,認知地圖1繪制區域與實際基本吻合,但是該參與者對海晏村石板路兩旁更外側的區域認知度極低。在其余7個樣本中,同樣有5個樣本對于外側道路兩旁區域認知度極其缺乏。僅有2個樣本涉及外側道路兩側區域。

圖1 游客有效
從幾個樣本來看,一半以上的參與者對村口—居住區—湖畔的軸線認知清晰,大部分參與者能夠較準確的畫出日常行走路線或游覽時的路線及其周圍的一些環境意象因子,雖然有部分認知地圖中有意象因子的顛倒,如圖2中祥和園大門與門口岔路口的位置是有一定偏差的,說明意識中的環境認知方位與實際方位是有差異的,但總體方向與實際空間差異較小。

圖2 游客有效
(二)認知地圖類型
阿普蘭德通過研究發現認知地圖存在順序型和空間型兩種主類型,其中順序型認知地圖以道路導向為主,而空間型認知地圖以區位導向為主[10],其中空間型還可以細化出馬賽克型認知地圖[1]。依據阿普蘭德的認知地圖類型劃分標準,本文將所回收的9份認知地圖進行了對比和分類。在9份樣本中,順序型認知地圖為5份,空間型認知地圖為4份,其中包含1份馬賽克型樣本。
(三) 不同群體認知地圖差異分析
在本文中主要通過對比不同性別、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齡、不同居住時間人群的認知地圖類型來獲取空間感知上是否存在差異的數據。此次數據統計后,回收的認知地圖中樣本數據結果,(見表2)。

表2 不同群體認知地圖差異
性別差異:從不同性別的角度看,順序型和空間型認知地圖數量差異較小。在男女比例相近的前提下,可以看出女性在空間認知上更偏向于順序型認知,且女性認知地圖中存在馬賽克型認知的情況,而男性兩種認知比例相同。
年齡差異:參與者主要是三個年齡段,其中35歲以上群體偏向于順序型認知, 18歲以下群體偏向于空間型認知,且存在馬賽克型認知地圖。18—35歲人群對兩種認知類型都存在。
文化差異:大學及以上群體空間認知地圖類型分布較平均,高中主要偏向順序型認知,初中及以下學歷兩種認知都有,但空間型認知不是很清晰。
居住時間差異:主要通過對比村民和游客的認知地圖類型分析。游客通常采用順序型認知地圖,而村民對環境較熟悉,所以更偏向于空間型認知地圖。
由上可知,認知差異受居住時間影響最大,其次是會受到年齡、學歷的影響,但是影響不大,另外,性別對認知地圖的類型也有一定影響,女性更多的是順序型認知,這可能與女性的感性認知有關。除此之外認知地圖可能還會受到出行方式的影響,但由于總體樣本較少,此類型不易對比。
五 結語
在對海晏的改造和規劃下,一些物質意象元素逐漸失去原本的樣貌,村落中許多入戶巷道、土坯房、歷史建筑已經荒廢、倒塌,無明顯指向牌,游客難以辨認,加上現代化磚瓦建筑穿插其中,整體空間景觀較混亂。使得村落的傳統精神文化意象逐漸消失,越來越少的人知道或認可村落文化,最終造成本地居民地方認同感、歸屬感逐漸降低,外來游客對村落空間意象整體感知度不高的結果。不同類型的人群對于空間的認知方式或過程具有差異,主要會受到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的影響而形成不同的認知地圖的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