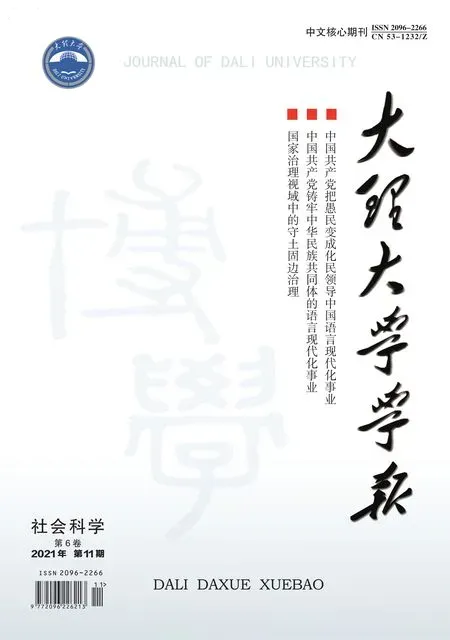白族文化負載詞的翻譯
李慶豐
(大理大學外國語學院,云南大理 671003)
隨著中外交流的日益加深,世界也越來越關注中國各民族的文化,因此,少數民族文化翻譯工作的重要性逐漸凸顯。眾所周知,文化和語言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翻譯不單純是兩種語言的轉換,更是兩種文化的交流。文化差異的轉換歷來是翻譯工作中的難點,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譯介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少數民族在漫長發展中,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其中蘊含大量的文化負載詞。“文化負載詞(culture-loaded words)是指標志某種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詞、詞組和習語。這些詞匯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積累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的活動方式”〔1〕。由于這些詞語在英語中沒有對等項,要成功地譯介少數民族文化必須先攻克這些負載詞的翻譯。同樣,白族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須先探討白族文化負載詞的英譯方法。
筆者在中國知網輸入檢索詞“白族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檢索結果為零。更換檢索詞為“白族”和“翻譯”,發現檢索結果多為在校翻譯專業學生的翻譯實踐報告,關于白族文化翻譯的研究只有3篇,其中有關白族文化負載詞英譯的文章只有1篇。尚路平在《大理白族傳統民居文化負載詞英譯研究》中認為,在翻譯白族民居相關文化負載詞時可以采用音譯加注釋、直譯加注釋的方法〔2〕。朱黎在《淺析白族龍傳說中的民俗翻譯策略》中提出了直譯、直譯加注釋、音譯加注釋等方法來翻譯白族的龍傳說〔3〕。施紅梅在《少數民族神話故事英譯的異化策略——以白族創世神話〈人類與萬物的起源〉為例》中提出了采用音譯、音譯加解釋、直譯、直譯加解釋的方法來翻譯白族創世神話〔4〕。鑒于白族文化負載詞翻譯相關的研究非常少,然而文化負載詞的翻譯至關重要,關乎白族文化向外傳播的有效性。所以,筆者將對白族文化負載詞的翻譯進行探討。
一、白族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現狀
為了解白族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現狀,筆者查閱了一些有關大理的英文版或中英雙語版書籍如Dali—AWonderful and Beautiful City、《云南特有民族文化知識》《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大理》和《大理攻略》等,瀏覽了旅行社網站(如Travel China Guide、Trip China Guide、China Highlights、中國國際旅行社、Top China Travel、亞索國際旅業等)和政府網站(如湖南省人民政府網站)等。在資料檢索過程中,筆者發現出現頻率最高的“三月街”和“三道茶”這兩個文化負載詞譯本眾多,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筆者以這兩個詞的翻譯為切入點,來探討白族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現狀。“三月街”和“三道茶”的譯本歸納見表1和表2。

表1 “三月街”的翻譯

表2 “三道茶”的翻譯
經過分析,筆者總結出在上述網站和書籍中,對于白族文化負載詞目前常用的翻譯方法有以下幾種。
(一)直譯
例如“三月街”的翻譯March Fair、March Street Festival、the Third Month Fair、The March Street都采用了直譯的方法,“三月”被翻譯為“March”或者“the Third Month”,“街”被翻譯為“Fair”或者“Street”。這樣的直譯看似與原文一致,但是如果對三月街做進一步的了解,我們就會發現,這樣的直譯是不夠準確的。三月街亦稱“觀音市”“觀音街”,于每年農歷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在大理城西的點蒼山腳下舉行,是白族傳統的盛大節日。最初它帶有宗教活動色彩,后來逐漸變為白族傳統的民間物資交流和文娛活動的盛會。“三月街”中“三月”指的是農歷的三月,如果簡單翻譯為“March”,就變成了公歷的三月,這樣是不準確的,也容易讓外國游客對于舉辦時間產生誤解。即使后文中有解釋具體舉辦時間,也會讓人對這種譯法產生質疑,為什么農歷的三月要譯為公歷三月(March),兩個歷法是不一樣的,顯然不能直譯。有的網站和書籍如《云南特有民族文化知識》將“三月”譯為“the Third Month”,看不出到底指的是農歷的三月還是公歷的三月,也不夠準確。“街”在一些網站和書中被譯為“Street”,字面上看是與“街”對應。中文里的“街”指居民區、城鎮中交通功能較完善、兩邊有房屋的、比較寬闊的道路,通常指開設商店的地方。牛津詞典中“street”的定義如下:“public road in a city,town or village with houses and buildings on one side or both sides”〔16〕1510,從該解釋可以看出它指的是兩邊有房屋的、比較寬闊的道路。然而,在“三月街”中的“街”并不是指某一條道路寬闊、商鋪林立的街道。三月街不僅是民間物資交流盛會,也是文娛活動的盛會,因為三月街不但有琳瑯滿目的各式商品,也是舞蹈、對歌、賽馬、競技的園地。從節日內容來看,“三月街”中的“街”不是單純的街道,因此不能簡單直譯為“Street”。有些網站將其譯為“Fair”,牛津詞典中的解釋如下:“market(esp for farm animals and farm products)held regularly in a particular place,often with entertainments”〔16〕519,從解釋可知,該詞包含了娛樂活動和商品交易,貼近“三月街”的內涵,比“Street”更恰當。
白族在逢年過節、男婚女嫁等喜慶日子里,或是在親朋賓客來訪之際,都會以“三道茶”來款待客人。三道茶的第一道是苦茶,將茶葉放在瓦罐里置于文火上烘烤,待茶葉焦香時倒入沸水烹煮而成。第二道茶是甜茶,開水中放入紅糖、姜末、核桃碎、米花和乳扇制成。第三道茶是回味茶,用蜂蜜加少許花椒、姜、桂皮加水烹煮而成。在一些網站和Dali—A Wonderful and Beautiful City這本書中,三道茶被翻譯為“Three Courses of Tea/three-course tea/the Three-course Tea”,這三個譯本都采用了直譯的方法,反映了白族茶禮包含三道,內涵有傳遞出去,但是原詞的發音被完全擯棄了,文化意象沒有足額傳播。
(二)意譯
在Dali—A Wonderful and Beautiful City這本書中,將三月街意譯為“Lunar-calendar-March Fair”,“三月”根據節日時間翻譯為“Lunar-calendar-March”,相對于公歷的“March”要好一些,但是這樣譯是否準確有待商榷。Lunar-calendar準確來說指的是陰歷,是根據月球圍繞地球運轉的周期制定的歷法。然而,三月街于每年農歷的三月十五開始舉辦,農歷是一種綜合陰歷、陽歷而制定的歷法,這種歷法既重視月相盈虧,又重視寒暑節氣,以月球繞地球一周的時間為一月,但設置閏月,使一年的平均天數跟太陽年的天數相符。我國的農歷就是一種陰陽歷。英語中有個詞語“lunisolar”,有道詞典app中新版牛津詞典對它解釋如下:“of or employing a calendar year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phases of the moon,but adjusted in average length to fit the length of solar cycle”,該解釋對應了陰陽歷的意思,所以農歷應該翻譯為“lunisolar calendar”。那么,三月街譯為“Lunisolar-calendar-March Fair”可能更準確。
(三)音譯
Travel China Guide網站上在喜洲鎮嚴家大院的介紹中有提到三道茶的一段文字:"Sandaocha"is a traditional regional tea ceremony consisting of three unique tea flavors,and is an experience not to be missed in Yan' s compound.The host begins by presenting a bitter tea which stands for the hardships in life.Then,a sweet tea of sesame and walnut symbolic of happiness in life.Finally,a bitter,sweet,and spicy tea symbolic of pondering life〔5〕。這段文字中譯者用音譯的方法將三道茶翻譯為“Sandaocha”,然后再解釋它的內涵。音譯是異化翻譯中最常用的一種方法,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語文化,將白族這個傳統的茶文化習俗原汁原味地介紹給西方讀者,再加上后面的解釋,能夠讓西方讀者了解這個詞語背后的內涵。《大理攻略》這本書也采用了音譯的手法,將三道茶譯為“The San Dao Cha”。觀察發現,兩個譯本雖然都采用了音譯的手法,Travel China Guide網站的譯本“Sandaocha”拼音是連寫的,而《大理攻略》中的譯本拼音分寫。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了三月街的譯本中,一網站將其譯為“March Street(Sanyuejie)Festival”,括號中的“Sanyuejie”為音譯,而《大理攻略》這本書將三月街音譯為“San Yue Jie”,兩個譯本同樣存在拼音連寫和分寫差異以及首字母大小寫的問題。音譯時拼音到底應該分寫還是連寫?拼音的書寫是否有參考規范?這些問題都值得譯者去思考,筆者在后文中也會給出建議。
(四)音譯+直譯
China Highlights和中國國際旅行社的網站上將“三道茶”翻譯為“sandao tea ceremony/Sandao Tea”,這兩個譯本采用的都是音譯“三道”和直譯“茶”的混合譯法,讀來十分別扭,這個譯法有些類似中國地名翻譯中的通名音譯、專名直譯的方法。筆者想起了之前讀過的一個例子,“據2005年8月14日《中國社會報》報道,一對年輕的丹麥夫婦來上海自助旅游,在上海最熱鬧的人民廣場迷了路。他們手中拿著的是上海星級賓館贈送的地圖。‘西藏中路’在這張地圖上是Xi Zang Zhong Lu,而該路指示方向的路牌是Central Tibet Rd.,幾步開外,人民大道和西藏中路交接點上豎著的‘上海旅游圖’燈箱上,西藏中路則是Central Xi Zang Rd.”〔17〕59。如果“西藏中路”的譯文統一使用音譯,用漢語拼音標注,外國游客問路時,當地人或許能夠聽出所問的地名并成功指路。路牌標識本就是指示方向的,翻譯方法不統一,譯文混亂,使得標識的功能喪失。和路牌標識這個例子同理,三道茶音譯+直譯的譯本和之前討論的直譯、意譯版本有一個共同的問題,西方自助游游客來到大理,如果和當地人說起這些文化負載詞,不懂英語的當地人是完全無法理解的,這些譯本既沒有實現交際的功能,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足額傳播。
通過梳理和分析三月街和三道茶的翻譯方法,我們不難發現,目前白族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方法不統一,同一個專有名詞有多個譯本,這不但會引起外國人的困惑,也不利于白族文化的向外傳播。因此,白族文化向外譯介和傳播亟待解決的問題是翻譯方法的統一。那么,什么樣的翻譯方法更合理呢?
二、白族文化負載詞翻譯方法之我見
對于白族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應當采用歸化還是異化的翻譯策略呢?我們先梳理一下這兩個術語的內涵,它們最初是由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其著作《譯者的隱身》中提出的。他認為歸化(domestication)是指譯者以目標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采取目標語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傳遞原文的內容。異化(foreignization)是指譯者以源語文化為歸宿,采取源語作者所使用的語言表達方式來傳遞信息,保留和反映異域特征〔18〕。基于以往的翻譯實踐和思考,筆者認為我們在處理白族文化負載詞的英譯時,應當采用異化策略。鄭德虎在其文章《中國文化走出去與文化負載詞的翻譯》中明確指出:“在文化負載詞的翻譯上,應盡量采取異化為主的翻譯策略,因為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體現中國文化特色,也最終有利于中國文化走出去。”〔19〕筆者在篇首提到的尚路平、朱黎、施紅梅三位研究者在他們的研究中都有提到一個共同的觀點:在翻譯白族文化時,應當以異化翻譯策略為主,筆者對此非常認同。因為采用異化策略是由翻譯的目的決定的,我們之所以要翻譯少數民族的文化,目的就是向外傳播該民族的文化,讓西方讀者領略該民族獨一無二的文化特色,以異化策略為主,以白族文化為歸宿,才能足額地保留白族文化,更好地向外傳播。否則,運用歸化策略,譯者以英語文化為歸宿,一味地轉換為西方讀者所熟悉的表達,只會犧牲掉白族的“異域特色”,造成翻譯中的文化虧損。
那么,英譯白族文化負載詞時,我們具體該采用什么翻譯方法呢?筆者在檢索資料時瀏覽了《孤獨星球》的官網,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旅行指南出版商,由托尼·惠勒和莫琳·惠勒于1972年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創立,其所出版的《孤獨星球》旅行指南備受全世界旅行者的推崇。該網站介紹大理美食時有這樣一段描述:Bai food makes excellent use of local flora and fauna.Specialities include rǔbǐng(乳餅;goat' s cheese)anděr kuài(餌塊;toasted rice"cakes").Given the proximity of Erhai Lake,try shāguōyú(砂鍋魚;a claypot fish cassero le/stew made from salted Erhai Lake carp)〔20〕。文中大理一些有代表性的美食如乳餅、餌塊、砂鍋魚等的翻譯全部用帶聲調的漢語拼音再加上對食物原料或制作方法的解釋構成,翻譯方法為音譯+解釋。王銀泉在討論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時就明確指出:“縱觀已有的翻譯理論研究與翻譯實踐探索,不難發現,對于漢語文化負載詞的英譯,我們已達成基本的共識,即采用漢語拼音音譯加解釋性譯文的翻譯策略不但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行的。”〔21〕音譯加解釋的翻譯方法不僅可以完整地保留少數民族文化,還便于西方讀者理解,一舉兩得。
上述《孤獨星球》網站的這段文字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化負載詞的音譯與日常我們接觸到的音譯文本不同,這些詞都有添加聲調,這樣的翻譯方法不僅準確、完整地將白族文化負載詞的發音呈現出來,而且對詞語的解釋也進一步把該詞的含義展現在外國游客面前,易于理解,這樣一來這些文化概念就可以足額地譯介出去。筆者非常贊同音譯中標注聲調的處理。郭柏壽等人在《中國人名和地名的漢語拼音在科技論文英文翻譯中拼寫的審視》中討論了科技學術期刊中,中國人名和地名的漢語拼音在英文翻譯中存在的一些典型問題,比如署名時人名拼寫未加聲調符號的問題,他們認為:“音符符號是一單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隨便丟棄;同理,聲調符號也是漢語拼音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不加聲調的漢語拼音也是不完整的。”〔22〕該文章的作者們建議中國人名翻譯后應當標注聲調符號,因為漢語中同音字和詞相當普遍,添加聲調可以有效解決同音字、詞的區分和辨析,此外,加上聲調后若按人名拼音檢索文獻將更加精準。
翻譯涉及兩種語言和文化的轉換,當源語和目標語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語言和文化鴻溝時,譯者很難使譯文和原文達到形式和內容的完美對等,所以譯者只能想盡辦法使譯文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文化負載詞反映了特定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民俗習慣,是各個民族所特有的詞匯,在英語中沒有對等詞。筆者認為在翻譯這些文化負載詞時,可采用和人名、地名類似的翻譯方法,音譯為拼音并標注聲調,然后再進行解釋,這樣一來可以在對外傳播中原汁原味地保留這些詞的發音,同時又便于外國人了解少數民族文化,此外,帶有聲調的漢語拼音也可以促進漢語在全世界的傳播。當然,音譯應該嚴格遵守源語和譯語的標準發音規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于2012年6月29日共同發布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GB/T 16159-2012,這是漢語拼音拼寫的國家標準,譯者在音譯時應該參考該規則。可能有的譯者會說,文化負載詞可以先音譯專名,再直譯通名,這樣可以省去解釋,使譯本更簡練,如上文中的三道茶被翻譯為“Sandao tea”。
這個譯法仿照的是1978年《關于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范的報告》中地名翻譯專名音譯、通名意譯的做法。“1978年9月國務院批轉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國家測繪總局、中國地名委員會聯合提出《關于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范的報告》。報告指出:①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中國人名、地名;②在各種外語中,地名的翻譯實行專名音譯、通名意譯。1980年,中國地名委員會印發《城市街道名稱漢語拼音拼寫規則(草案)》,對通名的翻譯又作了修改,規定地名中的專名及通名均采用漢語拼音拼寫”〔17〕。之所以擯棄專名音譯、通名意譯的做法就是因為路標指示牌這樣翻譯后反而會令人困惑,如上文中的外國游客就是因為這樣的譯文向當地人問路時找不到“西藏中路”。而且,譯音不全不單會導致文化傳播中的文化缺失,也不利于外國人向當地人進一步了解該文化詞匯。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白族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方法可以統一采用音譯,即用帶聲調的漢語拼音拼寫加上解釋的方法,將詞語的發音原汁原味地展現在外國讀者面前,這樣可以確保文化信息的足額傳遞,也利于后期外國人來大理與當地人交流,進一步了解這些文化意象。筆者覺得也可以像《孤獨星球》網站的做法一樣,把文化負載詞的中文書寫也展示出來,這樣有利于外國人全方位地認識這些文化意象,也有利于漢字的傳播,如上文中提到的餌塊這個詞的處理:ěr kuài(餌塊;toasted rice"cakes")。不過,根據《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GB/T 16159-2012中“表示一個整體概念的雙音節和三音節結構,連寫”〔23〕這一規定,餌塊的音譯正確拼寫應當是“ěrkuài”,應該連寫。此外,三月街是節日名稱,屬于專有名詞,所以拼音首字母要大寫。而三道茶不是專有名詞,普通事物名詞首字母不用大寫。那么,按照這樣的思路,文章開頭討論的三月街和三道茶就可以做如下翻譯:
三 月 街:Sānyuèjiē(三 月 街;Bai minority' s traditional festival between 15thand 20thof the third month of Chinese lunisolar calendar)
三道茶:sāndàochá(三道茶;Bai minority' s three-course tea)
翻譯方法不統一,必然導致同一文化負載詞有多個譯本,這非常不利于白族文化的對外傳播。要將白族文化足額且準確地介紹給全世界,我們應當先統一翻譯方法,這樣才可以避免譯文的五花八門、良莠不齊。筆者認為翻譯白族文化負載詞時,應當采用音譯即用帶聲調的漢語拼音拼寫,再加上解釋的方法,如果篇幅允許,中文漢字也應當寫出來,這樣不但可以足額譯介白族文化,還可以促進漢字的傳播。希望大理政府相關部門能夠召集一批優秀的譯者,統一采納該翻譯方法,集中譯介白族文化負載詞并向社會公布,有了統一的規范譯本,之后凡是涉及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均可采用這些譯本,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免文化負載詞翻譯混亂的局面,從而極大地促進白族文化有效地向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