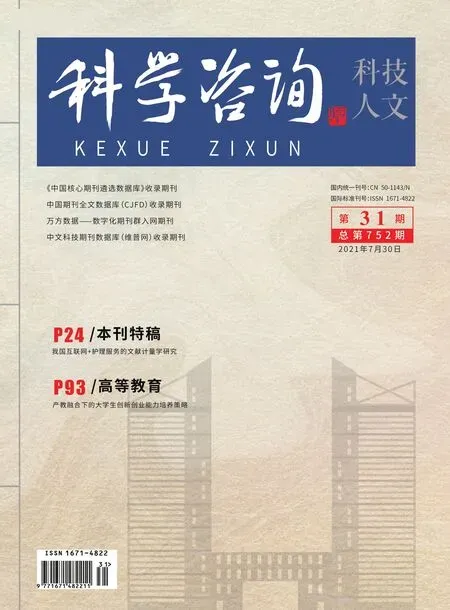新時代下低保標準提升策略探究
楊 彬
(山東省東營市墾利區民政局 山東東營 257500)
一、低保概述
最低生活保障,是國家針對貧困人口所制定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向貧困家庭按照最低生活標準發放資金補貼的方式確保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一項惠民制度。低保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低保受眾群體為貧困家庭;第二,是一種通過向貧困家庭發放最低生活補貼的救濟方式;第三,低保并不具備長期性,而是屬于臨時性補貼,倘若補貼的家庭其資金收入超出國家制定的救助標準,便不會再向其發放救助資金。如何確定低保標準則需要依照所在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并將最低生活所需物品、服務等按照市場價以現金的方式進行呈現,最終得出的金額便是最低生活保障金額[1]。
二、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
隨著社會的發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從實施到現在也逐漸趨于完善化,近幾年更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隨之進行調整,不同地區、城市與農村的低保標準差距也逐漸縮小,有些地區已將低保標準調整為統一標準。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的發放嚴格按照國家規定進行,低保經辦人員依據申請人共同生活家庭成員家庭收入情況及財產狀況,核定保障資金,由財政部門進行審核并撥付資金,之后再由金融機構代發到具體保障對象手中。這樣既可以確保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發放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也能確保低保惠民政策得到全面執行。低保標準跟隨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隨時進行調整。如2020年,湖北武漢的城市低保標準提升為每月830元/人,農村低保標準提升至每月680元/人;河南城市低保標準提高至每月570元/人,農村低保標準提高至人均4260元/年;廣西欽州城市低保標準提升至每月760元/年,農村低保人均5500元/年。2020年,全國民政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現階段我國低保標準都有所提升,城市與農村低保標準分別提升至每月665元以及人均5842元/年,同比增長7.7%和11.3%。并且有很多省份已經實現了城市與農村低保標準的統一,如北京、上海、長沙等。低保是我國救助貧困人口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是貧困人口從當地人民政府獲得基本生活物質幫助的直接途徑,是維護困難群眾基本生活權益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為此,在新時代背景下對低保標準進行有效提升非常有必要。
三、新時期低保標準提升策略
(一)增加財政部門資金投入
要想實現低保標準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相一致,就必須提升低保標準,并增加財政資金投入。我國城市與農村的經濟發展存在明顯差異,尤其是一些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貧困人口相對較多。該地區的低保標準更需要國家財政部門資金的支持,為此,國家可采用傾斜性補助的方式提高其低保標準。此外,對于經濟發展較快,人們生活水平比較高的地區,可能會擔憂由于提升低保標準而導致福利依賴,現階段我國的低保標準與經濟發展之間還存在一定的差距,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適當提升低保標準也并不會陷入福利。低保標準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僅僅保障其最低生活需求。基于此,增加財政部門資金投入,不僅能提升低保標準,縮小低保標準差距,對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也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二)建立低保標準動態調整機制
新時代背景下,低保標準也應伴隨物價的增長而進行動態調整,為困難群眾的生活提供保障。近兩年,我國的物價一直處于持續增長狀態,若還是依照以前的低保標準發放資金補貼,會使困難群眾的生活水平受外界影響出現較大波動。所以,除了要建立低保標準調整機制,還要創設價格補貼之類的應急機制,以便在物價增長過快等其他情況下能夠適當增加專項補貼來保障群眾生活水平。發放臨時價格補貼來平抑物價過快增長對困難群眾生活水平帶來的影響,需要以政府部門專業人員的物價增長報告為依據,對低保標準進行輔助調整[2]。
(三)拓展低保資金籌集渠道
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的籌措來源主要是各級政府的財政資金,資金來源比較單一,且政府財政資金有限,以致于民生保障資金的支出會出現延時的情況,給困難群眾的日常生活帶來影響。對此,需要政府切實履行職責,合理籌措農村低保資金,拓展籌資渠道,實現社會力量的資源整合,為低保標準的穩步提升奠定基礎。《國務院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低保制度通知》指出,“農村低保資金的籌集以地方為主,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將農村低保資金列入財政預算,省級人民政府要加大投入”“中央財政對財政困難地區給予適當補助”。現階段各級財政收入下行壓力增大,若分擔過重難以維持穩定的低保資金,不利于城鄉低保的發展。為減輕基層財政負擔,支持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建議適當調整市縣財政嚴重困難地區不同層級財政對城鄉低保投入的職責分工,將大額資金籌集定位在省級[4]。福建省能在全省范圍內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方面走在全國的前列,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省財政出大頭,它的省一級財政為全省4/5的縣(市)提供農村低保補助資金,其中2/3的縣(市)獲得了高達75%的農村低保專項補助資金[5],湖北省農村低保資金由省、市、縣三級共同承擔,也是以省級財政為主,省級和地方籌資比例為5∶1[6]。通過轉移支付確保省級財政資金在低保專項補助中占據主導地位,緩解基層財政壓力,并在安排補助資金時要對發展相對緩慢地區重點傾斜,以平衡整體保障水平。輔之諸如義演、捐贈、民間互助基金、扶貧基金等其他資金籌集方式確保民生資金充足,為低保標準的有序提高打下基礎。
(四)科學匡算數據,據實提高標準
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確立可以參考不同地區的最低生活需求、經濟發展狀況、物價標準、居民消費能力以及財政收支狀況等多項指標,按照區域進行分級評定,并以此為基礎,對各個地區的低保標準提升進行明確的規劃,以此實現低保標準的合理、有效提升[3]。低保標準的確定和提升都需要明確的數據作支撐,并通過科學的測算方法判定低保標準是否符合城鄉居民基本生活所需。
首先是城鎮地區的居民,以武漢為例,建議其低保標準為“每日飲食攝入量×當地平均價格”。即按照居民基本生活保障所需的平均花費作為當地城鎮居民的低保標準。為保證測算結果真實有效,工作人員需要定期進行市場調研,比較得出生活必需品的平均價格,確保低保標準制定的科學化、公開化和合理化。
其次,農村地區的生活條件與城鎮地區有較大差異。如時令蔬菜及小麥玉米之類的糧食作物,農村居民可采用自耕地的方式獲得一部分,相應的農村低保標準的計算就要復雜很多。筆者建議從農村居民的年消費入手,由于農村居民收入來源單一,他們的消費支出往往能夠反映其真實家庭生活情況。再輔助計算本地區往年因天氣、洪澇等自然災害影響農作物的減產情況,最終得出農村地區的低保標準。
(五)明確地理差異,按地區提升低保標準
我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發展情況不同,導致經濟狀況、就業情況和消費情況也會有很大差異。雖然各地區陸續實行了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但因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物價指數及消費習慣等原因,保障金水平差異較大。我國低保標準的設立應因地制宜,統籌考量。我國一線城市,經濟發展速度快、消費高、就業比率高,相較于西部偏遠欠發達地區,低保標準就要高一些。因為缺乏較為客觀的衡量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參照基準,很難對各地區保障水平的合理性作橫向比較。比如,深圳地區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1087元,而重慶地區城鎮居民每月636元,我們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認為深圳市民享受了高于重慶市民幾乎一倍的低保待遇[7]。為此,我們建議各地區設定城市低保標準時要更多地參考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月支出水平和當地的恩格爾系數,利用兩者的乘積作為該地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隨后按照城鄉低保標準1.3∶1的比例來確定農村低保保障標準,隨著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不斷深入,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實現城鄉標準的統一。
四、結束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民生保障部門扎實履行政治責任,充分發揮脫貧攻堅兜底保障作用,全力做好社會救助兜底脫貧工作,持續深化特殊困難群體關愛幫扶,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的傾斜支持力度,有力服務支持了脫貧攻堅大局。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國民生保障領域中的重要一環,其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發揮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背景下,結合保障對象的實際生活情況,以當地經濟發展、消費水平等為依據的低保標準動態調整機制不僅能為保障對象的基本生活提供資金支持,又可以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進一步提高國民的幸福指數,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