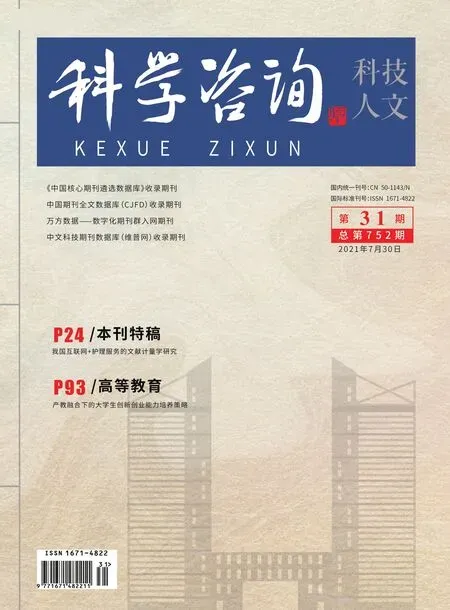體育復歸教育:體教融合的現實抉擇與時代擔當
劉寶豐
(南陽師范學院體育學院 河南南陽 473061)
我國的當代教育傾向于以社會本位為中心,過于重視教育的工具性價值,對教育的直接本位價值重視不足,造成教育價值取向錯位和教育功能的短視性和功利性。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深改革委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我國體育和教育事業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面向21世紀教育事業的全面振興,體育復歸教育本真的價值應然之義[1]。
教育價值是教育主體即人通過教育實踐活動得以體現的。關照所有主體的價值,才能使教育政策價值全面而完善地體現出來。《意見》的出臺為當下和未來一段時間改變學校體育面貌、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徑。體教融合的根本目的是育人,必須切實改變在學校教育中重德輕體的狀況,充分發揮體育在教育中的育人功能,為建設健康中國夯實基礎。體育回歸教育是體教融合的現實必然抉擇,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也是我們新時代主人翁應該主動挑起的時代擔當。
一、融合:體育回歸教育本真
“體育”一詞是舶來品,體育是教育的多元載體,教育是體育最有效的體現,體育可以指代“體育教育”“競技體育”“體育運動”等,體育界曾對體育概念有過幾次大的討論,仍難以達成共識。對體教融合的解讀時,有觀點認為:體教融合都存在學理上的悖論,即體育本身就是教育一部分,體育與教育的融合是不成立的。體教融合雖說是中國獨創,但按學理分析卻是一個不準確的提法[2]。
從世界發達地區經歷來看,體教結合的對應表述為“combination sport and education”,體教融合英語表述為“dual career of athlete”,直譯為“運動員雙重職業”,這些地區更著重運動員培養的全過程,包括退役后的階段。如有運動員在退役前獲得行醫執照,前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是世界賽艇冠軍,也曾做過整形外科醫生。
中國特色體教融合模式,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同時,首先需明確學理層面問題,因為體育本身就是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體育就是教育,由于“體”“教”從概念上二者沒有分開過,也就談不上融合。因此,體教融合不應理解為“體育”和“教育”,“體教融合”中的“體”和“教”指的是“體育部門”和“教育部門”,通過整合兩大部門的優質資源實現優化配置,來實現青少年全面健康發展。
廣大青少年放下后顧之憂從事競技體育才能從底層助推高質量的金牌,即使因故放棄職業運動生涯也能很快成功轉換角色。從社會國家層面來看競技體育金牌的培養成本不是增加了,反而是降低了。對運動員個人來講,多了一道保障,風險降低了,反而可以大膽實踐更為激進的訓練理念和方法。此外,可以帶動相關體育科學研究。對于體教融合的另外一方國民教育體系而言,體育回歸教育能為學校體育活動注入新的活力,促進課外活動,還能加強青少年的身體鍛煉,增強體質健康、健全人格、錘煉意志。
二、體育:面臨現實發展難題
計劃經濟年代“舉國體制”資源集中效率高快速地提升了我國的競技體育水平。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市場經濟的探索,先前的模式逐漸面臨挑戰。進入新世紀后,體制機制弊端愈發嚴重。很多群眾基礎差的項目其運動員在退役后生活窘迫,例如“街頭賣藝的體操冠軍”張尚武,“冠軍搓澡工”鄒春蘭等。近年來,政府已注意到問題的緊迫性與嚴重性,從國家到地方相繼出臺并完善了一系列制度與政策。如國家體育總局2000年出臺的退役優秀運動員免試進入高等學校學習的政策,解決優秀運動員的職后再教育需求,補救體教分離的后果;2014年出臺退役運動員就業安置工作優惠政策等,但效果依然不容樂觀。此外,在《意見》出臺之前,國家體育總局召開了“三大球工作會議”,會議討論當前我國體育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競技體育后備人才萎縮嚴重的困境,尤其是足、籃、排三大球項目后備人才匱乏,已成為體育強國建設的掣肘。
究其原因是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體制機制急需重大調整,改革面臨深水區。一個時期的急功近利政策總是要求教育展現出即時的、顯性的功效,忽視或者輕視教育的長期效益;往往只強調教育的實用價值,忽視培養個性、使人的潛能得到盡可能發展的深層價值。正如H·SPENCER所說:“它為了得花,而忘了根株。追求虛美,而遣實質[3]。”
三、教育:邊緣化體育飽受詬病
我國青少年各項健康指標從1985年開始持續下降20多年。從2007年“中央7號”開始,黨中央國務院分別就全民健身、健康中國、青年發展等主題相繼出臺多個重磅文件,均將青少年作為重點對象。截至2014年,我國兒童青少年體質持續下降的狀況得到基本遏制,但各年齡段學生的肥胖率、近視率仍居高不下,大學生身體素質達標率較中小學生更差。2020年政協會議上提到我國兒童、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健康隱患,“眼鏡娃”“小胖墩”比比皆是。我們在競技賽場上屢獲佳績的同時,學校體育、全民體育卻得不到同等重視,導致學生身心健康悄悄丟失。
體育的長期弱勢與矮化加強了教育中人的異化,致使現實教育中的人與人自身本質屬性出現了偏離。在學校體育中,學生成為直接的受害者,也正是應試教育造成的人格的悲哀。于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三十年來我國奧運會金牌一直穩居世界前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就。在現代社會里,體育要肩負著崇高的使命——維系人類的健康,滿足人類的精神文化需求,最終使人類充分地享受自由和幸福。這也應該是比較全面和合理的,任何時候都應成為體育的理想和追求[4]。
四、復歸:現實抉擇時代擔當
教育就應該是全面育人,體育本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對青少年進行體育、德育、智育、美育和勞動教育從來都是一個系統的工作。教育的復歸應當是其整體性的復歸,體教融合是體育本真的回歸,讓體育真的成為教育有機組成部分。體育回歸教育是體教融合的現實必然抉擇,也是我們新時代應該主動挑起的時代擔當。
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中這樣寫道:“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而德智皆寄于體。無體是無德智也。”蔡元培先生認為:完全人格,首在體育。青少年的教育首先是身體教育,青少年的發展不能只借助理性或靈魂來折射真理,而是將身體作為體知事物的重要手段。在青少年教育中,身體的作用與其他年齡段的教育相比更為重要[5]。體育復歸教育,體育才能向全體學生,充分發揮體育育人的效應。體育回歸教育,將體育與教育融合起來,使得運動員有機會享受平等的文化教育,讓他們有機會為自己將來的職業道路做出更好的選擇,只有全面的發展后備人才才能走得更高更遠。全面深入落實體教融合,促進體育更好地回歸教育,是家庭、學校、個人乃至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馬克思說:“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體育最大的“功利性”是在于將人類從物質的囚禁和奴役中解放出來。體育復歸教育才能建設體育強國、教育強國和健康中國。我們要以推進治理現代化為目標,以機制體制建設為根本,以改革創新為驅動,推動廣大青少年體育鍛煉與文化學習協調發展,錘煉其意志、健全其人格促進全體青少年健康成長,培養全面發展的社會建設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