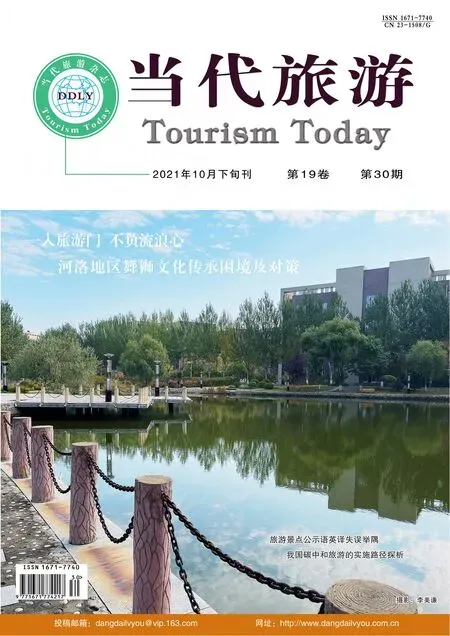河洛地區舞獅文化傳承困境及對策
趙 楠 王佳婷 郭曉洋
河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河南洛陽 471000
引言
“河洛”意指黃河與洛河。經學者考證,“河洛地區”指以洛陽為中心, 東至鄭州、中牟一線, 西抵潼關、華陰,南以汝河、潁河上游的伏牛山脈為界,北跨黃河以汾水以南的濟源、焦作、沁陽一線為界的地理范圍。“舞獅”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之一,發端于此。
舞獅活動作為一項民俗活動在我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舞獅文化經歷了多維度的變遷。在當前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以及非遺進校園的大背景下,高校開展相關調研工作,對于舞獅的保護與傳承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本文將以河洛地區三個舞獅團體為研究重點,采用文獻資料法、深度訪談法對其進行全面深入的了解與研究。發現其當前存在的不足,通過總結自身的看法、查閱相關文獻、請教專業教師以及非遺傳承人,給出相應的解決對策。了解三個不同發展路徑的舞獅社團所處的發展困境并提出對策建議,對于推動河洛地區的非遺傳承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 問題的提出
舞獅是河洛地區社火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排鼓等其他民俗活動相伴發展,傳承于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大里王舞獅人形容為“舞獅子是在我們的基因和血液里的。村里男子沒有經過訓練,戴上獅子皮也能舞起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推廣,這項曾根植于鄉土的民俗活動的文化傳承有了新問題。
前人研究將文化傳承作為一種手段,認為文化傳承能夠為新的社會秩序的建構做必要的文化要素積累(趙世林,2002),能夠促進民族認同,增強民族自信(王德剛,2019;竇坤,2010)。另一種觀點認為保護與傳承本身就是根本目的這樣一種“本體論”觀念(和少英,2009)。社會群體在文化傳承的過程中不斷自我完善,而文化傳承維系了社會再生產。從研究視角上來看,文化傳承一方面被認為是代際間相互“傳遞”的過程(姚艷,2006);而另一方面則被認為文化傳承不僅僅是“傳遞”,更有在“傳承”中的自我生產,即文化接受者對接受的文化進行吸收和自我的再加工,從而創造出適合社會發展需要的新的文化模式(趙士林,2002)。還有學者將文化傳承分為了橫向和縱向兩個層面,橫向是指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影響和吸收,縱向是指通過特定的方式和路徑實現縱向傳遞的過程(譚淑玲,2007)。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我國文化建設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本來”“外來”與“未來”同時也構成了文化傳承的三個維度(王海英,2021)。文化傳承在學人的研究中存在著從單一維度到多維的視角轉換。
學人對舞獅的研究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探討舞獅的歷史淵源及傳播(顧城,2002;張延慶,2003;段全偉,2006;于兆杰,2008);第二個階段分析舞獅習俗與傳統文化的關聯(呂韶鈞,2008;丁保玉,2010;黃芝岡,2013;黃東教,2017);第三個階段研究重點為作為體育競技運動的舞獅研究(雷強,2017);第四個階段主要研究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舞獅(張豐,2017;向軍,2018;王標,2020;李本一,2020)。
近年來舞獅研究多集中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下傳承主體、傳承形式及傳承內容等問題。但在同一文化區域內部,“舞獅”的傳承存在何種差異性與共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級與分類為傳統民俗活動帶來了怎樣的機遇與挑戰?這將是本文聚焦的問題。舞獅作為河洛文化的傳統民俗活動之一,隨著歷史的發展,其參與方式、展演形式與傳承路徑都發生了改變。本文將在當前學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視角下,探討河洛地區三個不同性質的“舞獅”社團文化傳承的差異性與共性問題,并分析其解決策略。
二 河洛舞獅溯源
中國舞獅究竟起源于何時,學者并無統一界定。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分析,總結歸納出三種較為普遍的說法。第一種是漢朝起源說,源于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后,獅子由西域傳入[1]。第二種是三國起源說,源于三國時期廣陵亭侯孟康所注《漢書·禮樂志》中有“象人”一詞的記載,研究者認為“象人”就是扮演魚、蝦、獅子的藝人[2]。第三種說法源于南北朝時期。《宋書·宗愨傳》中記載,445年(寧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南寧軍“代林邑,愨自奮請引。林邑五范陽邁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后無際,士卒不能當曰:‘吾聞獅子 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御,象果驚奔,眾因潰散。遂克林邑[3]。’”自此之后,舞獅開始在軍隊中流行,然后逐漸流傳到民間。目前學界較為認可的是漢朝起源說。
河洛地區最早見于史料記載的民間舞獅為北魏。北魏時期楊炫之在《洛陽伽藍記》中有明確的記載:北魏每年四月四日浴佛節,洛陽長秋寺節日前后引像,“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師子導引”指舞獅在前開路,導引佛像隊伍[4]。隨著歷史的發展,河洛舞獅成為洛陽民間一項開展非常普遍的文藝活動,其本身也代表著民眾對傳統文化的高度認同。舞獅作為河洛文化的子文化,深深扎根于河洛地區。舞獅文化與河洛文化兩者相互促進,河洛文化提升舞獅的價值,舞獅作為河洛文化的組成部分,又反過來促進河洛文化的發展與完善。
三 獅舞文化傳承的問題
對洛陽市洛龍區大里王舞獅、陳李寨舞獅、曹屯舞獅的發展現狀進行梳理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舞獅發展現狀
(一)傳承方法單一
舞獅傳承多依靠口授身傳,表演技術技巧大多為個人經驗,沒有形成專門的文字資料。在傳承過程中,部分舞獅人年齡偏大,只有少部分難度較低的動作可以親身演示,難度較大的動作只能口授。這就導致高難度的動作越傳越少,為舞獅的傳承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同時,受口頭傳授的限制,舞獅學習缺乏整體性、系統性,無形中增加了新一代年輕人學習的難度。即使現在表演形式偏向于“地攤”,學習難度下降,其學習依然存在很大的困難。舞獅作為河洛文化的組成部分,傳承方法單一間接導致它對外傳播性減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河洛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二)缺乏適齡傳承人
在傳統北獅表演中有較多難度較高的動作,如“上老桿”等。一般未經過系統訓練且身體素質不過硬的年輕人難以完成舞獅當中的動作。曹屯獅舞隊會在本社區內招募退伍軍人進行訓練,陳李寨獅舞隊中的部分年輕人有過習武的經歷。同時由于舞獅表演的收入并不能作為主要經濟來源,大部分舞獅人都是利用空閑時間進行舞獅表演。時間的不確定性也導致了年輕一代的舞獅人缺乏練習。年輕人在工作和結婚后面臨著身材走形及身體素質下降等問題,加上缺乏練習,因此舞獅團隊中缺乏能夠堅持的適齡傳承人。
(三)非遺等級的認定重置舞獅邊界
自2007年大里王被認定為省級非遺之后,獲得了足夠的政府資金支持及表演機會。但舞獅作為河洛民俗文化活動之一,原根植于鄉土的日常生活當中。
以前參加關林廟會,全村都會出動。一大早家里的女人會準備做飯,吃了飯,大家扛著舞獅的道具開始往關林廟門口去。隊伍里除了舞獅子還有排鼓、秧歌等其他活動的隊員。沒有參加表演的,大家也會去捧場當個觀眾。哪邊的舞獅演得好,代表了全村的臉面。
各等級非遺的認定對河洛地區的文化發展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一方面,被認定為非遺的項目會得到政府資金和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非遺項目會有更多的展演空間,獲得一定的商業收入。但同時,對于舞獅一類的民間團體文化活動而言,非遺項目的認定為經過認定的社團帶來了政策、資金和演出機會,而該項目的其他社團則面臨展演空間的壓縮。舞獅逐漸從日常生活空間走向展演空間。
(四)傳承理念淡薄
河洛地區的傳統舞獅主要為村集體負責、團隊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原有村落融入到城市社區當中,村集體領導轉為城市社區的居委會負責制。原有的村集體意識及地域認同,在物理空間改變的過程中逐漸消解,但新的社區認同并未強化。這也導致舞獅作為曾經的鄉土集體活動在當前城市社區傳承的過程中出現認同淡化的問題。
(五)舞獅商業市場不規范
舞獅社團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商業演出。雖然近年來傳統文化愈發受到社會的重視,但如何使傳統文化走向市場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以舞獅為例,社團參加商業演出,除了舞獅之外,還需要排鼓等其他樂器的配合,同時也會產生交通費等其他相關費用。社團的集體收益除了舞獅核心人員,還要分配給參與活動的其他人員。現有的舞獅商業活動收益難以維持社團的正常運轉。同時,面臨壓價等社團間的不良競爭,舞獅市場不規范,缺乏良性競爭的環境。
(六)宣傳不足
隨著信息技術以及自媒體的發展,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利用移動設備來獲取信息,如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而舞獅表演團隊的主要宣傳方式依然為傳統的線下宣傳,宣傳范圍小,受眾少。部分舞獅團隊緊跟時代潮流,也嘗試進行線上宣傳。比如大里王獅舞社,推出了快手賬號,在這些平臺進行宣傳推廣,但受設備、技術、人員等的限制,上傳的視頻質量低,數量少,吸引流量少,線上宣傳效果不明顯。
四 河洛舞獅傳承對策分析
(一)拓展傳承方法
一方面,政府或社團負責人可以牽頭組織,梳理相關舞獅文獻并對傳承人進行訪談,將舞獅的歷史、內涵、技法和理念等進行文字整理;另一方面,邀請經驗豐富的舞獅人,錄制專業的教學視頻。同時借助VR、AR等科技手段,使舞獅教學活起來。拓寬舞獅傳承方法,進行系統化、專業化的學習。在宣傳舞獅的同時,也完善了舞獅的傳承途徑,引流的過程幫助年輕一代舞獅人建立自信心。
(二)完善傳承機制
開展舞獅進校園活動,邀請舞獅人去小學、初中授課,既可以豐富校園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舞獅的普及性。對于舞獅,不僅要有技法上的傳承,同時也要有理念的傳承,包括舞獅的歷史及其文化內涵等。在這個過程中,學生不僅可以深入了解舞獅文化、增強對舞獅的認同感,還能強化體質,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在普及的基礎上發展,是舞獅文化傳承的需要,也是廣大舞獅傳承者的心愿。
(三)強化舞獅社團所依托社區的主體性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原有的村集體意識淡化,新的社區認同尚未形成,為舞獅的發展帶來困境。陳李寨年輕一代舞獅人僅有4人,限制了相關活動的開展。在傳統社火表演中,經常出現借人的現象。強化舞獅社團所依托社區的主體性,加強宣傳,強化傳承意識。同時,加強社區間的交流與互動。舞獅社團的主動交流,可以為真正對舞獅文化感興趣的年輕人提供交流和展示的機會,促進河洛舞獅文化的繁榮發展。
(四)積極舉辦“北獅”比賽
南獅在海內外都很流行,種類偏多,比較著名的有佛山醒獅、鶴山獅和東莞獅等。比賽有云頂世界獅王爭霸賽、“黃飛鴻杯”獅王爭霸賽等。南獅是由北獅演變而來,又發展創新為新的模式。可借助南獅的發展經驗及關林廟會、河洛文化節等民俗節慶活動,先在河洛地區舉辦北獅比賽,保留其技巧,培養專業人才,彌補北獅演出技巧性相對較弱的問題。同時邀請南獅參加,加強內外交流,活化舞獅文化,使社會公眾對舞獅等民俗活動產生興趣,并自愿深入學習與傳承。
(五)融入河洛旅游發展
作為河洛文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舞獅的傳承與發展也影響了河洛文化的延續。2020年國家文化與旅游部在洛陽建立“河洛文化生態保護試驗區”,河洛文化的整體保護與傳承上升到了國家層面。將舞獅活動與河洛旅游相結合,能夠有效促進舞獅文化的活態傳承,開拓其商業市場,強化舞獅團體的文化自信。同時舞獅也可以在旅游活動中成為河洛文化宣傳的窗口,增強河洛文化的傳播效果。
(六)拓展宣傳渠道
借助互聯網和大眾傳媒,弘揚舞獅文化。隨著移動設備的普及,人們更傾向于在網絡上獲取信息。通過互聯網,對舞獅活動進行宣傳推廣,讓更多的人了解“舞獅文化”[5]。利用微信公眾號,推送一些科普性的舞獅文章;借助短視頻平臺,上傳優質舞獅表演片段等;還可以借助媒體,開展跨地區的舞獅文化交流、競賽。由此,讓更多的人了解舞獅、愛上舞獅、走近舞獅。
五 結語
對舞獅進行深入研究,了解其發展現狀并提出對策建議,既有利于傳承與保護舞獅,促進舞獅的現代化發展,又可以對外宣傳、展示河洛文化,提升河洛文化的知名度。舞獅作為河洛文化的組成部分,對其進行傳承與保護,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河洛文化的多樣性,延續了歷史文脈,推動了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在舞獅表演過程中,人們在潛移默化間接受文化的熏陶,社會公眾更深層次的感知了河洛文化,文化通過“舞獅”這一載體,有了生動的體現。時代在高速發展,如何緊跟潮流,喚醒昏昏欲睡的舞獅[6],在傳承與創新中推動河洛文化的發展,讓傳統文化煥發新活力仍是我們應當不斷探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