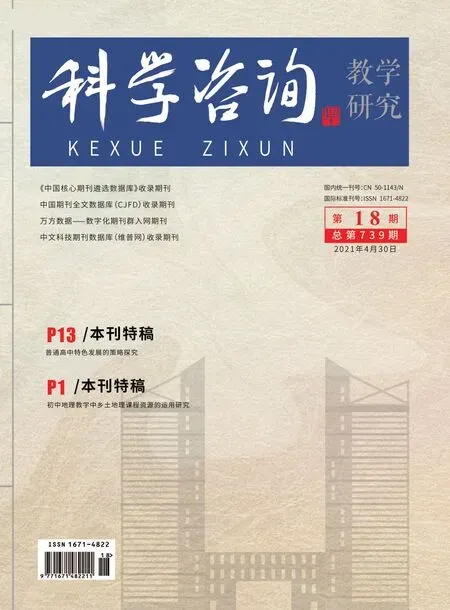從語文核心素養角度探析《背影》里“父親”的情感訴求
張茹茂
(重慶市求精中學校 重慶 400015)
《背影》一文是朱自清的經典名篇,這篇文章在中學教學中歷來被解讀為“父子情深”的典范,尤其專注于在質樸的文字里挖掘出“父親對兒女的深刻細膩、真摯動人的愛”。但新時代對語文課堂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學生語文核心素養的養成需求,這要求我們解讀這篇散文時必須落腳字里行間中,立足真真實實的人,把事件經歷者、作者、讀者三者內心彼此貼近,才能體會文章帶來的情感觸動。
一、找到《背影》里的“父親”形象
常規解讀里,我們把朱鴻鈞當作“父親”,朱自清當作“兒子”。然而當我們細細把握“兩個時間”時,我們便發現“父親”這一身份有很深刻復雜的形象特征。
在“當時時間”中,朱鴻鈞是一位49歲的中年父親。首先是事業衰落和情感失意,朱鴻鈞作為中年人,事業和情感本應是相對穩定的兩大人生支柱,但朱鴻鈞偏偏因為情感原因(潘姓姨太太大鬧徐州)導致丟了徐州榷運局長這一“肥差”的營生。這在舊時小官僚家族里這可謂是經濟和名譽的雙重打擊,直接加劇了家境的沒落。本就受五四思潮影響而全面批判和反對父權的朱自清,此時對父親便更加嫌棄、鄙夷、甚至嘲諷。而且,朱鴻鈞的母親也因他的糟心事急火攻心而離開人世,常言父母在人生尚有出處,父母亡人生只剩歸途,于朱鴻鈞而言,他不再是誰的兒子,真正成為了直面老去和死亡“老一輩”,更何況母親還是因自己而去。
在“當下時間”另一位父親,便是朱自清自己。在1917年浦口分別時,朱自清仍舊只是一個兒子,用他自己的話講:“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朱自清《兒女》)而此時朱自清已然是不止一個孩子的父親,這一身份的轉變十分的關鍵,讓朱自清真正有機會觸碰到中年父親的內心深處。在《兒女》文中,有這樣的表述:“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著,和普通的父親一樣。”這里可以看見文中朱自清對自己初為人父時期的一些回顧和心理感受,可以說此刻他才真正從另一個角度去審視了自己的父親,其根本原因在于朱自清的心理狀態轉變,為人父方能體會為父的心理。這就解釋了為何《背影》不是1917年“感動而作”,而是時隔八年“回憶之作”。
二、背影里“父親”的實際情感訴求
已為人父的朱自清感受到了“父親”心里什么樣的情感訴求呢?其實于結合朱鴻鈞所處的境況和早年經歷來看。朱鴻鈞“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憑借自己的本事安身立命,經營起一大家子。而到了1917年強烈的反差一下便出來了,朱鴻鈞對自己的家庭、事業、情感全然無法把控,在兒子面前也威嚴喪失,而且突然少了心理的“依靠”——母親。可以說朱鴻鈞完全由一個生活中的強者轉化為了“弱者”。這對于人處中年、本可完全掌控自己人生,且一生要強當慣了“大家長”的朱鴻鈞而言,其內心的悲愴、無力之感就必然而然的產生。這時我們再品浦口送別時朱鴻鈞的幾個細節,“本已說定不送我……他躊躇了一會,終于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爸爸,你走吧。’他往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這里面當然有不善言表的父愛,但更有一層“弱者”對親人(兒子)尋求依賴和呵護的需求(被愛的需求),對于關心、陪伴、支撐的渴望。朱鴻鈞此時多么渴望有個地方可以作為情感的宣泄口,多么希望有個人告訴他沒關系的,會好起來的。然而他只能夠說一句“好在天無絕人之路”的話語算是安慰兒子,也算作為自己打氣。其實“父親”不僅是偉岸的山,也是一個平凡的人。然而他此刻心里的情感訴求完全被朱自清忽略掉了。因為彼時朱自清僅是把自己當作一個可以在父母面前“肆意妄為”的兒子,一個“被照顧者”。而未曾想到父親的“柔弱”,父親也需要照顧,需要有人給他安慰、給他支撐的力量。
對于父親這樣的心理情感訴求,朱自清是在自己有了多個孩子后,才發現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自己的中年正是面對著父親朱鴻鈞當時的一樣處境。他甚至曾寫信給圣陶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著還是自殺的好”。(朱自清《兒女》)這里當然不是說他真有什么自殺傾向,但可以看見這時的另一個“父親”——朱自清,也深刻的體會到中年父親堅強的外表下,也渴望有個依靠和放松的地方,期待有人給予他力量與支持,告訴他沒關系,一切都會好的。因而1925年,當朱自清收到父親的來信時,看到“大去之期”的字眼,才猛然回想起,父親不正是從“那年冬天”開始“老去”。而1917年那個冬天,自己安心當一個被照顧者,對父親的情感訴求竟然毫無察覺,所以心中才會充滿著愧疚與自責。如今自己雖已醒悟,但父親已然老去,自己又還能照顧父親幾許呢,唯有遙寄一分理解,說父親“情郁于中,自然要發之于外”。至此我們或許能夠理解為什么朱鴻鈞在看了《背影》后終敞心結,因為這么多年來,自己的內心訴求真正被兒子所理解,自己終于不是那個內心的孤獨者。
三、解讀“父親”心理訴求對培養語文核心素養的積極意義
其一:情感意義。從人的角度去理解文章,可以讓學生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故事中人的所感所聞、所思所想,通過對其真實的情感訴求探析,貼近讀者、作者、故事中人之間的心靈,產生情感共鳴,擺脫了單純的宣教父愛偉大,拉近文章與學生的距離,使學生真學、真品、真悟、真用。
其二:語用意義。學生通過辨析回憶性散文中人物的當下和當時的形象、情思及變化過程,有助于理解回憶性散文的行文邏輯,有利于學生把握“兩個時間”里不同的情思,以及其表現的不同手法。
其三:德育及心理意義。從人出發,可以引導孩子的情感塑造,學會轉變自己是受照顧、受保護的對象之觀念,樹立起關心他人,照顧他人的情感意識。有助于“半成熟半幼稚”心理時期的學生心理發展,緩解其既謀求獨立又尋求依賴的心理矛盾,引導其合理思考內心的自立訴求,以及有效與父母溝通的方法與尺度,反哺現實生活。
總之,把握回憶性散文的“兩個時間”,從人出發,理解和探析文中人物“父親”的真實情感訴求,不僅有利于加深學生對文章的感悟和理解,也有助于塑造和培養學生的語文核心素養,是解讀這篇文章的另一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