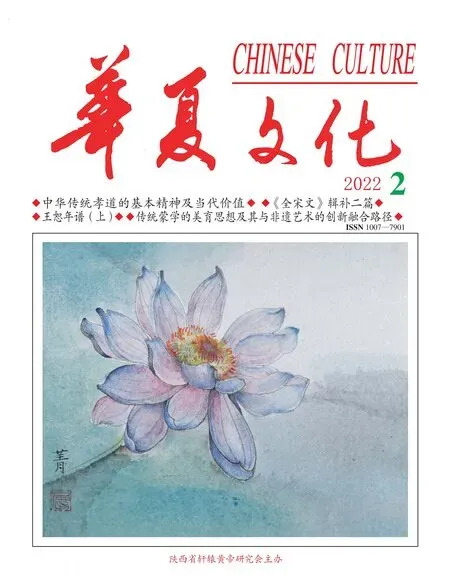民族大融合下的儒學會通與變革
——評《元代理學與社會》
□劉 育
文化的革故鼎新離不開特定的社會背景與意識形態。理學肇始于宋,是儒者們在對傳統儒學進行反思的過程中,融合佛道所產生的哲學,也是中國古代思想深度最高、理論體系最為完備的學術流派。其對宇宙本原的思考,對心性的探究,對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對孔孟之道的宣揚,對倫理觀念的進一步哲理化,無一不吸引著有宋以來儒家學者的目光。元代理學承上啟下,因元代獨特的社會構成與政治特色而呈現出不同于前代的理論特點,在整個理學發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
朱軍著《元代理學與社會》一書,突出元代理學對宋代理學的發展與創新,探究其在宋元朝代更迭的特殊社會背景下,逐步官方化、世俗化的重要原因,通過對諸多古籍文獻、研究著述進行耙梳,闡述了元代理學與社會發展的互動關系。該書由巴蜀書社于2022年1月印行,屬儒道釋博士論文叢書系列。
一、元代理學的發展線索
《元代理學與社會》是一部以社會與理學關系為核心的元代儒學學術史著作。元代理學在不同區域、不同時期呈現出不一樣的學術形態,作者認為理學“具有較強的適應性和變通性”(朱軍:《元代理學與社會》,巴蜀書社,2022年1月,第410頁),這是其能夠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下,應對“接踵而來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多重沖突”(《元代理學與社會》,第410頁),并不斷保持頑強生命力的主要原因。作者在行文中從當權者、理學諸生、少數民族士人、鄉紳及下層知識分子五個角度對元代理學的發展過程進行梳理,概括出元代理學發展的特色。
首先,從當權者角度考察了理學發展與元代的社會狀況。作者在該書的第一章詳細研究了元代帝王對理學的態度問題。作者認為從成吉思汗至元仁宗,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矛盾的轉變,為鞏固王權統治,元代統治者認識到了漢族文明的優越性,“蒙古文明在發展的過程中,借鑒漢族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元代理學與社會》,第27頁)進行統治,因而在意識形態層面,對理學的態度也有著明顯的轉變:第一階段為蒙古族統治初期,成吉思汗、窩闊臺和蒙哥在蒙古文化的建設中借鑒儒學思想。成吉思汗任用耶律楚材進行文治改革,為理學在元代的發展奠定基礎;窩闊臺在逐步恢復儒學社會地位的基礎上,修建經籍所與太極書院,舉行戊戌選試,開創元代科舉先河。第二階段為大元王朝開國時期。忽必烈實行漢法,重用儒生,在開設金蓮川幕府與登帝初期大量網絡漢族士人,注重以儒學為教育內容與教育理念,理學“準官學”化即在其統治時期奠定基礎。第三階段為成宗、武宗、仁宗在位時期,繼續施行始祖所推行的漢法政策。成宗、武宗著重提升孔子地位,重視新建廟學,仁宗則更是推行科舉,以程朱理學作為學校教育和科舉選士的主要內容。經過統治階級沉默—思考—崇尚的態度轉變,理學至此發展為官方學術。
其次,從理學后學的角度考察,程朱理學在元代的發展特點可歸納為“傳承中創新”,陸學則主要呈現出“會通中發展”的態勢。作者在梳理元代程朱理學發展脈絡的過程中,以趙復為理學北傳的第一人,以姚樞、竇默、許衡為元代朱學發展的重要代表,以北山學派、新安學派探討朱學的延續與補救。此外,作者還關注到了這一時期陸學的傳承與中興,認為程朱理學雖在元代因受到統治者青睞而上升為官方學術,導致了儒生紛紛趨之,但“宋代陸學的余緒并未銷聲匿跡”(《元代理學與社會》,第190頁),經由劉塤、陳苑、趙偕等人的努力,使得朱陸兩派取長補短、互為補充,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朱學“支離”、陸學“狂禪”的學術流弊。在該書的第二章至第三章,作者不僅探究了理學后學在宇宙生成論、心性修養論、認識論等義理層面的繼承發揚,還對他們的社會治理、教育思想、道統觀念進行了探究。
再次,作者立足于元代社會獨特的階級構成,從文化認同角度探討了少數民族士人學習與傳播理學的具體線索。對不同文化環境下所產生的學術認知層面的矛盾,并不是進行簡單的取舍處理,而是抽絲剝繭地尋找出矛盾生發的可能性原因,盡可能地為造成不同見解的學術觀點尋求思想淵源,這也是該書的優點之一。元代的社會構成決定了文化的多樣性,受少數民族士人認知水平、生活環境、知識結構等方面的影響,理學思想的傳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也在不斷地經受反思與批判。如倡導“以儒治國”的耶律楚材就對理學持否定態度。作者分析指出,作為元代的名臣,耶律楚材對理學的批判并不涉及本體論、心性論、工夫論等具體內涵的沖突,而與其時代背景及學術旨趣相關。其原因一是耶律楚材重視經史詞章之學,因而不滿理學的不事經說;二是耶律楚材曾經出入佛老,在思想上有融合三教的傾向,因此對理學駁斥佛老又在暗地里吸收佛教、道教宇宙本體論、道統論的做法頗有微詞;三是其生逢亂世,儒學觀以經世致用為導向,與理學提倡講學的空疏學風不相適應。耶律楚材的儒學觀實際上是元代很大一部分士人的代表,但其對漢民族儒家文化不遺余力地提倡,仍在客觀上為理學的傳播提供了條件。而以保巴、耶律有尚、孛術魯翀為首的少數民族后裔,也在具體實踐中以理學思想的內在規范性為價值導向。
元代理學的發展有著向上與向下兩條路徑,向上發展有賴于統治者與理學名臣的共同努力,最終將理學逐步發展為官方正統的學術思想,向下發展則更多關注元代理學對社會教育、藝術發展的諸多方面。作為一種時代性的意識形態,理學對鄉村秩序的重建、對文教的提倡,與史學、文學的交融,構成了更為完整的元代文化。
二、《元代理學與社會》的方法論自覺
在《元代理學與社會》一書中,作者具有明確的方法論意識,作者在對傳統史學進行考證的過程中,注重社會史對學術思潮、學者思想的影響作用,將思想史與社會史相結合,使得該書呈現出較為鮮明的方法論特色:
一是以文獻學研究為基礎,資料詳實,論證合理,分析得當。見于該書參考文獻與腳注,古籍文獻資料豐富,不僅包括《宋史》、《金史》、《遼史》、《元史》等正史著作,還包括典章、縣志、通志等專書,這說明作者在對元代理學與社會的關系進行考察時,注重對不同區域的地理風俗、人物文教進行分析,這就使得該書在論證時有理有據,十分具有說服力。元代理學相關研究成果浩瀚,作者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展開的,因此回顧學術史,對研究現狀進行歸納分析在該書中占據很大比重,充分體現了“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的學術自覺。
二是結合歷史事實,運用學術史的研究方法還原元代理學的本來面貌。任一思想的產生都與特定的學術土壤息息相關,是書聚焦于理學在元代的發展與創新,必然要從宋代理學中尋求思想淵源。因此梳理學術史,了解理學內部思想的演變與轉化,分析不同區域、不同派別理學家思想上的異同,有益于“系統地了解元代理學的產生發展與宋代及明代理學的內在聯系,同時厘清元代理學內部各分支的學術淵源和內在聯系”(《元代理學與社會》,第23-24頁),這也是學術史方法研究的優勢之所在。
三是將個案研究與整體研究相結合,既注重對元代理學主要人物的哲學思想進行分析,還注重考察理學在元代發展的整體概況,揭示了元代理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作者認為,元代理學的發展可以從三個層次呈現:(一)在元代王朝進行構建的社會環境中,統治階級與少數民族士人對理學懷疑—審視—崇信的態度轉變過程。(二)不同學術流派的理學家在自我環境與彼此交流中對理學進行反思的小歷史。(三)將理學作為元代社會文化的構成部分之一,論述其對宋元之際,不同學術傾向、各種知識觀念的影響作用,從而將理學發展這一“小歷史”融入元代史乃至中國史的“大歷史”發展脈絡中。作者正是通過對這三個層次的把握,才清晰、完整地勾勒出元代理學的發展線索與社會地位。
四是運用思想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增加了研究的廣度與厚度。思想史與社會史相結合,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重要方法。《元代理學與社會》注重對社會思潮進行比較全面的考察,力圖從元代理學的轉變中透視元代社會的時代特點,以期“了解理學發展的具體路徑及產生這些發展變化的原因”(《元代理學與社會》,第24頁),對民族史的探究、對民族文化融合問題的思考也使得該書擺脫了同類型史學研究過于單一的學術線索,將元代學術史研究向前推進,也為同時期政治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借鑒。
三、《元代理學與社會》的學術價值
作為一部學術著作,理應以學術價值評判其可讀與否。筆者認為,《元代理學與社會》有以下兩點值得稱道:
一是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乏創見,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觀點。如在分析元帝王對理學的態度問題時,詳細論述了忽必烈在李璮之亂后的政策轉變,進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作為蒙古帝王的忽必烈“真的能夠了解漢文化的精髓嗎?”(《元代理學與社會》,第87頁)由此反思帝王與理學發展的實際關系。作者在論述陸學在元代的發展時提出,吳澄師承關系不明晰正是其“合會朱陸”思想傾向的原因之一,其思想表現“不僅僅是辯駁朱陸爭斗的實質,而且對兩家思想有相應的評價與會通”(《元代理學與社會》,第231頁),因此不必要強行定義吳澄的學派歸屬。對學者的學派歸屬進行判斷,是長久以來學術界分析理學家哲學體系與學術傾向的重要依據,然而在吳澄這樣兼宗兩家的理學家身上難免落于僵化局面。
二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該書不僅理清了元代理學發展的線索,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會通精神。元代理學的發展問題,一直是元史研究中存在的重要課題,但由于這一時期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夷夏情懷、文化沖突的作用下,元代學術、文化都呈現出紛紜、繁復的態勢。加之元代理學不比宋代理學創見多,因此長期以來不受學界關注,研究相對薄弱,學術界一向評價不高。《元代理學與社會》一書卻敢于發前人與今人未發之言,論前人與今人未論之處,提出了新觀點、新問題,為后人研究元代歷史提供借鑒。該書還具有很強的學術史意義,填補了宋元之際理學傳播與創新的空白,對讀者系統地把握理學在宋、元、明、清各代的發展具有指導意義。
綜上所述,《元代理學與社會》一書,既關注形而上的思想層面,也關注思想與社會的互動,彌補了當前學界研究元代理學著重個案分析的薄弱,推動當前元代理學研究走向深入。該書還對民族文化融合問題進行了探討,指出沒有元代理學的發展,理學只是漢民族的學術,經過元代之后,理學所蘊含的道德主義精神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