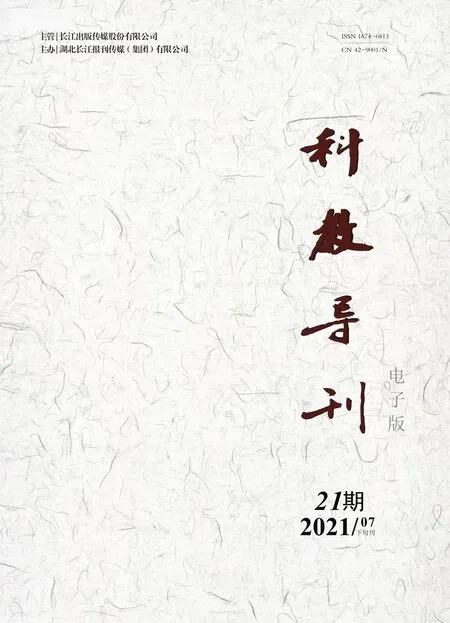藝術院校人才培養過程中藝術與科學協同育人研究
王永平
(廣東舞蹈戲劇職業學院 廣東·廣州 510075)
科學求真,藝術求美;科學在物質世界探秘,藝術在精神世界尋幽。科學與藝術的關聯,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說:“事實上如一個硬幣的兩面,科學與藝術來源于人類活動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著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義”。科學與藝術相互啟迪,從而產生無限的創造力;在達成健康的人格、成就有價值的人生中,科學與藝術具有同等提升作用。藝術院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要注意將藝術與科學緊密結合,協同育人。
1 藝術與科學的區別
藝術創立是在求“美”,科學創立意在求“真”。
真:即真理、真知、真功,是對一切事物的客觀規律和真實內涵的正確反映。真理是一個不斷探索、不停追求的永恒過程;人類的全部文明史,就是一部永無止境的求真歷史,學習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其它一切知識技能,都以求真為起點,以求真為歸宿;藝術院校所教所學包括表演藝術在內的一切知識技能,都是一個求真的過程。求真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精神。學習教育的過程就是求真的過程,就是要探索真理、掌握真知,練就真功。無論真理,真知,還是真功,并不是當先生的天生就懂就會的,也不是書教口傳本身就是真來源的,真來源是人類的社會實踐,是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所以學生要達到求知求學的高境界,就要有實踐第一,人民為本的學習理念和方法;老師除此之外,還要有既當先生又當學生、當好學生才能當好先生的教學理念和方法。
美:即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形象美、作品美、環境美。它除了包括“五講四美”中的四美(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內容外,還有藝術院校固有的或應有的特點或特色(形象美、作品美),也是應當不斷傳承、保持和弘揚的優勢。也就是說藝術院校所學所教內容,無論舞蹈也好,戲劇也好,音樂也好,還是舞美設計等也好,應當追求達到的最好效果和最高境界。從本質上講,美,就是在求真的基礎上實現對精神文明美的終極追求,就是追求文化藝術事業者的完美境界,使之各盡其美,美美與共,齊為大同。
2 藝術與科學的聯系
“科學使人認識物質世界,但科學的高度發展帶來了許多負面問題,藝術使人認識美,它的最大功能應是凈化人、抒發人類的情感,二者的結合是人類的理想,如果結合得好了,人類就進步了。”李政道先生強調智慧和情感,藝術也是,科學也是,它們本質上是一樣的。藝術不是點綴、美化,也不是裝飾,它是一種生存方式、思維方式,而這種方式可以通過科學的方式展示給人們。藝術與科學一樣都是建立在對美的追求之上。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創作方法雖然有所不同,但他們都是從紛亂中找出秩序,從現象中揭示本質,都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3 藝術院校學生對科學與藝術的關聯認識不足及其原因分析
一種不足認為科學是理工科學生在事情。藝術學科缺少科學性,即學科目錄與社會需求有很大的矛盾,我們應關注學科內部的科學問題。另一種不足認為藝術活動只著眼于藝術圈之內,對藝術教學、藝術實踐、藝術理論與相關學科交流借鑒的認識不足,在藝術的發展方面,僅限于藝術與社會、藝術與政治、藝術與個人感情,新的藝術活動方式,新的藝術通道的探索不足。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從歷史上看,藝術比科學的出現要早得多。從廣義上意義看,與“表象思維”相伴生的就是各種藝術的雛形。“抽象思維”的出現,雖說為“科學”的問世提供了重要條件,但從狹義上看,真正的“科學”是出現于近代的四五百年前。各自問世的藝術和科學,兩者相隔時段很長,不存在所謂兩者“相分離”的問題。
第二,藝術與科學的分離是以近代各學科的“分門別類”為背景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分”不是藝術或科學之過,說到底,它是“抽象思維”之過。通過“抽象”的“分”,朦朧的“整體”看得清晰了;又因為“分”,“整體”蕩然無存了。
第三,克服藝術與科學根體分離的出路,就是讓思維主體自覺意識、主動協調“表象思維”與“抽象思維”。因為前者與“表象思維”相貼近,后者注重運用的是“抽象思維”。現在流行著一種說法,為著克服學藝術的不懂科學、學科學的不懂藝術的狀況,應該設法讓兩者相揉和。比如學藝術的要開設科學課,學科學的要開設藝術課。這主張干脆利落,能立竿見影。但能否讓學者真的感受到“自己缺乏的正是眼下要學的”,就有疑問了。因為它完全屬于“外在操作”,并不顧及學者的“切身需要”。當然,形式(組織)上的執行是需要的,為人擔憂的可能陷入走走形式。
4 藝術院校培養人才避免藝術與科學分離的對策
第一、圍繞“一個主題”,設法尋求兩種(藝術的、科學的)表達方式。
例如,1995年,科學家李政道與畫家吳冠中聯合舉辦主題是“科學與藝術”研討會。會上展出畫家李可染的《對撞的牛》和吳冠中的《柳與影》,前一幅是表達“質子對撞”的,后一幅是表達物理范疇“對稱與不對稱”的。用“形象”表達“抽象”,這不正是要求得兩思維的協調嗎?你無論從物理學意義上看“畫”,還是在看“畫”中思考物理學意義,都各有所得,各有感悟。
其實,對科學家與藝術家聯合舉辦以“科學與藝術”為主題的研討會,往更深層方面去思考,它還隱含著另一重意義:從表達形態來看,一種是自然科學,另一種是人文科學,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互不相關的“分隔帶”,你搞你的科學探索,我搞我的藝術創作,互不干擾相安無事。但是,誰曾料到,無論是搞科學發現(創作)的還是搞藝術(發現)創作的,都是地球演化出人類的“同一個”大腦,無論個體如何奇特,他還是人腦,只要是創作(而不是日常活動),就要充分調度兩個“半腦”各有所側重的功能發揮,就要發揮直覺思維——通過直覺“圖示”(它為直覺所發現又為直覺理解提供直接“判據”)抓住“對象”(或發現的或創作的)的本質。據研究,這“圖示”(科學研究的“理想構圖”、藝術創作的“雛形構圖”)“恰恰是溝通這兩種文化的橋梁”。
第二、藝術工作者應主動向科學這邊“靠”。
這里的“靠”是指主動了解科學的研究成果,從中汲取營養。例如,創立立體主義的畢加索,他的畫作是很少人能看明的“立體”。人們回到他創作的“背景”中,認定在創出他的風格中,是參照了許多學科(數學、三角學、精神分析學,甚至音樂)研究成果的。但他卻在公開場合作了否認,這否認更加引起了人們對他如何創作的興趣!
在現代,科學發現(創作)與藝術(發現)創作的相互“參照”,已不屬罕見之例,尤其藝術家對科學探索及其成果的熱心和關注,似乎要勝于科學家對藝術家創作的“參照”。當然,藝術家“熱心”于科學,并不在于對科學探索所獲得成果的“理解”,正如你要求畫家李可染對物理中的“粒子對撞”、要求畫家吳冠中就物理學中的“對稱與非對稱”“理解”,基本變得“隔行如隔山”那樣,來得強求困難!那么,怎樣才能使藝術家不僅“接受”科學,而且從中獲得啟示,作出畫來呢?這過程的關鍵就在于,藝術家通過對科學家將科學知識“轉換”為“日常所見”的“了解”(不是“理解”!),并將“了解”“轉換”為自己認定的(如“兩牛對角”“柳與影”)“直觀表象”后,再用藝術畫作的形式作出表達。
同樣的過程,也往往出現在另一種形式上。如有些藝術家對科學著“謎”,不在于科學家著作中表達的深奧拗口的“知識”,而是其中配與知識的“示意圖”,尤其是“理想實驗”的“圖示”。對藝術家來說,書的內容是讀不懂、不理解的,但科學的“圖示”(雖說它是表意的,但又是直感的)不僅可以看,而且在看中能獲得啟發。藝術家就是在啟發中突發靈感、轉入繪畫創作的。如荷蘭畫家埃舍爾就是依據“彭羅斯臺階”(由天體物理學家彭羅斯設計),創作了《上升與下降》的名畫。
第三、科學工作者應自主地向藝術這邊“靠”。
上面列舉科學家李政道就是一個例子。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更典型。他隨身帶小提琴,酷似隨時登臺演奏的小琴家。他不是一位演奏家,但一旦有機會,所演奏的小提琴曲,與專業演奏相比毫不遜色。他很喜歡音樂家巴赫、莫扎特和一些意大利以及英國的老作曲家。他憑直覺,抓住作品是否具備結構上的“內在統一性”,聽出該作曲是否“缺乏深度”,是否流于“淺薄”,是否泛起“平庸”,總之,他從藝術欣賞中獲得的不止于情感、樂趣的享受,更多時候是從中獲得科學探究的靈感。
在現代,普通教育的改革大體沿兩個方向展開,一是從體制上改革。主要著眼于教育活動的組織方式和學科組合方式兩方面。前者更重視活動主體和活動內容來確定如何組織的問題,是分班還是拆班、是行政規范,還是自由組合,都是值得探索的;二是從如何設法挖掘學者自身潛能方面展開,人們力求尋找到最及時發現、最有效挖掘學者潛能的途徑、方式和方法。
目前,人們似乎更聚集于“怎樣發現、培養未來科學家和藝術家”上。一般認為,個體在“兒童時代的興趣也許便預示其后來的職業選擇”——一種喜愛審查設備的內部并試圖揭示“內部機制”的少年,一種能用一小塊木頭制作木偶的少年;前者將來很可能就成為科學家,后者就會成為未來的藝術家。而過程發展的關鍵就是及早發現及時提供相應條件的培養。現在,無論是學者本人,還是家長、學校、社會都給予高度重視。但是,這一般的“重視”卻“掩蓋”著不為人們所“重視”的“根本”,這就是:大腦統轄著的“左半腦”與“右半腦”的開發,要借助“抽象思維”與“表象思維”,而擅長“抽象思維”的是科學探索活動,與此相應的“表象思維”卻是供給藝術創作活動的;要使“抽象思維”與“表象思維”相協同,必須借助既能提供抽象“概念”又能兼顧表象的“圖式”的“直覺思維”這座“橋”。這是科學發現(創作)與藝術(發現)創作所相“溝通”之奧秘。但是,就是它,卻被時時提積極倡導要大力挖掘人的“潛能”的人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