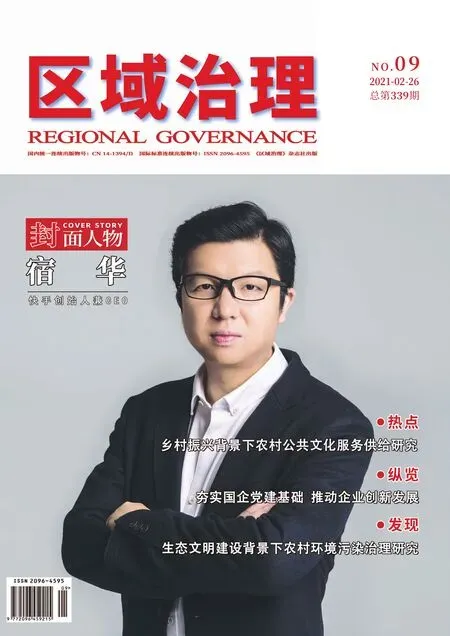新時代“楓橋經驗”在社區治理中的啟示與應用——以長沙市湘園社區為例
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劉嘉奕
一、理論框架
本文構建起一個“內涵-運用-結果”的分析框架,在該視角下,探索社區對新時代“楓橋經驗”是如何自覺運用和發展的,并發現問題,實現社區善治。
(一)內涵的多樣性
(1)黨建引領,以群眾為主體。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時代“楓橋經驗”才能堅持和發展好。而楓橋干部群眾從以說理斗爭的方式改造“四類分子”,到改革開放八九十年代探究綜合治理社會治安,到二十一世紀“和諧楓橋”和“平安楓橋”的建設,再到三治融合的新時代“楓橋經驗”,這一發展過程都始終以人民為中心。因此堅定人民立場、強調民眾參與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內涵之一。[1]
(2)運行高效,矛盾就地解決。我國現階段矛盾主要表現形式仍是人民內部矛盾。其遍布經濟社會生活中與改革發展的各領域,[2]“楓橋經驗”緊緊圍繞“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原則,開展源頭糾紛治理,這不僅降低了各社會成本,[3]同時也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和諧。
(3)成果共享,和諧穩定。實現社會和諧穩定的首道防線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但社會和諧穩定不只是治安問題,它還包括民生與民權等問題。而第二道防線以人為本,共享成果才是根本。為此要將工作從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拓展至“善治”范圍中,[4]而“楓橋經驗”正是沿著該路徑發展的。楓橋經驗順應時代發展,讓社會更加和諧穩定,讓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二)運用的創新性
社區根據實際需求對新時代“楓橋經驗”拓展創新,在運用領域上實現從農村至城市、從單向治理至網格化的并行,[5]以及在治理機制上從單一權威至多元共治、從政府管控至社會合作的轉變。[6]社區中建立起基層治理“網格”,讓社區管理服務從“橫向至邊、縱向至底”的全民覆蓋,實現社區居民從“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型,[7]為我國實現社會共治提供了經驗。
(三)結果的利弊性
新時代“楓橋經驗”率先探索黨政主導,培育了民間自治力量,形成了政府管理和社會自治的有效互動,降低了政府治理成本。但隨著社會轉型加劇,新時代“楓橋經驗”在社區治理主體、治理功能以及治理技術上出現相了應的弊端,需要我們結合實際去解決,推動社區治理現代化。
二、新時代“楓橋經驗”在長沙市湘園社區的實際應用
為了更好地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化解中的作用,實現“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湘園社區自覺運用和發展“楓橋經驗”,譜寫“平安樂章”。
(一)湘園社區的介紹
社區位于省會行政中心核心腹地,區域總面積約為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7820人。社區于2010年8月建立,起初社區公共設施薄弱、環境差,居民素質較低,導致管理難度加大。近年來,湘園社區在上級黨委和政府的指導下,秉持“以人為本、服務居民”的宗旨,先后榮獲全省和諧社區建設示范社區、全省“雷鋒號”志愿者工作站、市級“精品示范社區”等80多項榮譽,實現了從“白手起家”至“滿墻榮譽”的飛躍。
(二)湘園社區的治理經驗
1.“1+N”基層黨建工作法與“GRS”網格黨建工作法
其中“1”是指社區黨總支部,“N”指管轄區內外單位黨組織。社區與32家單位的黨組織簽訂《共建共創協議書》,并聘請13位駐社區單位黨組織的專職副書記兼任社區黨總支部委員,相應的共建單位承諾為社區每年辦好2-3件實事。在樓道中,隨處可見書籍、報紙雜志的“黨建之窗”,居民可以隨意取閱。共建單位也為社區辦理晾衣架安裝、天然氣安裝等便民實事將近200件。同時湘園社區還實施了“GRS”網格黨建工作法,其中“G”代表黨群小組,“R”代表資源,“S”代表服務,利用資源精準服務于民。“1+N”“GRS”工作法打造的“共駐、共建、共治、共享”基層社會治理格局,跑贏了服務居民的“最后一米”。
2.“六自”工作法
社區以居民“自提、自議、自決、自辦、自管、自享”的“六自”工作方式,評選表彰出善美家庭和最美樓棟,用以傳揚優秀家風文化與和諧文明理念。把社區的農民安置區按樓棟特點劃分為“明德網絡”“狀元網絡、…”等13個網格,按“黨總支領導,居民自治”的思路,每周開展集體清掃、家風知識分享學習等活動,每月由居民檢查、點評與總結,把家庭的參與情況轉換成文明積分并歸檔,憑此作為評選依據,并在次年2月表彰,這大大調動了居民的積極性。該小區僅用27天便完成了提質提檔,被長沙市評為2016年度提質提檔工作第一名。
3.營造志愿服務氛圍,打造特色服務品牌
“志愿服務”已是湘園社區的特色標簽,社區的市民大學為居民提供了緊貼實際的課程,豐富了老人晚年生活。同時社區也成功打造了“滿嗲和諧鄰里工作室”特色工作品牌。該工作室由居民張慶華在家中自行創辦,基本實現矛盾就地解決,不出社區。自工作室成立9年以來,先后調解了大約200多起矛盾糾紛,社區還成立了“李麗心靈教育中心”以及10多家社會服務團體,參與社區志愿服務的志愿者人數有500多人,整個湘園社區都充斥著志愿者忙碌的背影。
三、新時代“楓橋經驗”在湘園社區治理的實踐特點
(一)治理方式具有先進性,但在智慧化方面有待提升
2016年3月,湖南首個智慧養老系統落戶于湘園社區,長壽老人家湘園社區養老服務中心用先進的技術為社區老人組建了生命體征數據庫,實現了足不出戶的養老碎片化服務。同時重視居民的情感與精神文化的需求,將心理干預與人文關懷加入到治理當中,利用互聯網、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培養居民的主人公和共同體意識。但基于信息化應用的智慧化水平還有待提升,特別是在抗疫期間對數據信息的挖掘與整合上,對非核心數據的準確性和數據間易出現“數據孤島”的現象,將阻礙社區治理的智慧化發展。
(二)重視將矛盾化解在基層,但存在過度治理的隱患
湘園社區充分依靠和發動社區居民、社會組織團體,形成以人民調解的方式來化解矛盾的社會共識,矛盾糾紛基本實現了“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這大大降低了調解糾紛的行政成本,但社區居委會會將“矛盾不上交”直接視作考核指標甚至最終目的,忽視了“楓橋經驗”中“發動與依靠群眾”的本質特點,導致社區居委會出現“包辦主義”的潛在風險,讓市場主體與社會力量參與缺乏長期有效機制。
(三)治理主體多元化,但治理主體功能不均衡
湘園社區在治理主體上堅持以黨建為引領,社區居民為基礎,整合各行業志愿者、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發力。但社區“楓橋經驗”呈現出以街道、社區居委會等作為節點的網格化自治布局,這些基層自治組織大多被行政事務纏繞,其精力有限,湘園社區大部分調解工作也都交給了社區調解工作室處理,而化解矛盾糾紛的主力軍應是公安機關與基層民警,公安機關與基層司法部門在解決矛盾糾紛工作中分工不明確,會直接影響政府部門間、政府和社會之間以及社會與居民間的有效聯動。
四、新時代“楓橋經驗”對當代社區治理的結論建議
(一)堅持以人民滿意為宗旨
在“楓橋經驗”形成初期,矛盾糾紛就地解決,不上交的方式減少了治理成本。但進入新時代后,“矛盾不上交”的核心目的并不僅是上交矛盾本身,還要保質保量、和諧穩定地實現社會治理。因此政府應構建科學的社區治理評價機制,不應僅以“矛盾不上交”作為考核依據,還應加入人民滿意度、治理回饋等評判因素,在發揮人民主體作用的同時,為社區治理減負。
(二)提高社區治理的智慧性,打造自治、德治、法治融合的社區治理體系
要實現以社區為目標的信息管理向以社區為核心的轉變,須重視智慧化水平。特別是在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衛生事件時,將社區視作信息工作的來源與主體,特別是疫情防控中的人員登記、行動軌跡摸查、需求統計等工作,都可以借助技術工具依靠社區內生力量來完成,從而收集準確的數據且組建社區大數據治理系統。同時以“心理咨詢屋、法律咨詢熱線”等形式,加大“情感投資”與“人際建設”的投入,打造三治融合的社區治理體系。
(三)明確社區職能,銜接司法系統與行政系統
社區須明確自身的職責和權限,加強其管理和服務的職能,拒絕無償承擔不屬于其職責范圍的工作,確保開展工作不超權、不越界。同時,應明確與之相配合的基層法院與街道辦事處的職能,保證在處理問題時各司其職,不轉移責任、不推卸責任,各部門在其職權范圍內應相互配合社區居委會行使職權,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