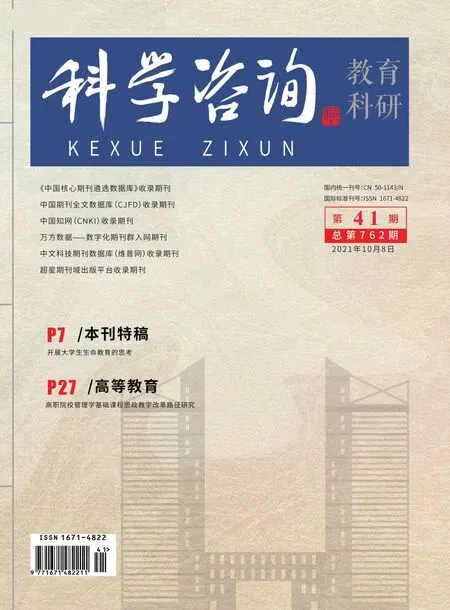信息爆炸時代大學生學習模式的變遷
——以“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研究”課程教學改革實踐中的學生為個案
楊 笛
(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 江蘇南京 19163)
一、信息時代對高校教育實踐的挑戰
計算機的出現和逐步的普及,信息對整個社會的影響逐步提高到一種絕對重要的地位。信息量、信息傳播的速度、信息處理的速度以及應用信息的程度等都以幾何級數的方式在增長。近幾年來信息量快速發展,其發展的速度如爆炸一般席卷整個地球。因特網使得信息的采集、傳播的速度和規模達到空前的水平,實現了全球的信息共享與交互,它已經成為信息社會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和“副作用”則是:洶涌而來的信息有時使人無所適從,從浩如煙海的信息海洋中迅速而準確地獲取自己最需要的信息,變得非常困難。這種現象被稱為“信息爆炸(Information Explosion)”“信息泛濫”。 同時,手機等移動終端的迅速發展伴隨“信息爆炸”的狀況,開始徹底改變人們的閱讀、學習甚至思考決斷模式。“碎片式閱讀/學習”“知識外掛”等現象在新一代的學生逐漸顯現,并對他們在課堂內的學習方式和知識學習吸收的模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帶來的這種信息過載,使得信息搜索能力成為新時代人才的重要素養之一。近幾年國內外大量與高等教育相關的研究中,這一主題都獲得了極大的重視。在學生能力、學校課程設計、教學內容、教材設計、教學方式、能力培養系統方案等方面都對其進行了詳細研究并有許多實踐性案例可供跨地域、跨文化、跨學科借鑒和對比研究。此外,隨著互聯網+以及各種移動終端設備的發展,對如何利用新興的設備和信息傳播模式進行教學方式的創新國內外的研究和探索也在不斷發展與豐富中。而同時,教育學和心理學的學者也開始逐漸意識到,新的信息傳播模式和設備更新,對于學習者本身的思考和信息接收方式與心態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變化必將對學習和教育雙方都提出新的挑戰。但此類研究還處于對各個不同群體進行大規模調研和實驗階段,具體對教學實踐的影響還基本處于空白狀態。
新的信息傳播技術、設備所帶來的信息搜索、知識攝入和學習、閱讀模式的變化對于新時代大學生不僅僅是在學習方法,而且在學習心理、思維方式,以及知識儲存模式的根本性影響逐漸被心理學認識并將進一步對教育學的研究提出新的挑戰。與此同時,在面對新一代學生在課堂教學中體現出的學習特征時,教學方面的改革與創新也勢在必行。而工作于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在學習和等待心理學和教育理論在相關研究方面有更進一步研究成果的同時,直接針對自己所教授的課程和學生群體,進行更有針對性的調研并實踐教學改進,從不同學科和不同學生群體中獲得經驗性研究成果將成為對這一領域的研究與探索的一個大趨勢。
二、針對“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研究”課程的學生的研究
(一)研究的設計與關注的主題
基于此,作者嘗試以學校勞動保障專業針對大三學生開設的自主發展課程“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研究”中的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觀察并調研新時代學生學習和知識吸收的新特征。
本研究以對全校范圍內147位學生校園偶遇式提問,42份針對該課程學生的小問卷,3次共8名高校教師參與的小型研討;8次共27位學生的焦點座談;12位學生的單獨訪談;一學期18次課程的教學互動與參與式觀察為基礎,針對以下問題進行了研究:
?互聯網+時代,學生在學習和閱讀方面有什么新的特征與變化;
?信息爆炸時代信息過載對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哪些影響;
?這些變化與影響對于學生在課堂學習中的表現的影響;
?這些變化對于學生對于課堂學習中知識價值等級分類的影響以及學習過程中信息記憶習慣的影響;
?面對這些變化,教學內容必須做出的回應和可以嘗試的調整。
研究關注現有的信息傳播獲取途徑和信息爆炸狀況、移動電子設備的大量使用對學生學習以及課堂互動產生的影響;依靠問卷、教師研討、學生座談、個案訪談,教學實踐中的參與式觀察(教師視角+學生視角——有一位學生研究助手),課后學生訪談等方法,多方位、多視角進行研究。
(二)研究的主要發現
1.手機已成為學生獲取信息的主要工具之一
調研中發現,所有被調研學生都表示,學習中有不懂的東西最先使用的方式是用手機查詢,其次是問同學(其中一半以上的學生將用手機單獨詢問和在群里詢問排在直接問身邊同學之前),然后是電腦查詢,最后才是詢問教師和查找專業書籍。且除兩位同學外,所有學生的信息查找只做一次性查找,即直接針對想要詢問的問題進行一次性搜索,以獲得基本信息為滿足,不會針對已獲得的信息進行進一步擴展性查詢或更多相關信息查詢或多信息來源信息比對。
可以看出,“互聯網+”的廣泛運用在幫助年輕一代更靈活方便地獲取信息的同時,也模糊了學生們對于信息的價值判斷能力,無法準確認識到基礎信息和其他更有價值的信息、知識之間的差異,失去獲取更有價值的信息的動力甚至是挖掘有價值信息的能力,大多學生都執迷于搜索引擎能帶來所有或差不多的所有信息,沒有出現在搜索中的就是不存在的或沒必要深究的這樣的認知中。這對于學生的學習尤其是研究能力的培養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2.在課堂教學中手機很少被用來獲取教學相關的信息
有在課堂上使用手機的經歷,因為本專業中有教師使用與課堂輔助教學,所以也是所有學生都有在課堂上為了課程內容使用手機的經歷,除此外三成學生最主要的因學習內容而在課堂上使用手機的情況是緊急應對(或幫同學應對)老師的提問。但同時,所有學生也都表示,在課堂上為課堂教學無關的原因使用手機的次數和時間遠超過為課堂內容使用的次數和時間。僅有一位同學表示除學習需要外,僅會被動地使用手機(即接收短信、微信、QQ、電話等,以防有緊急信息),其他學生皆表示會主動用手機瀏覽非教學相關網站、頁面、朋友圈、小說……
學生表示課堂教學內容并不會激起他們使用手機查找教學相關內容的原因是重要的內容都在課本上了,課本上沒有的應該也不重要,如果真的是比較重要的課本上沒有的,教師會在課上講,沒講到的會沒進一步介紹的必然不重要。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新一代的學生對于教師和教科書的權威的質疑是一直存在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并沒有興趣利用手機和互聯網提供的信息便利去獲取更深入的專業學術知識而是滿足于教科書和教師的教學內容。僅有的表示會擴展學習的5位學生,也并不是根據教學狀況,而是因為在網上了解到本學科的一些前沿研究主題和“新概念”或者新工具,帶著好奇心地去了解,完全脫離課堂教學和師生互動,且全部表示只是了解了下,并沒有學會學懂,當也沒有意識要去詢問老師。
3.“一心二用”的錯覺
幾乎所有主動使用手機進行非學習用途的學生在給出類似課程本身比較無趣,講的內容自己以前學過,覺得除了最后考試拿學分課程本身沒有意義等理由之外,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個類似的理由(因為這一方面大多是在座談和訪談中涉及,不是標準化問卷答案),就是認為自己在使用手機的同時也可以聽課,并不會漏掉關鍵的教學內容。這種自信自己能多線程、多任務并行的態度其實應該是長期使用移動通信設備以及電腦的結果,移動通信設備使得人們可以在行動間同時進行閱讀等任務,這讓學生對于自身“一心二用”的能力過度自信,而電腦可以多窗口、多程序同時運行,前臺后臺運作的獨特模式,使得學生養成了在手機和電腦上可同時處理學習、社交(QQ微信)、購物等任務的習慣,并將這種習慣或者說自信帶入了課堂。雖然在深入交流后,大多學生也會提到有的課程因為內容非常有趣,或者互動過多,或者需要“費腦子”而無法“一心二用”,但他們基本都沒意識到,這種無法一心二用的狀態正是說明一心二用其實會極大地影響到他們對于課堂內容的有效吸收,他們并沒有真正意義上做到一心二用,只是與沒有手機的時代在課堂上開小差、偷看小說的學生在做著同樣的事情而已。對于這種狀況是否是課程質量問題導致學生作出的一種選擇的問題不屬于本研究的探討,本文關注的是,正是長久以來的手機和電腦使用,給了他們可以“一心二用”甚至“一心多用”的錯覺以致忽視了他們事實上對于課堂學習的關注力投入不足的問題,這種忽略可能會很大地影響學生對于自我學習表現的評價以及學習精力的分配。
4.學生已習慣電子版文獻的閱讀,但忽略了自身在使用電子文本時深度學習能力的不足
而且,雖然學生中喜歡閱讀紙質文獻教科書的人數仍超過喜歡閱讀電子版的(大致比例為6∶4),但超過七成的學生表示電子版的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學習,所以替代紙質版的文獻完全可以接受,甚至有一半的學生支持老師以電子版的方式(最好是手機)傳遞拓展閱讀、學習文獻。但是除2位同學外,幾乎所有學生都表示教科書還是偏向紙質版,因為“有利于考前復習”。當問及為什么紙質版在考前復習上更有用時,學生大多表示因為可以寫寫畫畫(有其他在旁同學指出,很多閱讀軟件也可以做到),所以記得牢。也有的表示不知道,就是用紙質版更能記得住,看得進去。在被問及既然紙質版其實更有助于他們記憶和理解,也就是事實上,即使是對他們這一代來說,也是紙質版的學習閱讀效果要好于電子版的情況下,為什么他們之前仍認為電子版不影響他們的學習閱讀時,除一位學生反思自己對于閱讀投入和學習質量的判斷有誤外,其他全表示,因為之前的閱讀并不需要記憶,所以,電子版的閱讀質量和學習狀態是足夠的;同時這些學生也全部表示,覺得考試非要求記憶本身其實很沒必要。
5.“知識外掛”的迷思
事實上,“互聯網+”與信息爆炸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學生對于知識是“隨手可得”以及知識可以“外掛”的錯覺。調研過程中,所有學生都曾一次或多次表示了既然許多知識我們都可以隨手搜到,為什么還要逼他們去學習、記憶。幾乎所有學生都提到,有某些被迫學習的內容(具體內容或類型因人而異)其實在將來如果需要時完全可以現搜現用,沒必要現在學,而如果將來用不到那就更沒必要學了。學生因為手機以及利用手機對互聯網的隨時可使用性,使得他們與一個巨大的知識信息存儲有了聯系,并對這種聯系產生了一種擁有隨用隨取的“知識外掛”的錯覺,而因為大學生對于自己學習力的自信,對于使用“知識外掛”的能力也就產生了過度自信。當作者把這一狀況在教師研討中與其他教師分享時,其他教師都感到吃驚并表示,足夠廣博的基礎知識的掌握,包括記憶和理解,才有可能激發進一步綜合性思考,綜合性思考帶來結構性的知識理解以及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和靈感,可以“外掛”和被調取的知識只是最初級的信息,不能在大腦中形成足夠的知識儲備就無法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思考,那么就連要調取什么樣的進一步的信息的意識都不會有了。有一教師更是表示,這就跟一個坐在圖書館里,然后表示因為自己可以隨時查到需要的資料所以沒必要學習,需要時再說一個樣子,只不過手機、電腦的搜索引擎縮減了查找的時間而已。
同時,也是類似“知識外掛”這種想法,使得所有學生都有把老師推薦的視頻、文章等資料,或平時看到的“有用的”資料保存或收藏后卻沒有進一步閱讀的情況,除了1位同學坦承將來大概也不會閱讀,其他學生都表示將來“有空的時候”“需要用的時候”會閱讀學習的,但其中五成以上學生表示,到現在為止,這類資料并沒有被再提取學習過。
三、結束語
從研究結果來看,“互聯網+”和信息過剩時代給學生的學習方式確實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但更大的影響卻是在他們對于這些影響有多大的錯誤判斷,對于“一心二用”“知識外掛”等因長期使用互聯網和移動終端而對自己的學習能力和知識獲取能力的過度自信以及多層次信息調取和“挖取”意識的不足,使得在信息暴漲時代,信息的豐富并沒進一步促進學生專業知識的豐富,也沒能更好地促進課堂教學活動。作者認為,其實當務之急,是破除這種種迷思,讓學生意識到,去除了信息獲得的便捷性和呈現的多樣性,學習的內核和需要的付出其實并沒有巨大的變化,而知識的真正獲取吸收乃至轉化為可能的思想輸出的過程仍必須通過自己的漫長努力。而要使學生做到這一點,教師應該在教學中以不同方式刺激學生使用移動終端和信息搜索參與不同程度的學習任務,讓學生在實踐中意識到,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