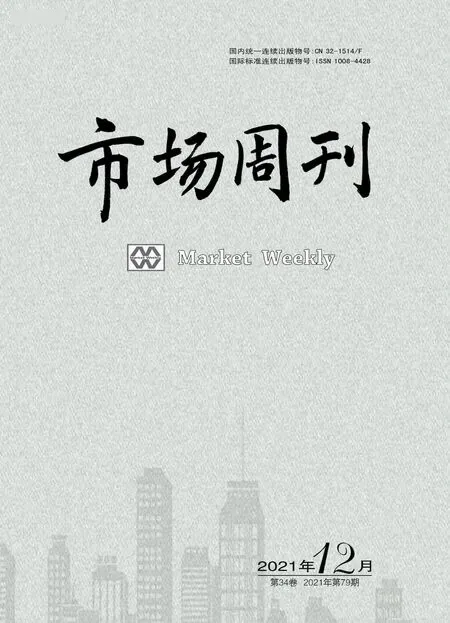廣西城鄉失獨老人的差異性分析
李月悅,林恩伊
(廣西大學,廣西 南寧 530000)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我國為調整“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的人口增長模式,推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倡導“少生、優生、優育”。以獨生子女為核心,向上輻射兩代直系血親的“421”核心家庭結構隨之形成,并逐漸成為時代主流。此舉在優化我國人口結構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失獨”則為其一。
深入調研后,筆者發現,廣西雖采用城鄉統一的特殊扶助金標準,但作為少數民族聚居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城鎮化率雖連年上升但農村人口仍占比明顯①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廣西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為12.2%,同比增長了2.96個百分點,而城鎮化率在2020年進一步提升,城鎮人口占比首次超越了農村人口占比。,城鄉經濟水平不斷提升但基礎設施、醫療條件等多方差距顯著,故使得城鄉失獨老人在失獨群體的共同需求外,呈現出程度不同的需求傾向,尤其在精神狀況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分化明顯。
二、廣西失獨老人的現有規模
所謂“失獨”,即根據計劃生育政策只生育了一個孩子,在孩子因故去世后未再有存活子女的現象。“失獨”是內源性風險與外源性風險并發的結果,而我們聚焦的僅為政策的內源性風險而導致的“失獨”,即“政策性失獨”。
關于廣西失獨老人的規模一直以來都缺乏官方數據的支撐,為了更好地進行人口調查與研究,學術領域針對失獨群體測算歸結了模型估計法、統計推算法等兩種方法,在以上計算方式中,尤以孩次遞進法在研究中的使用頻次最高。
所謂孩次遞進法,即觀測同一批已婚育齡婦女,統計生育過第N個孩子的婦女中將可能再生育第N+1個孩子的婦女人數的比例,由此來觀測不同生育孩次的婦女可能形成的再生育趨勢。學者王廣州曾基于年齡-孩次遞進模型,估算出2007年49歲及以上全國獨生子女的母親總量在30萬以內,享有失獨扶助的人群在58萬以內,死亡獨生子女的母親規模將在2038年達到110萬左右;同時根據其測算,廣西49歲及以上死亡獨生子女母親人數將在2021年達到18399人,其中非農戶口為7556人,農業戶口為10843人。
另有學者基于城鄉的二元差異對失獨規模進行估算,得出2010年全國失獨家庭規模——農村158.57萬戶,城鎮82.69萬戶,其中49歲以上的失獨父母,來自農村的有55.3萬人,城鎮有26.8萬人,到2030年相應規模將分別達到85.1萬人和57.2萬人。
廣西現有可查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7月,柳州市柳北區約有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400戶;截至2017年底,南寧市興寧區有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300戶;截至2018年,東興市有計劃生育失獨及困難家庭28戶;截至2020年,欽州市擁有失獨家庭共計180戶,其中60歲以上失獨老人120人,失獨失能3人。
由此可見,廣西失獨老人群體的數量在全區總人口中的比重不可小覷。
三、城鄉失獨老人的差異簡析
自2012年“失獨”問題爆發以來,學界對于失獨老人的養老挑戰已基本具備共識——無論是基于“風險-脆弱性”分析視角,還是通過人口老齡化視域,抑或是福利多元背景、社會工作理論中的優勢視域,大都認可并指出失獨老人的養老困境主要體現在經濟扶助、精神照護及保險供給等層面。而經調查研究發現,廣西作為西南地區的重點發展地區之一,其失獨養老所面臨的挑戰與上述理論研究結果高度契合,且在城鄉方面存在明顯二元分化。
(一)經濟扶助:形式標準一致,實質公平難斷
廣西采取城鄉統一金額的扶助金標準,2018年①本文所示數據來源于廣西統計局網站及《中國統計年鑒》,均已為最新可查數據。將計劃生育家庭特別扶助金從每人860元/月(中央財政負擔272元、自治區財政負擔588元)調整至每人970元/月(中央財政負擔360元、自治區財政負擔610元),該數額僅次于陜西,在全國各省市中位列第二,遠高于國家統一標準(城鎮每人340元/月,農村每人170元/月)。且根據2019年《中國統計年鑒》,廣西農村年扶助金與人均消費支出的比例較城鎮高出42.72%,農村年扶助金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較城鎮高出51.61%(廣西農村人均消費支出12045.0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675.7元/年;城鎮人均消費支出21590.9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4744.9元/年;農村年扶助金與人均消費支出的比例為96.64%,年扶助金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85.11%;城鎮年扶助金與人均消費支出的比例為53.91%,年扶助金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33.50%),城鄉差距在全國各省市中高居首位。
僅以上述數據觀之,廣西針對失獨老人特殊扶助金的發放數額相當可觀。然而,即便農村失獨老人的經濟扶助水平遠高于城市,但就長遠來看,城鄉失獨老人在經濟層面的抗壓能力仍存在突出差異。一方面,農村失獨老人的收入來源較城鎮相對單一(收入來源所占比重見表1):尤其部分以務農為主的失獨老人,本身無退休金等穩定收入,其一旦失去勞動能力,將直接面臨生存困境。另一方面,農村社會保障覆蓋范圍較城市局限性明顯:尤其在醫療條件差、入保率低等現實境況下,不排除因為子女生前治病、或本身身體狀況欠佳而導致的入不敷出、經濟壓力大等情況,故僅以金額作為比較,并不能客觀評價其扶助保障水平,也無法有效地緩解失獨父母的后顧之憂。且因城市和農村本身在物價水平、生活成本等方面存在不可忽視的差異,同等扶助金于城鄉失獨群體的實質價值亦難判斷。

表1 2019年城市和農村人均收入各項指標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二)精神狀況:典型特征顯著,排斥程度迥然
失獨老人作為社會特殊群體,唯一子女的離世對其精神和心理都造成了莫大的打擊,除孤獨寂寞和敏感脆弱的典型表現外,其還將經歷應激期、過渡期、恢復期的漫長過程,導致適應的困難和社會交往急劇減少,社會支持網絡迅速解體。拋開共性而言,環境和生活模式的差異是對城鄉失獨老人精神狀況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
在人口流動速度、宗族關系親疏、生產勞動方式等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市和農村失獨老人在人際關系、社會排斥方面形成了較大差別。前者會在相對陌生的關系中隱匿自我,以快節奏的生活沖淡喪子的悲痛情緒,從而達到自我療傷與保護的效果。與此相反,后者所囿于的“強聯系社會”,不僅使其在熟人高度重合的生活圈中難以逃離,且傳宗接代、封建思想文化的潛移更易導致農村失獨老人在過分關心與刻意疏遠的環境情緒中深陷藏無可藏的境地。進一步封閉自我增加了農村失獨老人社會排斥心理的同時,無形中也對其與社會的進階交互造成了二次阻礙。
(三)保險供給:普適保險建立,入保問題猶存
子女的唯一性即意味著脆弱性、稀缺性與非可替代性,故而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背景下城市與農村所面臨的社會風險日益趨同,然而,城市卻因較農村具有更優厚的資源支撐而在抗風險能力上稍勝后者。
于城市而言,基于社會保險體系普遍建立、醫療水平和養老基礎設施完善的背景,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方面優勢盡顯。而農村地區因地處偏遠、資金聚集力尚弱,導致部分社會保險項目落實困難。盡管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方面已漸完善,但與城市相比仍存較大差距。
國務院于2016年出臺的《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整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兩項制度,廣西緊跟《意見》精神,旨在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醫療衛生的城鄉差距雖逐漸減小,但落差仍不容小覷:醫療費用投入加大,但城市費用增幅大于農村;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均,呈現出城市醫療機構較為集中,而農村醫療布局相對稀少的現象(表2);專業衛生技術人員數額配比差異明顯,城市的醫療人才配置較為豐富,而農村仍存較大業務人才缺口(表3)。

表2 2019年廣西城鄉醫療機構床位數

表3 2019年廣西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 單位:人
實際上,由于經濟收入水平較低以及對政府相關政策缺乏了解,農村居民選擇較低檔次養老保險,甚至不繳納養老保險的情形仍然普遍存在,其中未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高達89.2%。
四、城鄉失獨老人差異的二元破解與一元嵌入
差異化體現往往是需求層次的第二表達。誠然,廣西城鄉失獨老人具有失獨群體的共同需求,同時也因為群體特征的差異而產生分化,顯現出程度不同的需求傾向。
結合城鄉一體化的背景,文章提倡在農村人口市民化的過程中嵌入城鄉協調發展機制,建立起具有廣西特色的失獨老人社會保障一元體系。然需明確,本文所論城鄉一體化發展并非城鄉失獨老人社會保障的全面一體化,而是老年群體享受服務的一體化,即基于廣西北部灣城市群及西江經濟帶的頂層規劃,實現城鄉失獨老人在社會服務享有上的配比均衡,適應城鄉失獨老人不同養老層次需求的一體化。
(一)經濟扶助:破除地區發展壁壘,置配價值趨等化服務
廣西統一的失獨扶助金標準在形式上加快了城鄉失獨老人保障水平的趨同化,但由城市和農村人均消費等各項指標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可知(表4),城鄉物價水平、生活成本等具有較大差異,因此同等扶助金標準于城鄉失獨群體的實質價值難以衡量。

表4 2019年城市和農村人均消費各項指標占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
同時,參照上述扶助金在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城鎮失獨老人享受的救助保障水平遠低于農村失獨老人,即統一的經濟救助標準無法讓城鎮失獨老人和農村失獨老人享有基本一致的保障服務,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同一群體、同一制度的新矛盾。基于此,政府可參考江蘇省城鄉低保的自然增長機制,在建立扶助金和物價水平聯動機制的同時,應讓城鄉失獨老人能夠購買與價值基本趨同的商品和服務。
(二)精神慰藉:借力環境文化交互,重構社會精神支持網
農村失獨老人與周圍社會的強聯系性實質上是一把雙刃劍,即除了給農村失獨老人二次施壓外,還可以起到“助人自助”的作用。相較城市環境的獨立性,更利于互助養老模式的形成——在自由居家養老的同時,與村民結成共同生活體,少隔閡、少摩擦、易親近,且給統一社會服務的開展提供了便利。由此,城鄉失獨老人的社會交互可借鑒農村互助文化環境,構建共同價值文化圈。
(三)保險供給:溯源保險實質覆蓋,引進階梯式過渡體系
從社會安全網看,農村失獨者同其他非獨農民一樣缺乏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持。其一,城鄉二元化的經濟結構模式導致了城鄉社會保障的不均等化。在我國長期的工業化建設歷程中,城市憑借優質資源的后備支撐,圍繞城市居民所需,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而農村地區受經濟發展的制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尚處在較低層次的發展階段。其二,地域發展程度各異導致城鄉社會保障資源分配不均。由于城市往往處于現代化和工業化建設的中心,發展較快,人口眾多,為了更大程度地利用地理資源、發揮地域資源優勢,政府在資金、醫療條件、基礎設施等投入上會對城市有所傾斜。相比之下,農村所處地理位置相對偏僻,資源的共存共享具有實質難度。
由此,文章提倡借鑒上海浦東在城鄉保險階梯性發展的先進經驗,運用分層級的服務發展體系,在廣西按照國民生產總值的排位層級劃分經濟發達區與欠發達區,并基于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適配相應的保險供給服務體系——在經濟發達區實行由農村向城市模式的過渡,在經濟欠發達區則對失獨老人按照不同的養老保障需求實行層級劃分。一方面經濟發達區擁有相對充足的財力水平支撐農村建設,以跨越城鄉發展間的物質鴻溝,同時也符合了國家對于農村人口向城市過渡的規劃要求。另一方面經濟欠發達區在資源分配上處于劣勢地位,對該地區的城鄉失獨老人實行分層級的保險供給服務標準更有利于資源的優化與置換。
五、結語
現實中,廣西城鄉失獨老人的比重不容忽視,自身排外與社會排斥致使其難以邁出精神失獨的泥潭。且由于發展的不均衡性,區內城鄉失獨老人即便在經濟補助層面有較為可觀的預期,但就整體而言,體系化的社會保障仍處于低水平發展階段。
實際上,任何公共政策的執行都存在著變異性,如何尋找與區域發展相適配的著力點是關鍵。而在失獨老人的家庭時代斷裂、子女代際支持缺失的情況下,只有政府和社會攜手建立起牢固的制度性保障體系,才能使得這一特殊群體不再深陷于“失獨”又“失助”的悲慘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