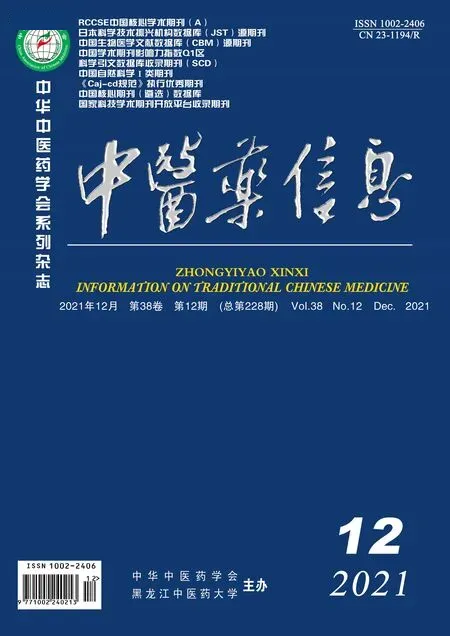藏藥二十五味兒茶凝膠對慢性濕疹模型大鼠血清中CCL17及CCL18表達的影響
費曉影,王思農,王亞紅,李丹
(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濕疹又稱特應性皮炎,是一種復雜的慢性皮膚病,兒童患病率高達30%,通常會持續到成年期[1]。有研究發現濕疹屬于基因性疾病,遺傳因素是構成濕疹發病的重要原因,加之皮膚屏障破壞、功能受損導致變應原侵入和細菌定植[2],引發皮膚異常的免疫反應和炎癥。慢性濕疹主要是以Th2為主的異常免疫反應、調節性T細胞功能障礙、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IgE)過度產生和嗜酸粒細胞增高等[3],從而導致器官的變態反應炎癥,一般伴有持續的瘙癢和皮膚組織的炎癥反應,如慢性濕疹皮膚樣變。有實驗研究發現,IgE介導的慢性濕疹的發病和全病程均有趨化因子CCL17、CCL18 參與。本研究主要基于血清趨化因子CCL17和CCL18研究探討藏藥二十五味兒茶凝膠方對慢性濕疹模型大鼠的影響,從而明確其治療慢性濕疹的作用機制。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動物
SPF級SD大鼠60只,雌雄各半,體質量(200±20)g,由甘肅中醫藥大學實驗動物中心提供。實驗動物許可證號:SCXK(甘)2015-001。在SPF級實驗動物中心統一飼養環境的標準要求下進行喂養,適應環境后開始實驗。
1.2 主要試劑及藥物
青鵬軟膏(西藏奇正藏藥股份有限公司,批號:2011271);醫用白凡士林(山東利爾康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批號:201203);2,4-二硝基氯苯(DNCB,上海中秦化學試劑有限公司,批號:150409);丙酮(上海久德化學試劑有限公司,批號:140916);CCL17、CCL18 ELISA試劑盒(上海信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 動物分組及造模
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60 只大鼠隨機分為空白組、模型組、陽性藥物組(對照組)、藏藥二十五味兒茶凝膠低劑量組(低劑量組)、藏藥二十五味兒茶凝膠中劑量組(中劑量組)和藏藥二十五味兒茶凝膠高劑量組(高劑量組),每組10 只。除空白組外,其余各組大鼠以致敏物質DNCB 反復多次激發,按照文獻[4]制備濕疹動物模型。大鼠在實驗前1日于背部取3 cm×3 cm的面積進行脫毛處理,次日脫毛區外涂5%DNCB 50 μL進行第1 次致敏。2 周后剪毛區再次去毛,次日外涂1%DNCB 100 μL,進行第2次致敏。此后繼續致敏,每周1次,連續4周。第4周致敏結束3 d后觀察各組實驗大鼠背部的皮膚狀態,出現紅斑、丘疹、水腫、抓痕、脫屑,即為造模成功。隨后各組開始治療干預。
1.4 給藥治療
根據大鼠背部面積與人臉面積之間外用藥物劑量等效換算公式計算給藥劑量。對照組大鼠涂抹青鵬軟膏0.02 g/(cm2·d),模型組大鼠涂抹凡士林0.02 g/(cm2·d),高、中、低劑量組分 別 涂抹0.01、0.005、0.002 5 g/(cm2·d)劑量的藏藥二十五味兒茶凝膠,空白組不予處理。每日給藥1次,連續給藥10 d。
1.5 評價指標
1.5.1 大鼠背部濕疹皮損程度評分
各組大鼠于末次給藥24 h 后,按照濕疹皮損程度評分標準進行皮損程度計分[4]。見表1。

表1 濕疹皮損程度評分
1.5.2 大鼠血清趨化因子CCL17和CCL18水平
根據試劑盒要求,采用ELISA 法檢測各組大鼠血清中趨化因子CCL17 和CCL18 水平。檢測過程嚴格按照說明書進行操作。
1.6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4.0 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多組間數據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以P<0.05 代表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各組大鼠背部組織皮損程度及評分比較
與空白組大鼠相比,模型組大鼠背部皮膚糜爛、紅斑、水腫、滲出、角化結痂等皮損程度明顯,皮損程度評分增加(P<0.05);與模型組相比,低、中、高劑量組大鼠背部皮膚糜爛、紅斑、水腫等癥狀普遍減輕或消失不見,角化、滲出等現象普遍減輕,皮損程度評分降低(P<0.05);低、中、高劑量組治療效果呈劑量依賴性;與對照組相比,高劑量組皮損程度及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各組大鼠背部濕疹皮損程度評分結果比較(±s)

表2 各組大鼠背部濕疹皮損程度評分結果比較(±s)
注:與空白組相比,*P < 0.05;與模型組相比,#P < 0.05;與低劑量組相比,@P<0.05;與中劑量組相比,&P<0.05。
組別空白組模型組對照組低劑量組中劑量組高劑量組n 10 10 10 10 10 10劑量[g/(cm2·d)]0.02 0.02 0.02 0.002 5 0.005 0.01皮損程度評分(分)0 4.81±0.17*1.92±0.33*#@&3.80±0.28*#3.20±0.29*#@1.93±0.27*#@&
2.2 各組大鼠血清趨化因子CCL17、CCL18表達比較
與空白組相比,模型組大鼠血清中CCL17、CCL18水平明顯升高(P< 0.05);與模型組相比,各治療組CCL17、CCL18 水平均下降(P< 0.05);低、中、高劑量組對CCL17、CCL18 的影響呈劑量依賴性;與對照組相比,高劑量組大鼠血清CCL17、CCL18 含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各組大鼠血清中CCL17,CCL18的表達水平(±s,pg/mL)

表3 各組大鼠血清中CCL17,CCL18的表達水平(±s,pg/mL)
注:與空白組相比,*P < 0.05;與模型組相比,#P < 0.05;與低劑量組相比,@P<0.05;與中劑量組相比,&P<0.05。
組別空白組模型組對照組低劑量組中劑量組高劑量組n 10 10 10 10 10 10 CCL17 89.5±4.8 157.6±7.9*110.6±6.2*#@&144.9±13.9*#125.5±5.5*#109.9±5.4*#@&CCL18 152.6±7.1 207.6±6.7*158.1±6.8*#@&193.1±7.0*#185.5±6.0*#157.1±6.9*#@&
3 討論
濕疹在中醫學中有“濕瘡”“濕癬”之稱,中醫學認為慢性濕疹發于肌膚,病在脾胃,主要由于稟賦不耐,飲食失節,或貪嗜辛辣刺激等發物,以致脾胃運化失司,濕熱內生,又感風濕或暑濕等外邪,內外之邪搏結于肌膚而發病;或因肝氣郁結,腎陽不足致水濕泛溢肌膚而發病。本病以外感六淫之邪為標,其本為五臟虛損,分為濕熱蘊膚、脾虛濕蘊、血虛風燥三型,臨床多以清熱利濕止癢為主要治法。本方為甘肅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院內試生產階段的院內制劑,藏藥二十五味兒茶膏最早記載于《四部醫典》,其組方主要包括乳香、紅花、兒茶、余甘子、毛訶子、訶子、肉豆蔻、木香、豆蔻、蓽茇、黃精、天冬、甘肅棘豆、黃葵子、決明子、安息香、麝香、水牛角、秦艽花、蒺藜、藏菖蒲、寬筋藤、鐵棒錘、珍珠母、西藏棱子芹等[5]。上述諸藥相和能夠健脾利濕、清熱祛風、潤膚養血,加之藏醫學理論認為,黃水由水谷入于脾胃而形成,人體功能異常失衡時就會形成“黃水證”,而本方也具有干黃水、消腫毒的作用,因此藏醫用其治療濕疹、滲出性皮膚病、黃水病等。藏藥二十五味兒茶凝膠是導師在原方的基礎上加減藥味、改良劑型,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傳統工藝制成。其中乳香消腫生肌,治療癰腫瘡瘍;紅花活血通脈以化瘀消斑;兒茶止血生肌、收濕斂瘡,治療濕疹、濕瘡;余甘子、訶子、毛訶子配伍使用,是藏藥方中常見的基礎方,稱為藏藥大三果,具有清熱、調和氣血、化解壞血的功效;木香、肉豆蔻行氣止痛;豆蔻、蓽茇化濕;天冬、黃精養陰潤燥;安息香、人工麝香行氣活血、消腫止痛;蒺藜、秦艽花祛風濕、清濕熱,活血止癢,治療皮膚瘙癢;珍珠母解毒生肌、潤膚祛斑從而促進創面愈合;西藏棱子芹是傳統常用的藏藥材資源,能愈合瘡傷。且凝膠劑作為一種新型制劑,具有親和性好、滲透性高、局部見效快、藥物經皮吸收快、透氣性好的特點,并可長時間作用于患處,發揮藥物作用。
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乳香中含有乳香酸類物 質acetyl-l1-keto-β-boswellicacid(AKBA),AKBA 能夠調節由產生干擾素γ 的CD4+T(Th1)細胞和IL-17 產生的CD4+T(Th17)細胞介導的自身免疫性疾病[6],可以通過影響炎癥因子以及細胞分子達到抗炎免疫的作用。紅花中的紅花多糖具有免疫調節活性,可通過TLR4 激活NF-κB 信號通路并誘導巨噬細胞產生各種炎癥因子(IL-1,IL-6,IL-12 和IFN-γ),參與炎癥反應[7]。此外,紅花黃色素能夠降低黑色素,作為皮膚美白劑。實驗研究發現豆蔻中的有效成分2-羥基-3-甲氧基苯甲酸對于活動性全身過敏反應,以及由IgE 介導的被動皮膚過敏反應具有預防和保護作用;此外豆蔻中的1,2,4,5-四甲氧基苯能抑制Th2 細胞因子在組織中的表達,還能改善由粉塵螨誘導的過敏性炎癥,其機制是通過抑制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表達,降低血清組胺、炎癥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的組織滲透[8]。大三果的藥理活性豐富,具有抗氧化、抗炎、調節免疫、愈合創面等功效,其醇提取物能抑制脂多糖誘導的巨噬細胞炎癥,減輕小鼠特應性皮炎的臨床癥狀,其機制可能與降低促炎癥因子釋放及減弱過度激活的免疫功能有關[9-10]。麝香的主要活性物質麝香酮,化學名為3-甲基環十五烷酮,臨床療效與天然麝香基本一致,可作為麝香的替代用品抑制炎癥反應[11]。安息香可通過降低炎性介質LDH、TNF-α 及IL-8 的活性,從而修復、改善內皮細胞損傷,同時還可抑制炎癥相關細胞因子(IL-1β、IL-6 和TNF-α)的表達[12]。藏菖蒲的水提取物可通過多重機制抑制由人體皮膚永生化角質細胞產生的促炎細胞因子IL-6和IL-8 形成,從而發揮抗炎作用,并有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有效的皮膚抗炎藥;同時,菖蒲根中提取出的多糖能刺激M1 極化巨噬細胞和促進小鼠體內的Th1 免疫反應[13]。秦艽、黃精、甘肅棘豆、決明子、寬筋藤均具有抗炎和免疫調節作用,黃精的主要活性成分黃精多糖、黃精皂苷,能夠調節炎癥信號通路;寬筋藤能抑制毛細血管的通透性、降低炎性因子的滲出率[14-18]。
目前慢性濕疹的病因病機尚未完全明確,有實驗發現遺傳因素、環境因素以及免疫功能異常相互作用導致了濕疹的發生[19]。慢性濕疹是由T 淋巴細胞浸潤為主的炎癥性疾病,而各種趨化因子參與調節和完成了疾病發病機制中T 細胞的遷移和招募的關鍵過程。CC 趨化因子功能包括趨化、免疫、遷移、炎癥反應以及誘導組胺釋放參與過敏反應等[20],在慢性濕疹的發生、發展過程中有重要作用。CCL17被稱為胸腺和激活調節趨化因子,其生物學的功能豐富,能夠參與到機體的炎癥、超敏反應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種病理生理過程,CCR4 作為CCL17 的受體,其募集的Th2 細胞可以誘導CCR4 配體在一個正反饋回路中進一步表達,從而增強過敏性炎癥。并且Th2 細胞可以通過IL-4、IL-5 和IL-13 促進炎癥的發作,CCL17 誘導Th2 細胞在趨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21]。因此,CCL17 被認為是濕疹發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趨化因子,是反映濕疹疾病活動性可靠的生物標志物之一[22]。CCL18 由Th2 型有關的細胞因子IL-4、IL-13 和IL-10誘導產生[23],CCR8 作為CCL18 的受體高表達于Th2 淋巴細胞上,CCR8 能夠招募Th2 型細胞趨化因子在慢性濕疹中的高度表達。研究顯示CCL18 通過自分泌或旁分泌的方式作用于單核細胞、巨噬細胞和T 細胞等參與機體的免疫和炎癥過程,CCL18 可以作為一種結構性的產物誘導趨化因子或吸引淋巴細胞、未成熟樹突狀細胞,使Th1 和Th2 均可參與細胞介導的免疫反應,特別是耐受性免疫應答,如對抗感染、促使傷口愈合或是平衡過度免疫應答等[24],據此表明CCL18 在慢性濕疹的發病機制及免疫調節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通過ELISA 法檢測各組大鼠血清CCL17、CCL18 的表達,進一步驗證了血清CCL17 及CCL18 參與、影響慢性濕疹的發病及預后,其血清水平與病情的程度聯系密切。由此結果可知,藏藥二十五味兒茶凝膠對下調血清CCL17 和CCL18 表達有重要作用,這可能是本方治療慢性濕疹的機制之一。同時本研究也可證實,血清中CCL17 和CCL18 的表達是治療慢性濕疹的又一靶點,值得在基礎研究和臨床治療中予以一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