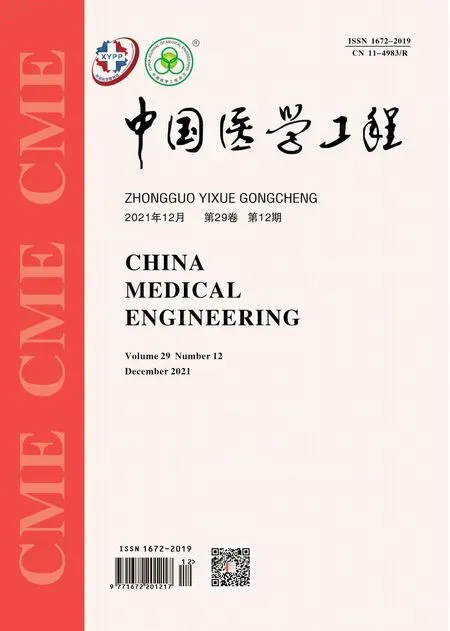血清IL-37、MMP-8水平與結直腸癌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相關性分析
魏慧娜
(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消化內科,河南 鄭州 450015)
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CRC)作為消化系統常見的惡性腫瘤,發病率與病死率僅次于胃癌、食管癌及肝癌,且流行病學調查顯示,近年來CRC 發生率逐年升高[1]。CRC 患者因腫瘤局限在腸壁,多數預后較好,但部分CRC 患者就診時腫瘤已浸潤至腸外,有較高的預后不良風險。據報道,TNM 分期、淋巴結轉移等與CRC 患者的預后息息相關[2]。因此,積極探尋與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相關的指標尤為必要。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是臨床評估CRC患者病理特征及預后的常用標志物,具有較高敏感性,但有研究指出,CEA 容易受到炎癥或其他指標影響,其穩定性不佳、應用有限[3]。
研究發現,CRC 的發展與免疫平衡紊亂有關,其中促炎-抑炎因子失衡可能會促進腫瘤細胞生長、轉移等[4]。白細胞介素-37(interleukin-37,IL-37)是抗炎家族新成員。研究指出,該因子具有阻滯腫瘤細胞增殖、抑制新血管生成等作用[5]。基質金屬蛋白酶-8(matrix metalloproteinase-8,MMP-8)是一種細胞降解基質,可降解多種細胞外基質,損傷腫瘤細胞侵襲組織屏障,促進腫瘤侵襲[6]。IL-37、MMP-8 可能與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有關,但目前相關研究較少。本研究通過觀察CRC 患者血清IL-37、MMP-8 表達,旨在分析患者血清IL-37、MMP-8 表達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 年7 月至2020 年4 月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收治93 例CRC 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性57 例,女性36 例;年齡41~67 歲,平均(54.36±3.34)歲;腫瘤位置:直腸45 例,乙狀結腸26 例,盲腸17 例,其他5 例。納入標準:①CRC 符合《中國結直腸癌診療規范(2017 年版)》[7]中相關診斷標準,且經腸鏡活檢組織學病理檢查確診;②均首次接受治療;③均接受手術為主的綜合治療方案,且患者預計生存期≥3 個月;④精神正常,可配合研究。排除標準:①合并胃癌、肝癌等其他惡性腫瘤;②合并心肌炎、腎衰竭等重要臟器疾病;③合并感染性肺炎、乙型肝炎等感染性疾病;④既往有放化療治療史;⑤合并免疫系統疾病。本研究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及其家屬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臨床病理特征評估方法 結合影像學檢查、活檢組織學病理檢查等結果評估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特征包括腫瘤直徑(>5 cm、≤5 cm)、TNM 分期[8](Ⅰ~Ⅱ期、Ⅲ~Ⅳ期)、腫瘤分化程度[9](高分化、低分化)、淋巴結轉移[10][經CT、MRI 等影像學檢查提示可見區域淋巴結腫大(單個淋巴結短徑≥8 mm 或有≥3 個直徑<8 mm 淋巴結聚集)]等。
1.2.2 血清IL-37、MMP-8 水平檢測方法 于患者入院第2 天取其空腹肘部靜脈血5 mL,采用低速離心機(廣州吉迪儀器有限公司,型號:JIDI-18RH)以4 000 r/min 轉速離心10 min。采集血清用酶聯免疫吸附實驗法測定IL-37、MMP-8 水平,檢測試劑盒購自上海晶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檢驗流程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進行。
1.3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SPSS 23.0 統計軟件。全部計量資料均經Shapiro-Wilk 正態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兩組間比較用獨立樣本t檢驗,多組間比較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偏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四分位數間距[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用Mann-WhitneyU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繪制受試者工作曲線(ROC),并計算曲線下面積(AUC),以檢驗血清IL-37、MMP-8 預測CRC 患者不同臨床病理特征風險的價值:AUC 值>0.90 表示預測性能較高,0.71~0.90 表示有一定預測性能,0.50~0.70表示預測性能較差;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93 例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分析
93 例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見表1。

表1 93 例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分析
2.2 不同臨床病理特征CRC 患者血清IL-37、MMP-8 水平比較
TNM 分期Ⅲ~Ⅳ期、有淋巴結轉移CRC 患者血清IL-37 水平低于TNM 分期Ⅰ~Ⅱ期、無淋巴結轉移患者,而MMP-8 水平高于TNM 分期Ⅰ~Ⅱ期、無淋巴結轉移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他不同臨床病理特征CRC 患者IL-37、MMP-8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表3。

表2 不同臨床病理特征CRC 患者血清IL-37 水平比較

表3 不同臨床病理特征CRC 患者血清MMP-8水平比較
2.3 血清IL-37、MMP-8 預測CRC 患者TNM 高分期風險價值分析
繪制ROC 曲線(見圖1)發現,當血清IL-37、MMP-8 Cut-off 值分別取43.385 pg/mL、70.255 ng/mL時,兩者單一及聯合預測CRC 患者TNM 高分期風險的AUC 分別為0.865、0.871、0.935,均有一定預測價值。見表4。

表4 血清IL-37、MMP-8 預測CRC 患者TNM 高分期風險價值分析參數

圖1 血清IL-37、MMP-8 預測CRC 患者TNM 高分期風險的ROC 曲線
2.4 血清IL-37、MMP-8 預測CRC 患者淋巴結轉移風險價值分析
繪制ROC 曲線(見圖2)發現,當血清IL-37、MMP-8 Cut-off 值分別取40.750 pg/mL、71.265 ng/mL時,兩者單一及聯合預測CRC 患者淋巴結轉移風險的AUC 分別為0.854、0.792、0.929,均有一定預測價值。見表5。

圖2 血清IL-37、MMP-8 預測CRC 患者淋巴結轉移風險的ROC 曲線

表5 血清IL-37、MMP-8 預測CRC 患者淋巴結轉移風險價值分析參數
3 討論
目前CRC 的篩查與治療雖有一定進步,但患者5 年生存率仍較低,且約有36%晚期CRC 患者經治療后5 年內可能出現復發,預后情況并不理想[11]。相關研究顯示,TNM 分期、腫瘤浸潤深度等均是CRC 患者預后的影響因素[12]。因此明確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對指導臨床干預尤為必要。
既往臨床評估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多依賴病理組織學檢查、影像學檢查等,該類方式雖可明確患者病變情況、指導臨床干預,但無法預測TNM 高分期、淋巴結轉移等風險,應用存有局限[13]。隨著細胞分子學的發展,研究顯示,多種血清指標與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均存在一定關系,可為臨床早期干預提供參考[14]。IL-37 是白細胞介素-1 抗炎家族一員,具有抑制炎癥介質生成作用,研究指出,IL-37 表達情況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15]。相關研究表明,IL-37 可抑制腫瘤細胞增殖,遏制腫瘤進展[16]。另有報道顯示,IL-37 與肺癌患者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微血管密度有關,且其IL-37 可抑制肺癌A549 細胞生長,阻止上皮細胞間質轉化,且可阻滯新血管生成[17]。結合上述研究發現,IL-37 抑制腫瘤細胞增殖機制,推測IL-37 可能與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有一定關系。本研究結果顯示,TNM 分期Ⅲ~Ⅳ期、有淋巴結轉移CRC 患者血清IL-37 水平低于TNM分期Ⅰ~Ⅱ期、無淋巴結轉移患者,初步說明IL-37表達降低提示CRC 患者TNM 分期高分期、淋巴結轉移高風險;進一步繪制ROC 曲線發現,IL-37預測CRC 患者TNM 分期高分期、淋巴結轉移風險均有理想的價值。當IL-37 Cut-off 值分別取43.385、40.750 pg/mL,可獲得最佳預測價值,且隨著IL-37 水平降低,TNM 分期高分期、淋巴結轉移風險增加。分析原因在于CRC 患者血清IL-37表達降低減弱對腫瘤細胞增殖、新血管生成有抑制作用,且可能會影響白細胞介素-6/信號轉導和轉錄激活因子3(STAT3)炎癥信號通路,從而促進炎癥因子釋放,推進疾病進展[18]。
MMP 是Zn2+依賴性蛋白酶家族的一員,具有降解細胞外基質作用,研究發現,MMP 表達與卵巢癌、胃癌等多種惡性腫瘤的發生均有關,且MMP 調控血管生成可能對腫瘤細胞新血管生成有促進作用[19]。MMP-8 是MMP 家族的一員,細胞降解作用與MMP 家族成員基本相同,劉小野等[20]研究顯示,MMP-8 表達顯著高于對照組,且MMP-8表達增加可能會增加腫瘤轉移風險。結合上述研究猜測,MMP-8 表達可能與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存在一定關系。本研究結果顯示,TNM 分期Ⅲ~Ⅳ期、有淋巴結轉移CRC 患者血清MMP-8 水平高于TNM 分期Ⅰ~Ⅱ期、無淋巴結轉移患者,初步說明MMP-8 與CRC 患者臨床病理特征有關;進一步繪制ROC 曲線發現,MMP-8 預測CRC 患者TNM 分期高分期、淋巴結轉移風險均有理想的價值,當MMP-8 Cut-off 值分別取70.255、71.265 ng/mL時,可獲得最佳預測價值,且隨著MMP-8 水平升高,TNM 分期高分期、淋巴結轉移風險增加。分析原因在于在腫瘤細胞侵襲過程中,MMP-8 表達增加可能會降解細胞基質屏障,促進腫瘤細胞入侵淋巴管,導致腫瘤出現淋巴結轉移;同時可能會造成腫瘤進一步浸潤,推進疾病進展[21]。此外有研究指出,腫瘤分化程度也是CRC 患者預后的獨立影響因素[22],但本研究發現低分化、高分化患者血清IL-37、MMP-8 表達比較無差異,這一結果可能與研究納入樣本量少、腫瘤低分化率低有關,因而未來需要進一步增加樣本量進行研究加以驗證。
綜上所述,CRC 患者TNM 高分期、淋巴結轉移可能與血清IL-37 低表達、MMP-8 過表達有關,考慮未來可檢測患者入院時血清IL-37、MMP-8 水平,輔助評估TNM 高分期及淋巴結轉移風險,可能對臨床擬定的治療方案具有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