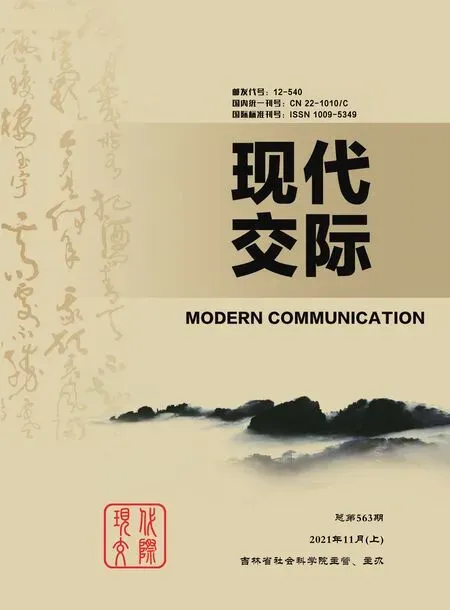社交拒絕、拒絕敏感性與人際關系滿意度的關系
于思佳 張 野
(沈陽師范大學 遼寧 沈陽 110034)
大學生會面臨與同學、教師、伴侶等多種人際關系,任何一種關系出現問題,都會影響其正常生活。人際關系滿意度逐漸成為衡量大學生生活質量好壞的重要指標。人際關系滿意度(interpersonal satisfaction)是指個體與他人之間的關系按照自己的標準進行綜合評價。[1]研究大學生人際關系滿意度有利于對自身的學習及價值觀形成積極的評價。[2]因此,了解人際關系滿意度的產生機制對改善大學生的身心健康具有積極意義。
一、研究現狀
社交拒絕(social rejection)是指個體的歸屬需要遭受了他人拒絕的情境。社交拒絕對個體而言是極為重要的威脅性刺激。
金童林等人研究發現,社交拒絕會導致各種不良的心理問題,使個體的人際交往很難得到良性發展。[3]
Maner等人發現,如果人們繼續與拒絕過他們的人交往,會增加將來再被拒絕的風險,也就是說,對社交拒絕的反應是遠離他人,以至不愿意與人交往。[4]
目前,許多大學生存在不良人際關系現象,諸如社交拒絕、人際隔離等都會影響其身心健康發展,降低人際關系滿意度。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社交拒絕能夠顯著負向預測大學生的人際關系滿意度。
那些在人際交往過程中被拒絕的大學生在意識到被他人拒絕后,不想去接觸更多的人,會產生更多的焦慮情緒。拒絕敏感性(rejection sensitivity)是指被他人拒絕后而產生的焦慮性預期及過度反應。研究表明,社交拒絕會影響其對拒絕的歸因解釋,個體在感知社交拒絕時,對自己和他人的評價及對拒絕事件的歸因和應對方式都會有所改變。例如,當人際關系需要得不到滿足或個體遭受他人拒絕時,有的人會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通過不斷提升自己得到他人接納,滿足安全的需要;而有的人采取消極的應對方式和行為反應,在人際交往時表現出較高水平的拒絕敏感性。由此可推測,當遭受社交拒絕或社交過程中出現拒絕水平更高時,個體的拒絕敏感性更高。
此外,當個體沒有得到積極關注或遭遇拒絕等威脅性行為時,其歸屬需要沒得到滿足,那么他們在以后的社會交往中便會出現更多的拒絕行為,從而導致人際關系滿意度降低。
Eck等人認為,如果個體在童年期很大程度上被別人排斥或拒絕,那么他也會選擇遠離別人。[5]
還有研究發現,高拒絕敏感性者的拒絕期望是伴隨著負面情緒增加的,這些負面情緒增加了不良的人際行為反應。[6]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拒絕敏感性在社交拒絕與人際關系滿意度之間具有中介作用。
綜上,本研究建立一個中介模型(見圖1),探明上述問題有助于揭示社交拒絕、拒絕敏感性對大學生人際關系滿意度的作用機制,為有效提升大學生人際關系滿意度,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和數據支持。

圖1 社交拒絕影響大學生人際關系滿意度假設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被試
采用整群抽樣法進行問卷調查,選取遼寧省某高校的大學生為施測對象,共發放問卷300份。問卷回收后,剔除回答不完整的問卷,最終獲得有效問卷240份,有效率為80%。其中男生115名(47.9%),女生125名(52.1%);大一15名(6.3%),大二30名(12.5%),大三37名(15.4%),大四80名(33.3%),研究生78名(32.5%)。
(二)測量工具
1.人際關系滿意度量表[7]
采用陳小華修訂的人際關系滿意度量表,該量表包含36個項目,由交際屏障、互利支持、外向干練、相似相容、差異沖突和道德素質六個維度組成。采用5點記分方式,總分越高表明被試的人際關系滿意度越強。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0.84。
2.社交拒絕量表[8]
采用汪向東等人修訂的社交回避量表。量表共28個項目,本研究選用量表的14個評價回避行為傾向的項目,采用5點記分方式,得分越高,說明社交回避行為的傾向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0.84。
3.拒絕敏感性量表[9]
采用Jobe編制、李霞修訂的大學生拒絕敏感性量表。該量表為單一維度,共含18個項目,采用5點記分方式,得分越高,說明被試的拒絕敏感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0.86。
三、結果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10]單因素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顯示,一共有11個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并且第一個因子能解釋25.07%的變異量,低于40%的臨界值,說明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變量間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表1為各研究變量的平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矩陣。結果表明,性別、年級變量與研究的三個核心變量的相關均不顯著。第一,社交拒絕與人際關系滿意度(r=-0.16,p<0.05)呈顯著負相關,與拒絕敏感性(r=0.16,p<0.01)呈顯著正相關;第二,拒絕敏感性與人際關系滿意度(r=-0.33,p<0.01)呈顯著負相關。

表1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及變量間的相關分析結果(n=240)
(三)拒絕敏感性的中介作用
從表2可見,在方程1中,社交拒絕的回歸系數顯著(β=-0.16,t=-2.47,p<0.05),說明社交拒絕顯著負向影響人際關系滿意度;在方程2中,社交拒絕的回歸系數顯著(β=0.16,t=2.55,p<0.01),說明社交拒絕正向影響拒絕敏感性;在方程3中,拒絕敏感性的回歸系數顯著(β=-0.31,t=-5.08,p<0.05)說明拒絕敏感性在社交拒絕與人際關系滿意度之間起中介作用。應用SPSS21.0的插件Process,通過Bootstrap法對中介效應進行驗證。中介效應的分析結果顯示(見表3):中介效應值為-0.02,95%CI為(-0.03,-0.01),不包含0,說明拒絕敏感性的間接效應顯著,占總效應的40%,占直接效應的66.7%;直接效應95%CI為(-0.07,0.01),說明社交拒絕對人際關系滿意度的直接效應不顯著,是完全中介效應。因此,以上假設均成立。

表2 社交拒絕與拒絕敏感性對人際關系滿意度的回歸分析

表3 拒絕敏感性在社交拒絕與人際關系滿意度之間的中介作用檢驗
四、討論
(一)結論1.社交拒絕對大學生人際關系滿意度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社交拒絕顯著負向預測人際關系滿意度,這與以往研究即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與其滿意度呈負向預測作用相符。可見,人際交往受到拒絕,大學生的人際關系滿意度會降低。另外,受到來自他人的拒絕時,其歸屬與愛的需要便受到威脅,社交拒絕會增強其害怕今后再被拒絕的焦慮甚至恐懼水平,使其出現社交退縮和孤獨等情感與行為,進而避免與拒絕過他的人接觸,從而降低其人際關系滿意度。
2.拒絕敏感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交拒絕對大學生的拒絕敏感性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究其原因,可能與個體早期不良同伴關系有一定聯系。拒絕敏感性理論模型指出,兒童在與他人交往過程中感知潛在的拒絕后,出現的消極情緒及回避反應會逐漸泛化到其他的社交情境中,從而使其更加敏感。個體遭受拒絕的經歷越多,對于拒絕的預期性焦慮也被強化,使其在今后的人際交往中變得更加敏感。上述消極情緒和反應會進一步強化他人的實際拒絕,從而驗證其先前對拒絕的預期。
本研究還發現,拒絕敏感性對大學生的人際關系滿意度有影響。此外,個體對于拒絕的敏感會逐漸形成自我防御機制,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不良行為,導致人際交往的失敗。即拒絕敏感性水平高的個體在人際交往中更害怕與他人交流互動,導致其人際關系滿意度下降。由此可見,長期遭受父母和同伴的拒絕,會強化大學生的拒絕敏感性,不利于其生活滿意度的提升。近年來,國內外的大量研究已經證明,拒絕敏感與個體不良的心理、人際功能有關,高拒絕敏感個體其人際關系質量更差。綜上,社交拒絕不僅直接影響大學生的人際關系滿意度,還通過拒絕敏感性對人際關系滿意度產生間接影響。
(二)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還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所有變量均采用自陳式的問卷形式進行測量,要想更準確地探究大學生人際關系影響機制,還應考慮從多主體角度收集數據。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的樣本數量較少,未來可以擴大取樣范圍并以改善其可推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