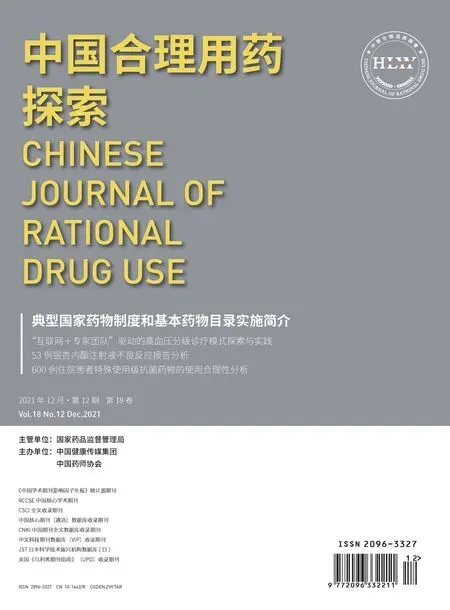典型國家藥物制度和基本藥物目錄實施簡介
王 莉,馮婉玉
(1 北京大學國際醫院藥劑科,北京 102206;2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藥劑科,北京 100044)
1 WHO基本藥物制度及目錄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通過其出版物支持全球國家的衛生戰略,并解決世界各地人口最迫切的公共衛生問題,從而實現WHO的主要目標——讓所有人都達到盡可能高的健康水平。
基本藥物(Essential Medicines)的概念最早由WHO于1975年提出,其目的是為臨床提供適應醫療需求、劑型適宜、價格合理、能保障供應、可公平獲得的藥物。第一版《WHO基本藥物示范目錄》于1977年頒布,又稱為WHO基本藥物目錄。這一目錄包括基本藥物清單(Model List of Essential Medicines)和兒童基本藥物清單(Model List of Essential Medicines for Children)。
《WHO基本藥物示范目錄》包含核心目錄(core list)和補充目錄(complementary list)。核心目錄列入的是最基本藥物的目錄,這些藥物最有效、最安全、成本效果最高。補充目錄列入的是需要優先診斷或監測的重要疾病基本藥物,可能成本較高。WHO在第一版《WHO基本藥物示范目錄》中明確了4項遴選原則:① 優先考慮可以盡可能廣泛地向公眾提供已證明有效和安全的藥物,滿足預防和治療最流行疾病的需要。② 應選擇可從對照研究中獲得足夠科學數據的藥物。③ 每一種選定的藥品必須達到適當的質量標準,包括必要時的生物利用度。④ 每一種基本藥物清單應附有從公正來源獲得的簡明、準確和全面的藥物信息[1]。《WHO基本藥物示范目錄》由基本藥物選擇和使用專家委員會每2年更新一次。遵循主動申請(依據藥品的可及性、藥物經濟學、安全性證據等信息提交遴選藥品申請書)、循證分級(采用國際統一的證據質量分級和推薦強度GRADE標準)、集體評審(邀請國際藥品采購便利機制、其他藥品消費者組織和衛生保健工業代表進行評論)、結果公示(所有評論意見在網上公示30天以上)的基本操作原則保障高透明度,使遴選結果能夠得到公眾的信服。
現行版《WHO基本藥物示范目錄》是WHO基本藥物選擇和使用專家委員會第23次會議于2021年6月21日至7月2日在瑞士日內瓦協調召開。委員會審議了88份新增、修訂和刪除藥物、藥物類別和藥物配方的申請,評估了有關藥物的有效性、安全性和成本效益的科學證據。委員會還審議了標準清單上藥物治療替代品的審查,更新了抗生素的AWaRe(Access,Watch and Reserve)分類,以及與基本藥物的選擇和使用相關的審查和報告[2]。2021年9月30日,WHO更新出版了第22版《WHO基本藥物示范目錄》和第8版《WHO兒童基本藥物示范目錄》[3-4],該目錄明確了基本藥物的定義和遴選標準。WHO提供在線版《WHO基本藥物示范目錄》,是一個全面的、可免費訪問的在線數據庫,其中包含有關基本藥物的詳細藥物信息以供公眾查詢。
回顧過往的40多年,基本藥物制度在WHO及其成員國和地區的共同努力下為全球衛生事業做出巨大貢獻。1975年,在第28屆世界衛生大會上,為了滿足人們基本醫療用藥需求,WHO總干事建議所有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根據國家衛生需要,制定基本藥物政策[5]。1977年,WHO基本藥物選擇和使用專家委員會在日內瓦舉行會議編撰第一版基本藥物清單,首次定義基本藥物為“對滿足公眾居民衛生保健而言的最重要、最基本、不可或缺的所有必需藥物”[6]。1985年,WHO在內羅畢會議上強調基本藥物除了致力于解決藥品短缺問題之外,還應重視合理使用,并推薦把基本藥物的遴選同處方集和標準治療指南的制定相結合。2002年,WHO重新定義基本藥物為“能滿足人類重點衛生保健需求的藥物,具有應當能隨時獲取足夠數量、適當劑型、質量有保證、具有充分信息且其價格能夠被個人和社會接受的特點”[7]。《WHO基本藥物示范目錄》是超過155個國家的國家政策基礎。許多政府在做出衛生支出決策時參考了WHO的建議。
2 典型國家藥物制度
基于實現藥物的可獲得性、可負擔性、質量保證和合理使用的目標,全球多國根據具體國情建立起基本藥物模式和制度,通過科學、系統的方法,遴選制定出國家處方集或基本藥物目錄。根據各國衛生保健系統的架構和經濟發展水平,制定基本藥物采購模式,發展中國家多采用規范化的政府采購。發達國家幾乎未建立專門的基本藥物制度,而是將基本藥物納入更為廣泛的藥品管理體系。發達國家傾向靈活度高的醫療機構采購或高效率的第三方采購模式,并且擁有更為完善的保險體系支持醫療系統。本文討論的典型國家總人口、衛生總支出占GDP百分比和人均預期壽命匯總情況見表1。

表1 典型國家總人口、衛生總支出占GDP百分比和人均預期壽命匯總
2.1 發展中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概況
印度的“德里模式”[8],以《WHO基本藥物示范目錄》為基礎,秉承安全、有效、充足、經濟和合理的藥物遴選原則,根據不同群體的健康需求和不同區域的疾病特點,德里州政府制定適宜的基本藥物目錄。基本藥物目錄內藥品的采購、存儲和供應由政府集中招標采購部門負責,采用“雙信封”招標模式以保證藥品質量和藥品價格。政府實施強制的行政監管,覆蓋從確保基本藥物生產供應,到限定醫院基本藥品的預算占比,再到控制基本藥物價格的各個環節。通過制定處方集、標準治療指南并強化培訓來促進合理用藥。最后,依托信息化傳播力度普及基本藥物制度,開展調研獲取基本藥物使用反饋,助力政府實施動態調整活動。
南非自1996年開始推行國家藥物政策[9]。參考WHO的基本藥物遴選標準,采用申請制,在審查過程中強調科學的證據及證據等級,制定標準治療指南和基本藥物目錄,使基本藥物的遴選模式日趨成熟。經中央公共采購系統進行價格談判,再由省級相關機構進行采購,政府免費為公立基層醫療機構提供基本藥物,大幅提高基本藥物的可獲得性。
泰國在1981年制定國家基本藥物目錄[10],2002年該目錄納入泰國醫療保險體系的報銷目錄。成立國家藥物體系發展委員會,負責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制定、藥物合理使用、藥物參考價格和藥物政策監測等工作。
津巴布韋自1986年起實施基本藥物制度[11]。其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含600余種藥物,劃分為5個層級,A類(最高級)藥物在國家及省級醫療機構使用,B類和C類藥物分別在區級和鄉村級醫療機構使用,另外設置特殊專用藥物和補充藥物。基本藥物目錄連同國家診療指南,指導醫務人員的臨床及護理工作。國家加強培訓和考核等舉措保障制度的執行。
2.2 發達國家藥物制度以及醫療保障概況
隨著企業兼并重組的興起,發達國家的藥品生產和流通企業的市場集中度日益增高,形成鮮明的大型企業壟斷型市場。
瑞典在1996年頒布基本藥物制度法律[12],是目前全球唯一建立基本藥物目錄的發達國家。該目錄包括200種用于初級保健及醫院診療的核心藥品和100種用于特殊診療的補充藥品。對基本藥物開展了長期跟蹤調查,為及時更新基本藥物目錄、提高藥物可及性以及合理用藥提供了有力的數據支撐。從2003年起,由省議會與藥商簽訂的“管理準入協議”能較好地兼顧政府、制藥企業和患者之間的利益,保證藥品療效的同時,也能控制成本增長、刺激市場競爭。
澳大利亞實施的是全民醫療保障制度[13]。制藥企業將已上市藥品的藥物經濟學評價報告遞交至一個完全獨立的非政府機構藥品利潤審查組織,通過該組織從經濟學角度對臨床效果與成本進行全面分析的藥品即可申請加入基本藥物報銷目錄。澳大利亞從1950年起實施的藥品福利計劃(Pharmaceutical Benefits Scheme,PBS)為公民提供藥品補貼。截至2009年7月,PBS已收錄2600種藥品。政府針對不同人群制定個人支付線,患者購買藥物時需先支付一定金額,超過的部分由PBS來支付[14]。
美國醫療保險市場發達,多數保險采用按病種標準費率付費,以達到推行標準化治療和降低成本的目的。因此,公立醫療衛生機構和保險公司都傾向優先使用普通藥品。以遵循循證、權衡風險收益和以患者為中心的三大原則,保障藥品目錄的準入制度。采用匯總藥物需求量并委托第三方組織進行采購的模式,美國藥品福利管理機構和團購組織是在醫藥企業、醫療機構和保險公司之間的第三方盈利性機構。該機構擁有大量信息資源,通過收集采購需求,整合購買力,進行買賣方議價,根據反饋信息決定最優采購方案[15]。美國的保險目錄采用等級管理制度,第一等級包括普通仿制藥,伴隨個人最低自付比例;第二等級包括受歡迎品牌藥,伴隨個人較高自付比例;第三等級包括其他專利藥,伴隨個人最高自付比例。
3 我國基本藥物制度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藥物政策與基本藥物制度司的主要職責是完善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組織擬訂國家藥物政策和基本藥物目錄。開展藥品使用監測、臨床綜合評價和短缺藥品預警。提出藥品價格政策和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內藥品生產鼓勵扶持政策的建議。我國通過基本藥物制度構建起全國藥物綜合管理體系,包括從基本藥物的遴選、生產、流通、使用、支付、監測等環節,通過推行宏觀政策和實施監督管理等手段確保公眾基本藥物的需求。
1979年,我國政府參與WHO基本藥物行動計劃,在原衛生部和原國家醫藥管理總局的組織下成立了國家基本藥物遴選小組,開始著手國家基本藥物的制定工作。1982年,我國首部《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問世,該目錄包含278個藥品,遴選主要以臨床必需為原則,保證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用藥需求。1992年,為配合公費醫療和醫療保障制度改革,我國成立國家基本藥物領導小組,組織領導國家基本藥物遴選和推行工作。2009年,九部門印發《關于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定義基本藥物是“適應基本醫療衛生需求,劑型適宜,價格合理,能夠保障供應,公眾可公平獲得的藥品”。參照國際經驗,合理確定我國基本藥物品種劑型和數量,在保持數量相對穩定的基礎上,《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實行動態調整管理,原則上每3年調整一次[16]。為進一步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原衛生部、國家衛生健康委于2009、2012、2018年每年遴選后發布一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國家基本藥物臨床應用指南》《國家基本藥物處方集》。我國最近3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品種數量及劑型規格情況匯總見表2。

表2 我國最近3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情況匯總
為貫徹落實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和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部署要求,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完善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意見》印發,從六大方面明確了改革方向:動態調整優化目錄,以適應基本醫療衛生需求和完善目錄調整管理機制;從提高有效供給能力、完善采購配送機制以及加強短缺預警應對三點出發切實保障生產供應;以加強配備使用管理、建立優先使用激勵機制和實施臨床使用監測保障基本藥物的全面配備優先使用;經逐步提高實際保障水平和探索降低患者負擔的有效方式下切實降低群眾藥費負擔;加強組織領導、督導評估和宣傳引導以營造基本藥物制度實施的良好氛圍。
2019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明確提出:國家實施基本藥物制度,遴選適當數量的基本藥物品種,滿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藥需求。國家公布基本藥物目錄,根據藥品臨床應用實踐、藥品標準變化、藥品新上市情況等,對基本藥物目錄進行動態調整。基本藥物按照規定優先納入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國家提高基本藥物的供給能力,強化基本藥物質量監管,確保基本藥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2021年11月15日發布的《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管理辦法(修訂草案)》中規定,基本藥物遴選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需、保障供應、優先使用、保證質量、降低負擔”的功能定位,堅持中西藥并重、臨床首選的原則,參照國際經驗合理確定。堅持定期評估、動態管理,調整周期原則上不超過3年。調整的品種和數量應當根據以下因素確定:① 我國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和基本醫療保障水平變化。② 我國疾病譜變化。③ 藥品不良反應監測評價。④ 藥品使用監測和臨床綜合評價。⑤ 已上市藥品循證醫學、藥物經濟學評價。⑥ 國家基本藥物工作委員會規定的其他情況[17]。
國家基本藥物制度除了落實公眾對基本藥物的需求之外,開始注重解決藥品高價問題,綜合降低醫療衛生費用。同時,逐步完善醫療機構處方點評制度,保障藥品的合理使用;力求在全國各省市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中落實基本藥物的使用,在二、三級醫療衛生機構中有序推進基本藥物的優先使用。
4 對我國基本藥物制度的建議
基本藥物制度強調醫療衛生資源全民覆蓋的普惠性,落實每個社會成員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平等權利,在政府監管下保障制度的合法性、強制性、公益性和可持續性。基本藥物制度的穩步實施,解決基本藥物的可獲得性,提高基本藥物的可負擔性,保障基本藥物的合理使用性,落實人民用藥安全。
4.1 基本藥物目錄遴選建議
我國基本藥物制度在目錄遴選過程中,應落實公示以促進組織及個人的監督,從而提升過程的透明度;同時充分發揮循證醫學、藥物經濟學等科學方法的優勢,以提高目錄遴選的科學性[18-19]。我國幅員遼闊,疾病譜呈現地域差異性,可以中央制定基本版目錄輔以地方特色版目錄方式,落實基本藥物的疾病覆蓋性和可及性需求。我國《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目前尚不能滿足兒童特殊人群的需要,應在適當參考國外兒童基本藥物目錄經驗情況下,逐步建立適用我國兒童專屬版基本藥物目錄[20-21]。
4.2 基本藥物市場供應建議
在藥品供應環節存在個別因原材料不足等原因導致藥品短缺和資源配置不均等問題,應加強短缺藥品全生命周期監管,建立供應保障體系,優化供應機制,及時高效解決短缺和配置問題。針對藥品價格攀升、居民醫療保險覆蓋有限等問題,應進一步縮減藥品流通環節,嚴控流通秩序,完善報銷目錄,并提升異地就醫、重大疾病等特殊情況的報銷比例等,同時也應遵循市場經濟原則合理制定基本藥物價格,形成企業獲得利益、患者獲得益處、行業獲得發展的良性循環[22]。完善政府補償機制,加大政府投入,加強制度實施中各環節的管理,保障基本藥物制度順利推進。
4.3 基本藥物臨床應用建議
早在第一版《WHO基本藥物示范目錄》的實施過程中,就發現臨床用藥不合理的情況,于是在1985年WHO就強調對基本藥物的合理使用。同樣,我國在藥品使用環節也同樣存在用藥錯誤及不合理用藥等問題,亟需規范藥品使用的監督管理,推進客觀嚴謹的遴選程序以促進基本藥物目錄與臨床實際需求的契合程度,加強對醫務工作人員的基本藥物制度宣貫和培訓等[23-24],使其真正落實到促進臨床合理用藥的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