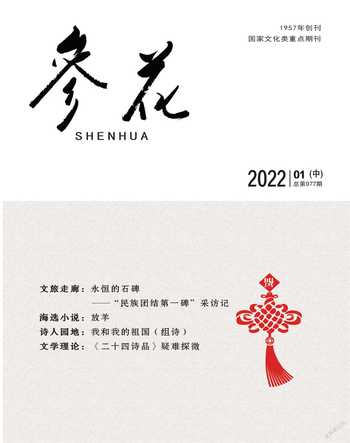《寒夜》和《圍城》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分析
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在20世紀文學作品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些形象跟隨時代環境的改變和作家審美的不同而不斷變化著,有理想型、批判型等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形象。
不同的文學創作環境產生了不同的文學作品和知識分子形象,例如,巴金的《寒夜》和錢鐘書的《圍城》,他們二人的作品基本寫于同一時間,都在《文藝復興》發表,他們所塑造的知識分子形象都帶有典型性,反映了知識分子在特殊時期的心理和形象的變化,描述了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本文從巴金的《寒夜》和錢鐘書的《圍城》兩部作品的知識分子形象出發,探究作品中知識分子形象塑造成因,分析《寒夜》《圍城》中知識分子形象的生存困境。
一、《寒夜》和《圍城》中的各類知識分子形象
(一)《寒夜》和《圍城》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剖析
20世紀40年代,由于外部環境的原因,知識分子本就艱難的理想更加難以實現,知識分子在堅守良心與社會責任時,生存就顯得尤為困難。《寒夜》中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為生活所迫、忙忙碌碌、只為尋求一方生存之地的形象。小說中的主人公汪文宣和妻子曾樹生在戰爭前,希望興辦教育,實現自己的理想,可所有的理想都被現實打破,他們一家四口只能蝸居在一個經常停電的小居室。汪文宣與妻子的結合,洋溢著當下知識分子所特有的激情,他們二人也曾像涓生、子君一樣,想做新時代出走的娜拉,但隨著曾樹生與家庭脫離聯系,二人的理想逐漸走向破滅,曾樹生成為汪文宣最后的寄托。汪文宣、曾樹生、老鐘等人,將所有希望寄托在抗戰的勝利上,他們渴望勝利,認為只要不再打仗,生活就能恢復如初,但老鐘死在勝利前,汪文宣也在勝利的當天夜晚去世,生活暫時還未發生他們預期的改變。曾樹生雖然在勝利后趕回了家中,可那個經常斷電的昏暗小屋已經失去了家人的存在,當曾樹生最終下定決心離開她與汪文宣的婚姻圍城時,就已經出了城再也回不到原來的圍城中。
雖然巴金沒有過多地描寫年輕時懷揣辦學育人夢的汪文宣,但從之后他對讀書的冷漠便可知汪文宣曾經的憧憬。汪文宣在生病時,給自己下過定義,“這個年頭……尤其是我們這些良心沒有喪盡的讀書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1]小說中,汪文宣只能通過老鄉的介紹,到一家小公司以校對翻譯為生,妻子則進了銀行工作,忙于交際。柏青、汪文宣和魏連殳、呂緯甫一樣,真正擊倒柏青的不僅是妻子的去世,還有自己曾經掙扎后的徹底失敗,真正打敗汪文宣的也不僅是妻子的離去和病魔的糾纏,而是努力過后的無路可走。當柏青和汪文宣心懷理想走入社會時,他們遇見了殘酷的外部環境,只能為生計奔波,在放棄理想后,汪文宣、柏青發現自己連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做不到,更何況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圍城》中的主人公方鴻漸家境優渥,父親是家鄉小縣城的紳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可以送他出國留學。方鴻漸在歐洲留學,輾轉三個大學和多門專業,從土木工程系到社會哲學系再到中國文學系,方鴻漸千里迢迢遠赴國外學習的,不是其他國家先進之學科,而是自己國家的語言文學。蘇文紈和方鴻漸一樣,在留學時期攻讀的是法國文學,但是,卻以《中國十八家白話詩人》獲得學位。在《圍城》中的部分知識分子眼中,留學就如同為自己履歷增光添彩的一件事情,因此,家境好的青年學生爭相外出留學,求學卻不是最終目的,是為了回國時能找個好工作。在劍橋攻讀文學的新詩人曹元朗在回國后,常將自己在劍橋留學的經歷掛在嘴邊,帶著自己不通順的詩到處結交朋友,并獲得了好名聲。方鴻漸在圍城中進進出出,從國外的圍城中留學歸來,便去了三閭大學工作,可是當方鴻漸被辭退后,看著來送別的學生,產生了雖厭惡這地方卻又心生留戀的心理變化,方鴻漸常常自我安慰,卻又不能真正與現實和解,找到自己的出路。相比于褚慎明、曹元朗這類自欺欺人型的知識分子形象,方鴻漸并非全無才華,他在面對蘇小姐和曹元朗作的詩時,能一針見血地指出蘇小姐的詩有哪些問題,但是,方鴻漸骨子里很懶,喜歡得過且過,雖然不滿現狀卻拿不出勇氣改變,是一個外表新、骨子里傳統的知識分子形象。方鴻漸渴望改變,可從小環境熏陶出的性格已經難以有根本上的改變,雖然他學習外語、哲學,又精通中國文化,但卻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找不到屬于自己的道路。
(二)《寒夜》與《圍城》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對比
《寒夜》中的汪文宣曾說過,只有自己這種沒有良心喪盡的讀書人活得最為痛苦,他的朋友柏青也有類似感嘆,其實,方鴻漸與汪文宣、柏青二人相同,仍舊保有初心卻沒有能力改變一切,而像褚慎明、劉東方、韓學愈這樣的知識分子,可以在當時的時代生活得很好。汪文宣在圖書公司做不到左右逢源,方鴻漸也不能很好地在三閭大學生存下去,可董斜川卻可以憑借幾首不通的同光體詩歌贏得尊重,高松年可以運行一個學校,韓學愈可以堂而皇之地教書。
相對于《圍城》,《寒夜》關注的是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他們是被現實打敗的。汪文宣、曾樹生之間的矛盾除了婆婆的影響外,金錢是避不開的現實問題,“生存”在汪文宣的小家里成為一個大問題。為了謀生,汪文宣不得不做校注工作,理想與愛情都排在生存之后,汪文宣已多年未進入咖啡店,舍不得給妻子買一塊奶油蛋糕,而方鴻漸卻可以思考是否買一件皮衣作為自己的行頭。巴金從汪文宣的生存困境來探究他精神上的茫然無助,從一對小夫妻的家庭生活探究戰爭背景下的現實,而現實最終蓋過最初的理想,與魯迅小說《傷逝》中的涓生、子君等知識分子形象有相似之處。
汪文宣在勝利前失去了生命,他在上海曾經擁有過的激情已經消失了。巴金在《寒夜》中所描寫的,是對國家、民族抱有希望的知識分子在戰爭背景下的生存狀況,體現的是對經歷現實無路可退的知識分子的關注,《寒夜》以對現實逼真的刻畫來傳遞當時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圍城》中,錢鐘書則借助方鴻漸的思想變化、心理活動來傳遞他自己對當時知識分子整體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錢鐘書在塑造知識分子形象時,更多是對大環境下知識分子放棄自己操守、理想的思考,用看似幽默化的寫作技巧書寫了“圍城”內外的故事,在一場看似喜劇的演出中揭示了人性的悲劇,體現了對喜劇背后更深層次的思考。在這里,不僅包含知識分子的命運,還有關于人類生存境遇的思考。
二、《寒夜》和《圍城》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塑造成因
(一)時代語境的影響
近現代以來出現的知識分子,他們受外部環境與西方文化的沖擊與影響,產生了與西方知識分子不同的特質,在新舊交替的時代語境中,承接古代士的社會責任、良心,“他們所關懷的不但是如何‘解釋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變世界。”[2]西方知識分子更看重個人的價值,而近代知識分子則更看重社會的價值,即自身的價值并不僅僅通過學術層面來體現,還通過社會價值來表現。這樣的知識分子形象也一直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例如,魯迅筆下的夏瑜、魏連殳、呂緯甫等知識分子形象,他們都受到革命的感召而投身于革命,追求自由、平等,以期求得民族解放。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戰爭打破了以往較為和平的環境,救亡的需求壓倒了啟蒙,不少知識分子陷入迷茫與自我懷疑的境地,同時,戰爭打破了他們的計劃和生活,讓他們陷入困頓的局面,本就艱難的理想更加難以實現。
《圍城》中的方鴻漸,迷茫到找不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一方面是因為時代環境,一方面是因為性格使然。方鴻漸出生在一個傳統家庭,從小接受傳統的中式教育,并且依賴父親,留學時期接觸的新式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這就造就了他的矛盾心理,即性格上猶豫不決、怯懦無能,整個人既新又舊。另一方面,方鴻漸處于一個特殊時期,他身邊的許多人并不是依靠自己的真才實學成功的,而是依靠投機取巧等方式來獲取金錢與地位的,例如,曹元朗以交流自己不通的詩文來獲得關注等。錢鐘書塑造方鴻漸,“不只是以揭露‘新儒林的弱點,或探求知識者的道路,而是企圖以寫‘新儒林來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反省。”[3]錢鐘書通過描寫方鴻漸在圍城中的不斷進出,來表現他自己對現實人生的思考。
《寒夜》中影響汪文宣悲慘命運的,有外部環境的影響因素,他無力去抗爭現實,但是,卻又不能放棄自己的良心與理想和其他謀求利益的人一起追逐名利。他只能帶著自己的良心、初心在困境中掙扎著,最終淹沒于時代的洪流,汪文宣曾經也反抗過,卻因為妥協與怯懦被現實打敗,放棄堅守的理想。他的妻子曾樹生想要脫離這樣的困境,卻又猶豫不決,離去了又歸來,也是困于良心、初心的掙扎。汪文宣與妻子曾樹生受到個性解放思想的影響,沖破一切束縛走出家門,追求自由的愛情,但是,當激情褪去,種種沖突便表現了出來。值得關注的是,出走后的現實生活是否如想象中的幸福,青年男女是否真的反抗成功等問題,青年男女在獲得了自己期望中的自由平等后,才發現,實則是進入了新的圍城,且進進出出,始終尋不到正確的道路。
(二)作家主體創作意識的影響
知識分子這一形象在二十世紀的文學作品中,所占比例是很大的,且在不斷變化。作家一邊書寫作品里的知識分子形象,一邊借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來反映自己的心路歷程、書寫自我。巴金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過,如果自己不在法國從事小說創作,汪文宣就是自己,汪文宣的結局也很可能在自己身上上演。巴金與自己筆下的人物形象——汪文宣有著類似的經歷,都得過肺病,在重慶生活過一段時間。在20世紀40年代,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并不是很理想,他們只能在艱難的環境中勉強度日,巴金寫汪文宣、柏青等各種知識分子形象,也正是為了反映現實以及知識分子所遭受的種種經歷。
《寒夜》寫于1944年的秋冬,完結于1946年,最初在《文藝復興》連載,巴金在談到自己的創作主旨時曾經說過,寫《寒夜》,寫汪文宣、曾樹生、汪母并非是為了鞭撻,其中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寒夜》的主角汪文宣是一個在貧困線上掙扎,不幸因肺病去世的知識分子形象。汪文宣所患的肺病不僅巴金得過,巴金現實中的幾個朋友也得過,所以,在汪文宣身上凝聚的,不僅是某個個體的悲慘境遇,還是一部分群體在當時所經歷的生存困境,汪文宣每天所經歷的,也正是巴金所熟悉的生活,“他寫的是自己的親朋好友,傾吐的是他們的悲傷和希望。”[4]巴金在評價《寒夜》時說過,“《寒夜》是一本悲觀、絕望的小說。”[5]但巴金在自白時,也曾說過,這是一部充滿希望的小說,絕望過后,迎來希望。汪文宣在勝利的那個夜晚死去,并不是預示著希望的徹底離去,而是黑暗中的光明即將到來。
《寒夜》與《圍城》的寫作時間大體相同,都在《文藝復興》連載。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初,充當的是啟蒙者的角色,但是,隨著革命失敗,前方道路的愈加困難,部分知識分子失去了社會責任感和良心。錢鐘書指出了人性的弱點,卻沒有給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錢鐘書的《圍城》寫了兩年,1944年開始寫,1946年完成,是在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寫成的。錢鐘書寫這部小說時,從自己熟悉的階層取材,借助方鴻漸的思想變化、心理活動來傳遞他自己對當時知識分子整體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知識分子需要重新定義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在批判諷刺背后所表現出來的,是對前行之路的隱憂。錢鐘書在小說中整體表現出的批判意識,實則也是對文化的一種反思意識,錢鐘書所塑造的“圍城”,不僅體現在婚姻愛情上一座又一座的圍城,還體現在人生上。
三、結語
巴金書寫了汪文宣、柏青這樣良心還未滅絕的知識分子形象以及他們的悲慘命運,想要表達的是對現實的反思以及對自我的救贖。錢鐘書的《圍城》,塑造的是方鴻漸、趙辛楣這樣兜兜轉轉找不到人生道路的失路型知識分子形象,以及那一群失去了社會良心與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形象。巴金與錢鐘書雖然描寫的對象、塑造的知識分子形象不相同,但是,都體現了對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在20世紀40年代不同命運的關注,探究了他們的心路歷程與人生選擇,試圖追尋造成知識分子生存困境的真正原因。
參考文獻:
[1]巴金.寒夜[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91.
[2]祝勇.知識分子應該干什么[M].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9.
[3]陸文虎.錢鐘書研究采輯(一)[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256.
[4]譚興國.巴金的生平和創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07.
[5]巴金.探索與回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65.
(作者簡介:張萌,女,碩士研究生在讀,寧夏大學人文學院,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文學)
(責任編輯 杜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