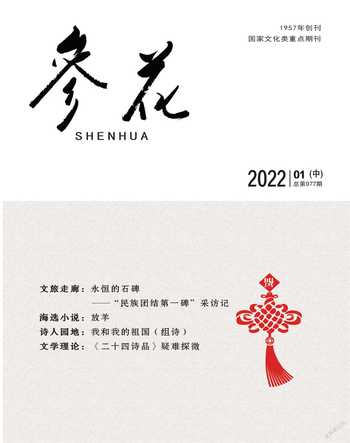在馬孔多中生活
一、引言
加西亞·馬爾克斯是拉丁美洲文學史上一位代表性人物,他的出現通常與拉美“文學爆炸”和“魔幻現實主義”緊密相連。這兩個概念的傳播,一定程度上也歸功于他所創作的小說《百年孤獨》。作為當代拉丁美洲文學的代表,《百年孤獨》中虛構出的文學地域“馬孔多”也受到了廣泛的關注。馬孔多如同一個濃縮的世界,文本通過多種不同類型人物的經歷反映出馬孔多的興衰。
“馬孔多”系列小說基本包括了從《枯枝敗葉》到《百年孤獨》期間,馬爾克斯所創作的內容,同時,這個時期也是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
在馬爾克斯的創作中,總是伴隨著“魔幻現實”的字眼,但實際上,馬爾克斯并不認為自己構想的故事帶有魔幻的色彩,他本人表示,書中的故事都是家人講述和自己親身經歷的,并非虛構。馬爾克斯作品出現的很多人物與經歷都可以在其自傳《活著為了講述》中找尋到原型。
在馬爾克斯的作品中,“馬孔多”系列小說占據了重要的地位。馬孔多的發展與命運,以及其中發生的故事充滿了神話與寓言的色彩。在《枯枝敗葉》中,馬孔多的形象已經基本形成。馬孔多是馬爾克斯完全虛構出的一個地點,是作者思想中的一個虛構的地帶,但馬孔多發生的種種事件仿佛“一個世界的縮影”。這個特點在他的作品《百年孤獨》中體現得更為明顯,小說以馬孔多為故事背景,描繪出在這個世界中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各種事件。
二、馬孔多中的人物
(一)家族內的人物
《百年孤獨》中的馬孔多有著更加強烈的神話傾向,在馬孔多,尤其是布恩迪亞一家的社會屬性總是混沌不清的,具有一種神話的夢幻感。馬孔多的其他人總是被弱化為群眾,居民被刻意“無化”,《枯枝敗葉》如此,《百年孤獨》仍是如此。
《百年孤獨》以一個“古怪”的家族故事為中心,寫社會歷史。“《百年孤獨》描寫馬孔多小鎮的變遷,其主要的表現對象是一個家族的秘史。”[1]家族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著自己獨立而完整的世界,但是,卻又共同組成了一個整體世界,每一個人都在具有自己獨特性格的同時,突出著整個家族的集體性氣質。
《百年孤獨》描寫一個家族的興衰,家族之中,每一個人的發展,每一種個性的遺傳與迭代,作者有意地用相似的性格與相同的姓名模糊人物之間的差異,使得人物的整體性格氣質更加突出、鮮明。雖然每一代名字相同的人物的命運結局都相似,循環的敘述模式突出了家族集體性的氣質特點,但同時每一個人物都有著自己獨特的精神特質。
烏爾蘇拉在小說中也點明了這一點,布恩迪亞上校是個無力去愛的人,阿瑪蘭妲是世上最溫柔的女人,麗貝卡有無畏的勇氣……小說中的七代人在反映馬爾克斯“內心真實”的同時,也具有獨特鮮明的個人特質。在馬孔多,尤其是布恩迪亞一家的社會屬性總是混沌不清的,具有一種神話的夢幻感。同時,這也使得布恩迪亞家族的每個人的獨特性格更加突出。
(二)無根的人物
《百年孤獨》中,除了布恩迪亞家族自己的故事之外,還描繪了一類有些特殊的人,他們進入馬孔多,或是短暫地停留之后再次出發,或是定居在馬孔多,與布恩迪亞家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小說從不明確地說明這些外鄉人究竟來自什么地方,他們游離在世界之中,最終來到了馬孔多,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最開始來到馬孔多的是一群吉卜賽人,他們帶來了先進的文明,帶走了布恩迪亞家族的一位男性。梅爾基亞斯德就是其中一位,梅爾基亞斯德留下了一卷羊皮書,使得小說充滿了強烈的宿命感。同時,梅爾基亞斯德在馬孔多居民遭受“失眠癥”折磨時,又來解救他們,但最終他也沒有留在馬孔多。
自此之后,馬孔多這樣一個與世隔絕的“烏托邦”開始不斷地接待來自外界的各種人:抱著骨殖袋的麗貝卡,意大利技師皮埃特羅,能夠讓動物多產的佩特拉,布恩迪亞上校的軍人朋友等,還有最大的外鄉人群體“香蕉公司”,他們都涌入了這個類似世外桃源的小鎮。
吉卜賽人最初撕開了馬孔多的一個口子,使得各種文化都與馬孔多產生關系,他們推動著馬孔多的繁榮,也推著馬孔多慢慢走向已經寫好的結局。
馬孔多還有另外一類外鄉人,外出歸來的返鄉人。阿瑪蘭妲、烏爾蘇拉與何塞·阿爾卡蒂奧都是這類人物的典型。實際上,在小說中,自從馬孔多的大門被打開后,返鄉人也就形成了。返鄉人對自己的家鄉充滿期待與希望,最后卻發現自己的習慣與思想既不屬于家鄉也不屬于遠方。這些沒有或者拋棄了自己根的人物帶著強烈的孤獨感,或生活在馬孔多或離去,“沒能與任何人結下友誼,也沒能舉行一場聚會。”[2]這些人物的無所適從與作家馬爾克斯本人所處的拉丁美洲文化環境有極大關聯。拉丁美洲內部的文化是雜糅的,使得當時的拉丁美洲文學擁有了許多的新視角與反思。
在《百年孤獨》中,也有作者對處在文化雜糅下的自我身份問題的思考。之后,在1968年,馬爾克斯在《布拉加曼,一個優秀的奇跡推銷員》中使用了“孤兒”的形象。“孤兒”的形象體現出一種對自我身份的剝奪,對傳統身份的割裂,是自身的隱匿與游離。
(三)女性人物
在《百年孤獨》中,充斥著預言式的故事,整個故事的一開始便告訴讀者,馬孔多最終會毀滅。但無論小說中的人物到了第幾代,全書始終有兩個女性形象貫穿其中——烏爾蘇拉與特爾內拉。她們不僅是家族興衰的參與者,也是見證者。
馬爾克斯的作品語言細膩而充滿情感,這種語言特色與拉丁美洲地區語言本身具有的巴洛克式的風格有關,這種語言上細膩優美的特性使得馬爾克斯筆下的人物也生動而細膩,尤其是女性形象更加細膩動人。
《百年孤獨》中的女性內心豐富,烏爾蘇拉充滿了智慧,年輕時活力四射,老年時轉入悲觀;特爾內拉游離在家族之外,卻成為整個家族中男性的開導者與安慰者。作者在作品中透露出對烏爾蘇拉與特爾內拉的贊美之情,雖然特爾內拉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形象,但在作者的描繪之下,她同烏爾蘇拉一樣是勤勞而善良的女性。
在全書中,烏爾蘇拉是支撐整個家族道德與行為的規范楷模,特爾內拉則是整個家族的一面鏡子,她在家族之外,卻真實地觀照著整個家族的發展、興衰。她用自己的慈悲與愛意對待整個布恩迪亞家族,直到最后去世。
《百年孤獨》以一種魔幻的框架進行建構,使得作品充滿了史詩的質感,烏爾蘇拉與特爾內拉的存在使得作品看似混沌,但內部結構卻異常穩定。在《百年孤獨》中,與女性相關的描寫總是和情感欲望相關聯,文本中關于情感欲望的描寫帶著強烈的詩學特征,隱秘生活帶著夢幻的傾向,包含著大量的非理性因素與人物單純原始的激情。作品中對于情感欲望的描寫總是帶著憂傷的圓滿,瘋狂而無目的,這明顯與孤獨有很強的相關性。
(四)超自然的人物
在馬爾克斯的作品中,總是透露出一種愛與死亡的哲學,馬爾克斯本人也十分喜歡探討關于“死亡”的命題。在《枯枝敗葉》《百年孤獨》《家長的沒落》中,總是圍繞著“死者”展開,采用詩化的手段進行描寫。作品中不乏死者與生者的對話交談,打破了傳統的生死觀,抹除掉這種界限,讓時空交錯。
在《百年孤獨》中,經常出現已故的梅爾基亞斯德教家族中的人如何解讀羊皮卷,在樹下的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還有決斗中已故的男人。除此之外,書中隨處可以見到超自然卻又合乎這個世界情理的超自然人物行為,例如,為自己縫制壽衣又拆壽衣的阿瑪蘭妲等。
書中的生與死被拉到同一個維度,死亡并非消失、化為虛無。直到最后,隨著羊皮卷的預言被解讀出來,馬孔多消失,一切的意義與價值才算是煙消云散。
在拉丁美洲傳統的文化中,已故的人似乎以另一種方式一直存在。直到現在,墨西哥地區還會過亡靈節,所以,在拉丁美洲地區,死亡似乎并不意味著消失,遺忘才是。死亡是生活中的一部分,這樣的思想使馬爾克斯的作品對死亡的描寫變得平靜、淡然,甚至可以變成一件可以談論并坦然接受的事情。
三、馬孔多中的人物形象成因
(一)文化混亂中的“內傾”
在1930-1950年,拉丁美洲文學的發展是十分緩慢的,是處在一種幾乎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在這之后,拉丁美洲文學迎來了“文學爆炸”時期。“在1950至1970年產生的小說中,有一種很明顯的特征:努力放棄地區主義描寫,肯定新技巧、探索新技巧。”“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小說我敢肯定大家都知道。它們也即所謂的‘文學爆炸和許多‘文學爆炸之外的作品。”[3]
這個時期,歐洲文學對拉丁美洲文學的影響更加廣泛。由于當時拉丁美洲地區相較于歐洲是落后的地區,又由于現代主義的介入,當時拉丁美洲的作家不得不走向國際化的道路。“馬孔多”作為作者虛構的文學地域,它更像是一種自我精神的體現,這也使之帶有了神話的屬性。“馬孔多”成為作者內心“深蘊心里”的表現,變成意識形態的象征,也體現出作者的作品轉向表達內心世界與“非理性”的情感。《百年孤獨》中,“馬孔多”這個地域開始也是隔絕的,甚至可以說是滯后的,是在后來的進程中加入“現代”進程中的。同時,在《百年孤獨》中,視野基本上局限在宅院之中,宅院的內外形成了對比,這種宅院內外的二重性使得作者“內傾”的思想體現得更為明顯。馬爾克斯以一種內向的、夢幻般的描寫使得讀者的關注轉向了作品體現出的內心世界與情感,而非理性客觀的現實。
(二)文本架構技巧
馬孔多作為馬爾克斯小說中的一個重要文學地域,已經成為作者的一種精神狀態,也代表著一種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上的烏托邦。作品中的馬孔多實質上成了一種隱喻,隱喻著無法擺脫的孤獨。
作品中的馬孔多充滿著拉丁美洲的特色,神秘、浪漫,同時,從馬孔多出現之初,就被孤獨包裹著。馬孔多的起源隱喻著神話,特別是《百年孤獨》中的“羊皮卷”,這種預言式的展開,將現實融入極端精神狀態的刻畫方式更加突出了作品的神話特征。
《百年孤獨》的最后,“羊皮卷”被破譯出來,使得作品給人一種“書中之書”的宿命感。同時,小說中重復的人名造成了一種混沌的感覺,像是作者對讀者記憶的考驗。而且小說的開始就注定了結局,預言式的寫作與《佩德羅·巴拉莫》從特定精神狀態出發相似,并且小說中的時間也是混沌不清的,更加加深了小說的虛無感。
馬孔多的人物也總是充滿了壓抑與痛苦,他們總是固執又封閉,在虛無中迷失,這種孤獨并非刻意而為之,而是基于作者本身的人生體驗,是作者把這種體驗外化表達出來的結果。
《百年孤獨》中,馬孔多始終處在一種封閉的循環中,地理環境也是封閉的,缺少與外界的溝通,這使得馬孔多的孤獨感更為突出。雖然馬孔多經歷了繁榮時期,最后卻化為虛無,這樣封閉的敘事結構使得作品充滿了孤獨與虛無。地理上的封閉使得馬孔多充滿了無盡的孤獨感,這種孤獨也成為家族與馬孔多消亡的緣由。
四、結語
“魔幻現實主義首先是對現實所持的一種態度……那么,何為魔幻現實主義面對現實的態度呢?我們說過,不是去臆造用以回避現實生活的世界——幻想的世界,而是要面對現實,并深刻地反映這種現實,表現存在于人類一切事物、生活和行動之中的那種神秘。”[4]馬爾克斯認為,他描寫的發生在馬孔多的人物、故事并非魔幻,而是在誠懇地描寫現實,描寫社會與神話幻想的極端交錯。馬孔多的孤獨與衰敗是馬爾克斯所在的拉丁美洲地區經歷的歷史,他作品中無處不在的孤獨是拉丁美洲地區共同的迷茫與虛無所致,特殊的孤獨感在其他拉丁美洲作家作品中也能感受到,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東方,是拉丁美洲地區作家特有的精神特質。
馬爾克斯曾經說過,馬孔多是他對于童年故鄉的一種回憶所形成的虛構小鎮,在這種虛構中似乎潛藏著烏托邦的傾向,在外來人口入侵前,馬孔多的開端渲染出一種田園的氛圍,以一種神話的模式展開,雖然最終以一種宿命論一般的方式無法抗拒地衰亡。
參考文獻:
[1]許志強.馬孔多神話與魔幻現實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2][哥]馬爾克斯.百年孤獨[M].范曄,譯.海口:南海出版社,2011.
[3][哥]達索·薩爾迪瓦.回歸本源[M].上海:外國文學出版社,2001.
[4]陳光孚.魔幻現實主義[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
(作者簡介:吳明鈺,女,本科在讀,安徽農業大學,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責任編輯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