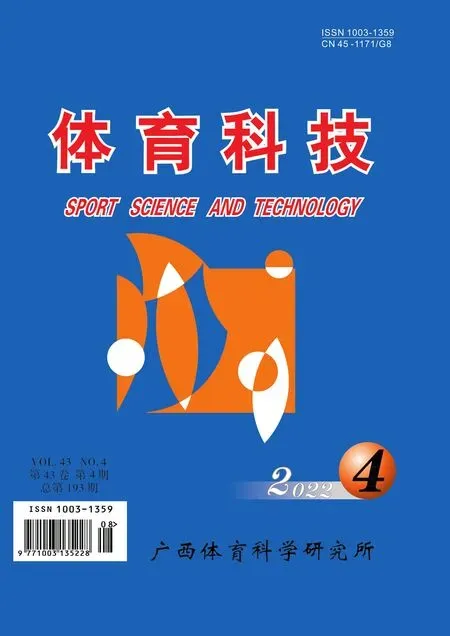武圣關公符號的歷史演進研究
孫曉源 王冬慧 李德柱
武圣關公符號的歷史演進研究
孫曉源1,2王冬慧2李德柱1
(1.運城學院 體育系,山西 運城 044000;2.內蒙古師范大學 體育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關公文化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現象的總和,它的發展經歷了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參與,是中國傳統文化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在古代人民的生產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主要以當時社會制度為基礎,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進行解讀,深入探究小農經濟制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官僚體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對武圣符號的促進和發展。對武圣符號在不同時期的發展狀況進行梳理,解析關公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內涵,挖掘關公“武圣”符號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發揮出關公文化的當代價值。
關公;歷史變遷;武圣;符號
中華文化歷經五千年的發展愈發輝煌,延續至今的著名人物當屬“文圣”孔子和“武圣”關羽,二者的發展歷經千年而經久不衰,關公文化即指關公的價值觀念、思想品德、精神氣質及其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影響,其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對社會生活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在思想方面,尤其是在道德倫理方面,關公文化精神價值的核心在于道德價值[1]。
1 武圣符號的構建基礎
1.1 經濟基礎
關公符號的構建與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密不可分。中國古代以小農經濟為主體,農業是古代民眾經濟生活的主要來源,原始時期,人們多使用石制的農具,生產力低下,隨著封建社會的到來以及鐵農具、牛耕等相對先進的生產工具的推廣使用,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農民始終沒有對土地的所有權,絕大多數的土地都掌握在封建地主的手中,農民只能租賃地主的土地,忍受著地主嚴酷的壓迫與剝削。封建小農經濟大多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形式,生產力低下,無力抵抗強大的自然災害,古代農業諺語“靠天吃飯”就是指農民在農業中聽天由命的現象,所以就注定了他們的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統治階級和地主手中,僅僅憑借自己的力量無法與天抗衡,與統治階級抗衡。所以農民只會選擇一味的忍受、等待,將希望寄托于別人身上,希望可以通過一個為民請命的明君或神靈來解救自己,帶領自己脫離苦海。所以關公應時而生,成為了人民崇拜的對象,為“武圣”符號的構建提供了豐富的土壤。
1.2 政治基礎
自秦朝起,中國長期以來的政治體制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官僚體制,但本質上還是奉行宗法制度,主張家國同構,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族制度和國家制度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為了維護統治,統治階級會自上而下的建立一套由中央到縣區一級的國家機構。俗話說“君如舟,民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國家政權出現危機時,統治者希望得到人民和將士的支持來鞏固政權。關公不斷被加封的背后,其實質無一不是為了鞏固政權,收攏民心。統治者需要通過權威性人物來穩定政權,通過權威性人物感召力量以達到爭奪政權、收買人心等作用。如元朝屬于“異族”統治中原,故民族矛盾尖銳,而漢族人數在政權的統治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所以更需要一種信仰崇拜力量來鞏固政權力量,所以就有了元朝皇帝元文宗圖帖睦爾于天歷八年(1335年)對關羽加封“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
1.3 文化基礎
由于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影響,古代人民始終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只想通過外界尋求一種需求和依賴,所以在戰亂頻繁的年代,人民希望有個英雄能夠帶領他們創造新生活。故而衍生出了英雄崇拜。關公作為一名真實存在于歷史的人物,通過人民的崇拜,逐漸由厲鬼演變成圣帝。中國古代文化推動關公神化主要方面有三:
(1)佛教的傳播。佛教最早將關公納入宗教,宋代時,關公成為了寺院供奉的伽藍神,佛教作為一個外來的宗教,通過借助關公的聲威來擴大自己的傳播范圍。當然佛教在借助關公發展的同時,關公也因此越來越神秘,逐步被神化。
(2)儒家思想的發展。因關公手持《春秋》的溫文爾雅的一面,得到了儒家的崇奉,縱觀關羽一生,行事立身都以“大義”為本,這就為儒家對關公形象的利用打下了基礎,儒家通過關公展現出了儒家獨有的文化內涵,也更好的詮釋了儒家“忠”“義”“仁”的良好品質。
(3)道教的推動。道教對關公符號的發展也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關羽出生于道教的創始時期,但直到北宋時才得到了重視,封號也從“顯烈王”到“忠惠公”再到“崇寧真君”,這些封號從側面反映出關公的政治地位的不斷增加[2]。
2 關公“武圣”符號建構萌芽階段
2.1 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關公的英雄事跡已經在民間流傳,但故事和傳說比較稀少且單一,魏晉南北朝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東漢末年開始逐漸形成的三國時期,也是關羽結識劉備、張飛,共謀天下事的時期,漢獻帝于公元220年禪讓于曹丕,稱魏文帝。此后劉備于公元221年建立蜀國,孫權于公元229年建立吳國,至此中國歷史進入了三國時期,直到公元280年西晉統一全國結束;第二個階段是兩晉十六國時期,公元266年,司馬炎取代曹魏政權,建立西晉,280年滅東吳政權后,西晉統一全國,但291年的“八王之亂”使得西晉元氣大傷導致外族入侵,于公元316年滅亡。公元420年,劉裕建立劉宋政權,打開了第三階段的序幕,歷代政權不斷更迭,直到公元588年,隋文帝滅陳結束了三百多年的分裂戰爭,建立隋朝,魏晉南北朝至此結束。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的頻繁更迭,給人民的社會生活帶來了嚴重的災難,社會矛盾激烈導致農民起義頻發,朝廷借助地方軍事力量來鎮壓,短時間雖有明顯效果但同時各地豪強的軍事力量也在逐漸強大,晉武帝的大肆分封進一步加劇了地方割據,導致“八王之亂”,出現尸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慘象。匈奴、鮮卑、羯、狄、羌等少數民族逐漸開始入主富饒的中原地區,雖然促進了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同時也加深了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民族間殺伐不斷,“尚武”之風盛行引發了對勇猛武將的崇拜,統治階級希望借此提高軍隊士氣,百姓則希望這些勇猛名將能帶領自己脫離苦海,過上幸福生活。許多歷史上有豐功偉績的名人,尤其是以“武功”著名的王侯將相也被民眾加以崇拜,包括“姜太公、秦始皇、劉邦、韓信、張良等”。“誅顏良斬文丑”的關公也成了魏晉南北朝民眾歌頌的對象,許多名將都會被民眾拿來與關公作比較。例如關公刮骨療毒的事跡被拿來與長孫子彥的鋸骨療傷作比較,突出其勇武,由此可見,關公勇武之名深深影響著后世人民,也正是因為關公勇武事跡,使其勇武形象在魏晉南北朝時逐漸確立,促進了關公符號的發展。
2.2 唐朝時期
隋文帝統一全國后,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隋煬帝昏庸無能、奢靡享樂,導致隋朝農民起義的爆發,公元618年,隋煬帝被殺,天下群雄紛紛自立為王,同年5月,李淵稱帝,建立唐,直至公元628年,唐朝完成了全國的統一,經歷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的開明治理,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后唐朝由盛轉衰,此后地方割據成為了唐朝的頑疾,直至滅亡也無法解決。
唐朝關公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佛教的推動,佛教經由漢代的傳入,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在隋唐時期逐漸顯現出鼎盛的趨勢,在統治者的支持下,佛教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其中出現了大唐玄奘去天竺取經、鑒真東渡等千古佳話。隋唐時期,統治者就已經開始認識到了發展宗教對鞏固統治的作用,除了出現唐武宗毀佛以外,隋唐時期統治者大多奉行三教并立的政策。佛教對于關公的利用和神化大約可以追溯到“玉泉顯圣”事件。
雖然關公在隋唐時期受到佛教的推動,但并未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公元731年,唐明皇李隆基建武廟,主神為姜太公,且關公并未以陪祀神的身份出現在武廟中,公元760年,唐肅宗追封姜太公為武成王,關公正式以陪祀神的身份進入了武廟。隋唐時期對于“忠義”尤為推崇,集中表現在“為國捐軀、以死報國”的精神,“忠義”成為隋唐時期倫理道德的重要標準,以“忠義”而受推崇的關公雖然在這一時期并未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隋唐時期對于忠義之舉的鼓勵和支持為后世關公符號的發展埋下了伏筆[3]。
3 關公“武圣”符號的快速發展階段
3.1 宋朝封王
關公武圣符號在宋朝的快速發展與宋王朝所面臨的內憂外患的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系。宋太祖經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后,由于親身實踐及對唐王朝覆滅的教訓。他深感軍事力量對一個王朝的影響,因此,通過杯酒釋兵權等一系列措施,削弱了兵權及相權,所以宋朝自始至終奉行的是重文輕武政策,這也為以后宋朝的國內危機埋下隱患:
(1)在重文輕武的思想指引下,宋朝的文官體系不斷壯大以至于統治階級文官系統過剩造成臃腫,同時文官質量也不斷下降使得有能之士屈指可數。從經濟角度看,供養文官體系的資金占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經濟發展,相對應的對于軍事的經濟支出相對降低,削減了國家的經濟實力及軍事實力。
(2)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后,宋朝的軍事實力處于持續被削弱的狀態,出現軍中無常帥等現象,也嚴重阻礙了軍隊的實力及軍隊的積極性。
(3)因軍事上節節敗退,統治階級對于國家安全、對于侵略者采取的不是積極政策,而是一味求和,致使大量白銀外流,百姓賦稅加重,社會生產力不斷降低,形成惡性循環,導致社會矛盾尖銳。
宋朝不僅內部積貧積弱,外部還有遼、西夏等國的威脅。遼國建國早于宋朝五十年,是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其國土范圍占據了現今的內蒙古、遼寧和山西、河北的部分土地,實力強勁。加之宋朝都城開封地處平原,既沒有過硬的軍事實力又沒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所以遼軍攻打宋朝時往往會出現敵方軍隊很輕松打到都城開封的現象,宋軍絲毫沒有抵抗的能力。統治階級過于懼怕遼國的軍事實力,最后以“澶淵之盟”議和賠款為結果。西夏見此,也開始進行趁火打劫。
統治階層在關公、張飛追隨劉備共圖大業建立蜀漢政權的過程中,發現了關公這一歷史角色的政治價值,至此,關公的政治價值開始被統治階層不斷構建。首先就體現在關帝廟的建立。關公死后,在荊州一帶被傳為厲鬼,荊州地區人民希望通過建祠堂、祀關公的方式,使其得到安息,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關公生前在人民中深厚的影響力。
3.2 元朝時期
元朝時期,作為“異族”統治中原地區,統治階級在進行社會統治和治理時便困難重重,面對尖銳的民族矛盾,他們希望通過不斷的吸收漢族文化來緩解,他們迫切的需要一種精神信仰來鞏固已有的政權,于是推進了關羽“武圣”符號的構建的進程。
這一時期中對關公符號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關帝廟由宋朝部分地域內的供奉逐漸發展到全國范圍內的供奉。民間信仰的不斷升級加之統治階級的不斷鼓勵與支持,關帝廟的數量在明朝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2)關公神像造型逐漸固定下來。后人根據歷史及自己的創造給關羽塑造了一個多須髯和手持青龍偃月刀的形象。
(3)關公祭祀逐漸頻繁。其原因大多來自于統治階級的推崇。關公祭祀制度也在發展中不斷完善。明朝時,對于關公的祭祀規格和次數都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4)對關公認識的不斷加深。關公“武圣”符號的構建初期主要看重的是關公自身所具有的條件,主要表現在關羽戰場上的英勇氣概。隨著關公“武圣”符號的不斷深入發展。到了宋元明時期,主要看重的是關公自身所表現出來的“忠義仁勇”的高貴品質。
3.3 關帝廟及謚號的發展
關帝廟在關公死后僅限于荊州地區等局部地區。據文獻記載,關帝廟在唐朝時的數量很少,至唐德宗貞元年間已有關帝廟,但并沒有充足的資料證明關帝廟建于唐朝。到了宋朝,關帝廟的數量不斷增加。
關公生前最高的爵位為斬殺顏良后,曹操上表漢獻帝所封的漢壽亭侯,陳壽《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中記載“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于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這是較低一級的侯爵,低于縣侯和鄉侯。據《三國志》“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可知,關羽生前最高職位為劉備稱漢中王時所封的“假節鉞”,是當時劉備軍隊武將中最高職位,劉備手下武將僅關羽有此殊榮。死后,后主劉禪追謚為“壯繆侯”以表彰其為蜀漢政權做出的貢獻及緬懷。此后至唐朝關羽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視,僅作為“武圣”姜太公的陪祀武將供奉于武廟中。宋朝趙徽宗年間,關羽才開始了由“武人”向“王”的轉變。北宋崇禎元年(1102年)追封關羽為“忠惠公”,由侯爵(壯繆侯)正式晉升為公爵;崇寧三年(1104年),宋徽宗再次封關羽為“崇寧真君”;大觀二年(1108年),宋徽宗加封關公為“武安王”,正式晉升為王爵;宣和五年(1123年),宋徽宗又一次加封關公為“義勇武安王”。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趙構追封關公為“壯繆義勇武安王”;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宋孝宗加封關公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4]。
4 關公“武圣”符號的鼎盛時期
4.1 明朝封帝
明朝起始,明太祖朱元璋通過農民起義建立了明朝,為了表現明太祖禮事神邸之意,明朝開始不斷祭祀關公等諸神,明朝祭祀關公還體現在明太祖吸取了元朝后主弱而臣強,導致強臣廢帝致使元朝覆滅的教訓,希望通過祭祀關公為王公大臣立下忠君愛國的典范,使其恪守奉行忠君之道[5]。
朱棣起兵篡位后,永樂年間正式將關公定為武廟的主神,與孔子的文廟呼應。此前,姜尚一直作為武廟的主神接受祭祀。關羽為何會取代姜尚?這就需要從朱棣的政治背景開始分析。朱棣經過“靖難之役”的勝利后,深感諸侯藩王割據的危害,所以他采用一系列手段加強中央集權,而姜尚作為一個權謀之師,又是西周時期一個強大的諸侯王,很明顯不符合明朝統治階級加強中央集權的要求,而關羽作為一個歷史上有名的忠臣,順應了統治階級加強中央集權的潮流,故而選擇了忠義之將關羽。
關羽之所以能成為主神是因為他們發現了關公的政治價值,看中了關公的“義勇”,看重他對正統王朝的忠誠,所以不斷地抬升關公的政治地位,將其作為宣揚思想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明朝中葉,由于統治階級荒廢朝政,使得國力不斷下降,民族矛盾激化,更甚者危及封建統治。統治階級需要利用神的力量來鞏固對民眾的統治。在明朝萬歷年間,關公被封為“協天護國忠義帝”而后又追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圣帝君”,關公“武圣”符號實現了從王到帝的轉變。
4.2 清朝封圣
隨著關公“武圣”符號政治功能的發現,關公“武圣”符號在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峰,其影響力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為了更好的利用關羽的政治符號,清朝對關羽的封號達到了另一個高潮。順治九年,關羽被加封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此后又先后進行了多達十三次的加封,封號的字數最多達到26字[6]。
清朝時期,由于封建統治階級不思進取及執政體系的貪污腐敗,使得人民負擔加重。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于清政府腐敗,在不斷戰敗、割地賠款中,農民的賦稅日趨嚴重,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農民起義愈演愈烈,當時的統治階級迫切希望出現一個挽救天下的神靈,所以極力抬高關羽的政治地位,不斷追封使得關公崇拜達到了歷史的頂峰。他們利用民眾對關帝的敬畏和崇敬,不斷加封關帝,目的主要是希望民眾能夠像關帝追隨劉備一樣,效忠清王朝,英勇反抗入侵外敵。
這個時期關公符號的特點表現在:關帝廟的數量上的持續增加以及關帝廟的規格更是比照帝王的標準,關帝廟的數量擴展到全國范圍內,并且在海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幾乎家家戶戶都會擺關公的雕塑像,這與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至此,關公“武圣”符號最終確立。
[1]王冬慧,暴麗霞,林辰宣.關公體育文化的概念、結構與功能闡釋[J].體育研究與教育,2020,35(4):80-85.
[2]王冬慧,馬苗,殷海濤.武圣文化視域下的關公民俗體育多維審視[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2020,19(8):73-78.
[3]王冬慧,王建洲,馬苗.關公青龍偃月刀的演變、文化內涵與傳承路徑[J].哈爾濱體育學院學報,2020,38(01):38-41+49.
[4](晉)陳壽.三國志[M].夏華等編譯.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16.
[5]王冬慧,張雨剛,馬苗.非遺視域下關公風箏的傳承與發展研究[J].哈爾濱體育學院學報,2019,37(5):50-54.
[6]王冬慧.文化軟實力視域下武圣關公大刀的人類學解讀[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2018,1(7):76-80.
O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Generative Logic of Guanyu Cultural Symbols
SUN Xiaoyuan, etal.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044000, Shanxi, China)
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武圣關公大刀文化軟實力研究2020YJ180;山西省體育局科研項目:體旅結合視角下山西“關公武圣”文化產業研究20TY124;運城學院體育系學科經費資助;山西省留學歸國科研項目:武圣關公體育文化產業研究2020-145。
孫曉源(1999—),碩士生,研究方向:民族傳統體育學。
王冬慧(1986—),講師,博士,研究方向:關公體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