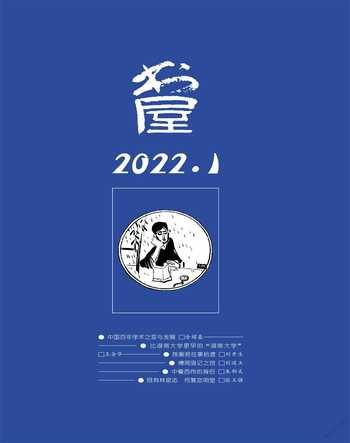再說周作人
張貽貝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走出了南京老虎橋監獄,距他1945年12月6日晚在家被捕,他做了精確計算,歷時一千一百五十天。為此,特做詩一首:“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學閉關。今日出門橋上望,菰蒲零落滿溪間。”這首詩后邊,他注釋道:“橋者,老虎橋;溪者,溪口;菰者,蔣也。今日國民黨與蔣一敗涂地,此總是可喜事也。”
周作人以漢奸罪被捕入獄。根據《懲治漢奸條例》,汪偽政府要員陳公博等人均被判處死刑。對周作人核其所為,罪列“通謀敵國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為漢奸,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之首,“周氏亦不無赴死之念”。但周作人是有幸的,在“國人皆曰可殺”聲中,有人以“人才亦不可以不惜”為由,為他呼吁、講情,“從寬發落”。1946年11月1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奪公權十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須生活費外沒收。又,1947年12月9日,法院改判有期徒刑十年,“其應負漢奸罪責自無疑義”。
周作人做漢奸,“下水”附逆后,隨之升遷,任汪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月薪一千二百大洋,對周作人是有誘惑力的。他曾得到汪精衛的看重,1942年5月11日,汪精衛參加偽滿洲國成立十周年慶典之后回來,同機隨行人員中就有周作人;次日晚“同仁宴請汪先生于寧遠樓,祝六十大慶”,周作人在座;1942年9月,周作人任偽華北作家協會評議會主席,“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學家,同時在文壇上握有最大的權威”;1943年4月5日,周作人應汪精衛之邀,前往南京就任偽國府委員講學等。
1949年10月18日,周作人返回北京八道灣11號家中,開始了新的生活。周作人充分發揮了筆桿子的優勢,不斷給中共高層領導人寫信,如他說:“又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已經直接送去。”至于給周恩來、康生、周揚、胡喬木、馮雪峰的信,就不止一兩封了。樓適夷說:“胡喬木同志特地召我談話,要我們重視周作人的工作,給他一定的重視與關心。”“還說過現在雖不方便,將來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適當出版的。”1950年1月,出版總署署長葉圣陶和秘書金燦到訪周作人,葉圣陶1950年1月23日日記:“飯后兩時,偕喬峰、燦然訪周啟明八道灣……聞已得當局諒解……晤見時覺其風采依然,較喬峰為健壯。”足見周作人精神風貌,健康狀況很是好了。
此間,周作人曾應邀參加北京市政協召開的座談會,中國文聯安排他同相當身份的人去西安旅行,中國文聯還宴請周作人,周氏可謂春風得意,運氣頗佳。
1955年1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更改稿費結算辦法,每月預支二百萬元(舊幣制),自此周氏始有固定收入。1959年12月4日,周作人“寄康生信”。次年1月13日,“人文社江秉祥君來談稿費事,三數日再作回復云。因與康生信故生效用,亦未知結果為何耳”,16日,“得人文社信,允每月支四百元。雖不足亦不好要求加多,寄信答應”。
四百元價值幾何?蕭軍從延安轉入東北工作,1951年定居北京,1959年10月1日,安排到北京戲曲研究所任研究員,每月發給生活費一百一十元。普通職工每月三四十元,養家糊口,多年不變,也挺過來了。
其實,周作人還有另外一些收入,“繼續為香港報刊撰寫文章”,為國內其他出版社、報刊寫文章,都得到不菲的稿酬。還有,“大約七年之久,其間中國文聯在生活上對周作人亦多有幫助”,又“先后將舊日記二十六冊售與魯迅博物館,共得1800元”。周作人的富裕生活是常人能比的嗎?但在國未富、民未脫貧的現實下,周作人應該“知恩圖報”,感謝中國共產黨,也應該對國人有懺悔之心吧!但是,他沒有,在他多次遺書里也找不到此類文字。
周作人不可能以一個單純的文化學者、散文大家而存在,因為這個名字與大漢奸聯系在一起,他已被公認“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他淪為漢奸,絕非偶然,他留學日本,親日、崇日,當日軍進犯時,他恐日,說:“和日本人作戰是不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岸來了。我們的門口是洞開的,如何能抵抗人家?”周作人不相信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取勝。因此,眾多友人講明利害,呼喚他南下,他是不認同的。在歷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他選擇附逆日本。
面對兇殘的日本侵略者,陳獨秀先生毫無畏懼地說:“我們的出路,只有忍受不堪忍受的犧牲與痛苦,給敵人一點小教訓,使他們知道我們也不甚容易欺負,……真正懂得絕對停止內戰與軍隊統一、國家統一之重要,真正懂得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之重要,經過兩三個五年計劃,我們便可以由破落世家變成新興世家。”陳先生對戰勝日本侵略者充滿著信心,對周作人叛國投敵的行徑給予痛斥,他說:“在日本帝國的槍尖指揮之下,在日本帝國主義走狗漢奸賣國賊領導之下,高談中國文化再生,這不能不是人類文化之奇恥大辱!因此我不能不為周作人先生惋惜,嚴格地說,應該是斥責不是惋惜,雖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美國哲學家桑塔亞那說得好:“人的見解是受利益驅動的,而利益上的差異必然要導致偏見的產生。”周作人在利益驅動下,就成為“人類文化之奇恥大辱”標桿人物了。
有的學者認為,“周作人的價值混亂與路徑迷失”,什么“意志薄弱”等,我倒不是這樣認為。周作人“學貫中西,融通古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周作人在文壇上的地位達到頂峰,幾乎無人可以挑戰”。他在文章中寫道:“人不能改變本性,也不能拒絕外緣,到底非大膽的是認兩面不可。”又說“因為世上本沒有唯一的正確的道路”,言外之意,只有適合他要走的路才是正確的路。
對于周作人“陷入迷途”,還有一種說法,魯迅三十余年的好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提到周作人:“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于后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這只是許氏的一廂情愿,看看魯迅研究專家朱正先生是怎么說的:“周作人做漢奸還是1937年以后的事,魯迅這時已經不在了。魯迅在世的時候,周作人最多是個資產階級文人,那個時候兩人在政治方面的分野還不能說是敵我矛盾的性質”,“周作人后來是漢奸,魯迅后來是無產階級戰士,政治上是天壤之別”。其實,周氏兄弟1923年鬧矛盾就分開了。
周作人充當日本侵略者的工具,是不爭的事實。吊詭的是,當下《齊魯晚報》某人說周作人“與日偽合作,實為中國近代學人中一種值得深思的文化政治現象,不能簡單以民族主義觀點斥之”(見《齊魯晚報》2020年11月14日)。把賣國投敵的漢奸行徑稱為“與日偽合作”,如果對漢奸“斥之”,就給你戴上“民族主義”的帽子。該文作者是否想為周作人翻案?
2010年1月20日,楊絳先生致鐘叔河先生信中寫道:“漢奸是敵人,對漢奸概不寬容。”(楊絳的話是否與鐘叔河彼時在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有關,不得而知)。季羨林在《周作人論》文中寫道:周作人“成為不齒于人類的大漢奸賣國賊”,“這一頂漢奸帽子是他給自己戴上的,罄東海之水也是洗不清的”。
至于有人說周作人的著作“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價值”,“人歸人,文歸文”。人與文完全分開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止庵先生在接受《齊魯晚報》采訪時說:“過去很多人喜歡拿魯迅貶低周作人,現在則有一些人常拿周作人貶低魯迅,這都是不對的。”(見《齊魯晚報》2020年5月16日)
今后,對周作人的解讀,人們還會有不同的說法,其實,對周作人的評價并不重要,但對漢奸、漢奸文化,是絕對不可忽視的。漢奸、漢奸文化對人性的扭曲,對社會的殺傷力,絕對不可低估,周作人也絕對不可能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