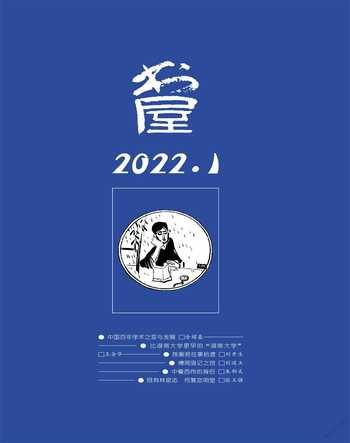程小青的“紳士帽”
劉臻
民國時期雖然與歐美偵探小說的黃金時代在時間上高度重合,但是黃金時代的主要作家卻大都沒有代表性作品被譯介到中國。也難怪姚蘇鳳在《歐美偵探小說新話》(《生活》雜志,第一期至第三期,1947年)中感慨道:“近年來的歐美偵探小說之新作被翻譯介紹過來的,委實太少了。”他進而提道:“在歐美所公認的第一流近代作家中,為什么只有過伊勒萊昆(Ellery Queen)的《希臘棺材》《中國紅橙》……這幾種?……即說上述的……也還是昆氏……的較失敗的作品。”
《希臘棺材》刊登于著名的《萬象》雜志,從第一年第一期(1941年7月)連載到第三年第二期(1943年8月)。此后,由《萬象》老板平襟亞創辦的中央書店出版單行本(1946年12月初版)。而《中國紅橙奇案》(今譯《中國橘子之謎》)則由上海春江書局于1943年出版。此外,埃勒里·奎因(即上文之“伊勒萊昆”)在民國時期尚有一些短篇譯作。而從年代上看,直到四十年代奎因才同中國讀者見面。不過近期筆者的一個發現,使得程小青翻譯的另一部奎因作品浮出水面,并且將奎因被引進中國的時間也提前了若干年。
1936年8月6日,《上海報》上刊登了時任編輯匡寒僧撰寫的《紳士帽前奏——介紹程小青先生的長篇小說》。其中寫道:
關于本報顧明道先生的長篇小說《蓬門紅淚》即將結束,與預備接登程小青先生的長篇小說的消息,已經在上次約略向讀者諸君報告過了。當時,因為篇幅關系,所以沒有作詳細介紹(引者按:7月4日《告讀者與同文》中提及,預備刊登程小青的偵探小說,但是沒有提到小說的名字和內容)。
現在,顧先生的《蓬門紅淚》全部僅余三千多字,不多幾天,就可以刊完了。這里,順便再將程先生的小說向讀者們介紹一下。
程先生的偵探小說,在本報已經登載過兩篇,博得讀者的贊美。所以,我們在顧先生的小說行將結束時,就寫信給程先生,請他再寫一篇偵探小說。雖然程先生教務很忙,但是,不多幾天,就接到回信,很直截地答允了。
這次的一部小說,名字叫《紳士帽》,是一部譯本。原作者是奎寧父子。奎寧父子是何許人,文名如何,在程先生的“引言”里有詳細的介紹。
這里提到的已經登載過的兩篇程小青的偵探小說是《白衣怪》和《活尸》,前者刊登時間是1931年11月1日到1932年8月6日,后者是1933年9月1日(?報紙缺失,不確定開始登載時間)到1934年2月28日。兩篇都屬于霍桑探案中的長篇故事。而所說的奎寧父子自不必說就是奎因父子,從《紳士帽》這個名字也不難讓人聯想到這就是奎因的處女作《羅馬帽子之謎》。
《上海報》是民國時期出版于上海的一份小報,1929年10月1日創刊。由當時蓬萊市場的老板匡仲謀主辦,陶壽伯、王雪塵、匡寒僧等人先后為編輯。該報英文報名為The Shanghai Pao,每日一期,每期出版一張,每張版式定為四開四版(也有段時間增刊至八版,每期兩張),刊載各種政治言論、新聞報道等內容,綜合性較強。日本攻占上海期間,該報受到影響停刊約一年時間,復刊后至少發行至1939年3月31日,其后停刊時間不明。龔建星的《溯影老上海》中提到,《上海報》總發行量約2.5萬份,其中上海1萬余份,外埠1.5萬份。
《上海報》具有一定政治情懷和抱負,提出“監督政府、領導社會輿論、指導建設方針、傳播真實消息”等四大使命。除時評、新聞外,該報也刊登連載小說等文學作品,不少出自名家之筆,如包天笑的《上海的解剖》、海上漱石生的《呆俠》、張慶霖的《捉刀六紀》、紅薇的《顛鸞艷影記》等。
1936年9月1日,《紳士帽》正式開始連載,第一節是《引言》。但是,這篇短小的《引言》卻并非原書的序言,而是程小青自己撰寫的,向讀者做了一些背景情況介紹:
偵探小說在歐美出版界里可說是始終占領著無上的權威,和把握著無量的群眾。自從美國挨侖坡的杜賓創作,繼之以集大成的道爾的福爾摩斯案問世以來,五六十年間,風起云涌,作家輩出,真所謂日新月異。每年出版的數量,如果統計起來,那數字的位置一定會使人眩目。老作家如挨侖坡、道爾、華拉斯輩雖先后逝世,而新興作家繼踵而起的卻不勝僂指。本篇也是新興作品的權威之一,主人翁為奎寧父子。據原序上說,老奎寧名叫列卻,本是紐約警廳的稽查員。他有敏銳的頭腦,堅強的記憶,和透視人類心理的眼光,所以他在任時的光榮的功績,在最近的半世紀中可稱數一數二。他的兒子名叫愛雷,是個偵探小說作家。他有獨特的天才,天賦的直覺和豐富的想象力。老奎寧列卻的克享盛名,一部分就得力于愛雷。他們父子倆合作的案件很多。本篇是他們得意的心血結晶之一,是由愛雷奎寧寫成的。篇中離奇緊張的事實,和勾心斗角的局勢,在偵探小說中是不可多得的。好在讀者自能領會,我用不著這里多說了。譯者附識。
這一連載一直持續了近一年。這期間局面動蕩不安,日軍侵華的腳步越來越快,《上海報》所在的上海和程小青所居住的蘇州(當時程小青在東吳大學附中執教)也未能幸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日本開始準備對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日軍進攻上海,蘇州也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8月14日,《上海報》刊發停刊前的最后一期,頭版頭條是《下大決心保衛上海》,第4版上刊登了《紳士帽》第十七章的開頭。
面對緊張的戰爭局面,程小青舉家倉促離開蘇州,之后歷盡艱辛,輾轉來到安徽避難。根據《上海報》1938年8月2日刊登的《程小青繞道來滬》中稱:“據程君云,去歲日軍在金山衛登陸后,鑒于局勢之緊張,乃拼湊得現金二千余元,一家八口逃難他鄉,先至南潯,旋又至安徽黟縣。當時,因天氣已冷,乃將夏季衣服盡遺于南潯,免得途中攜帶不便。乃不料南潯房屋付之一炬,所有衣服損失凈盡。”根據《程小青生平與著譯年表》,程小青一家離開蘇州是在1937年8月17日。另據1938年5月5日《上海報》刊登的《程小青君來函》顯示,程小青一家于1937年11月11日離開南潯,在那里待了三個月不到。
《程小青繞道來滬》又提道:“當日軍到蘇后,曾赴程宅搜索,得軍帽一只、軍衣一襲、刺刀一柄。日軍乃欲燒屋,然因無火種,故得以保全,此亦不幸中之大幸。”雖然家宅還在,但是早已被洗劫一空,真是有家難回。這期間還出現了藏于東吳校內的數萬言手稿被人無端拿走的情況(《程小青重返東吳》,《晶報》,1938年7月22日)。1938年7月底,時局稍有安定,程小青輾轉來到上海,一邊在上海重建的東吳附中教書,一邊從事創作和翻譯。
大約在安徽避難時期,程小青開始繼續翻譯《紳士帽》。1938年春天,程小青在給《蘇州明報》社長孫籌成的信中提到,曾托人將《紳士帽》的續稿帶到上海交給《上海報》。1938年7月《上海報》復刊,同年9月1日《紳士帽》開始繼續刊登,一直連載到當年11月27日方宣告終結。
程小青在極為倉促的情況下離開蘇州到南潯,又從南潯到黟縣,途中甚至為了方便而盡數丟棄夏裝。可程小青卻帶了這本《紳士帽》的原文書,并且一直掛念將它翻譯完整。這其中固有因為連載任務未完成而抱有的責任心,但是也不可不說程小青對這本書有著特別的喜愛。當時因為刊物的緣故或者譯者本身的緣故,譯文“爛尾”的情況時有發生。《紳士帽》在如此嚴峻的外界條件下竟然得以翻譯完整,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此外,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紳士帽》中的“挑戰讀者”被刪去了。是程小青沒有意識到“挑戰讀者”的重要性嗎?《紳士帽》也沒有翻譯原書的序言,可能程小青將它們都作為J.J.McC插入到作品中的內容而刪去了。可能這時候程小青還沒有閱讀過奎因其他的“國名系列”,不知道“挑戰讀者”是這個系列的主要特色之一。不過,到了后來翻譯《希臘棺材》時,原書中的“挑戰讀者”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了。
還有個問題是,為什么后來這么一部“不可多得的”偵探小說消失在人們視野中,即便在《希臘棺材》和一些奎因短篇都結集出版單行本之后,還是默默無聞地躺在故紙堆中呢?目前還很難回答這個問題。能夠想到的解釋是,或許因為避難離開蘇州的時候,大部分文稿都沒有帶走,之后又因為日軍的搜宅而毀掉了,程小青本人沒有了主要的稿件(只有后來翻譯的少部分文稿),而搜羅完整刊登《紳士帽》的各期報紙也難度很大,所以最終這部小說沒有出版單行本。類似的例子是,1939年3月29日,《上海報》上刊登了程小青的廣告,征求該報上刊登的《白衣怪》和《活尸》的剪報,以及之前出版的單行本《倭刀記》(不知是否成功,但是這幾篇故事后來都收錄進世界書局的霍桑探案叢書)。另一方面,《紳士帽》刊登在《上海報》這樣一份小報上,它的名氣不算大,發行數量不算多,而且也不是文藝刊物,故而鮮有人提到這部奎因的作品了。
盡管如此,通過這次發現,我們知道了奎因的處女作《羅馬帽子之謎》在民國時期有過譯本,而且從目前資料來看,還是奎因首度被引入中國。而這中間又穿插著關于程小青的一段“離奇緊張的事實”,如今看來不禁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