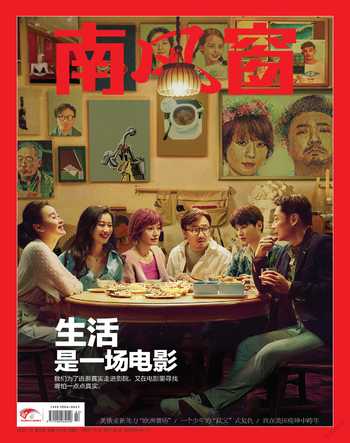同理心與現(xiàn)實(shí)感
董可馨

2022年南風(fēng)窗的新年獻(xiàn)詞,立意是呼吁人們回歸常識,走出偏見的洞穴,得到許多讀者的共鳴。不過后臺也有好多留言問,什么是常識呢?可見大家對此還有困惑。
因此有感于,有必要先來一場關(guān)于回到常識的常識大討論。也就是,討論什么之前,要先定義,否則對話不在一個平臺上,雞同鴨講。爭執(zhí)不休的雙方,雖說很多時候是觀念之爭,可若承認(rèn)觀念也是一種心理現(xiàn)實(shí),就不能輕視了從“現(xiàn)實(shí)”回到常識的難度,說不定大家都認(rèn)為自己才是更接近常識的那一個。
作家阿城90年代時在《收獲》上開了個專欄,名字就叫“常識與通識”。從瘋狂年代走來的人,能切身體會,常識看似簡單普通,卻太可貴了。
梁曉聲在《一個紅衛(wèi)兵的自白》里記,文革時候,紅小兵們盯上了紅綠燈,鬧著要把規(guī)則改為“紅燈行,綠燈停”,因?yàn)榧t燈象征著革命,革命大道寬又闊,怎么能見到紅燈就停下來呢?事情鬧大了,交通癱瘓,最后還是周總理被找來,對鬧事者耐心解釋說,紅燈停是符合科學(xué)原理的,因?yàn)榧t光傳得比綠光要遠(yuǎn),穿透力也強(qiáng),紅小兵這才作罷。有位意大利攝影師老安,80年代初來中國,發(fā)現(xiàn)司機(jī)下意識里還有“綠燈停”的陰影,在擁堵的北京交通中,綠燈一亮,大部分人無法馬上采取行動。可見違背常識的事情不管多么離譜,在咱們這兒曾經(jīng)卻是見怪不怪了。
上面的例子看起來荒謬,但最后也能矯正,尚因?yàn)樗锌茖W(xué)依據(jù),能被證實(shí),總還有個標(biāo)準(zhǔn),可以服人,那些不能證實(shí)也不能證偽的,需要權(quán)衡利弊的,關(guān)涉到不同價(jià)值觀偏好的,要確定常識、走向共識卻并不容易,否則也不會有那么多無謂的爭吵了。
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討論,變成空對空的觀點(diǎn)對罵,雙方誰也不服誰,說起來,也是對常識與常理的理解不同。
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討論,變成空對空的觀點(diǎn)對罵,雙方誰也不服誰,說起來,也是對常識與常理的理解不同,比如瞇瞇眼事件,相當(dāng)部分的人,認(rèn)為瞇瞇眼被商家選擇就是迎合西方對華刻板偏見,是辱華了。對此,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認(rèn)為對惡意的侮辱我們當(dāng)然要回?fù)簦蔷唧w情況要具體分析,也不要輕易和歷史上的“辱華”相提并論,畢竟中國與世界已今非昔比,審美也歷經(jīng)不同年代的變化。
本來,公共事件里,吵吵也無妨,如一位前輩說的,“價(jià)值觀就是用來分歧的”,觀念市場的繁榮,曾經(jīng)還被認(rèn)為是健康的公共空間的基礎(chǔ)呢,可現(xiàn)如今,叫人灰心的并不是觀念的分歧,而是實(shí)質(zhì)的傷害,成群結(jié)隊(duì)的人舞著觀念大棒,真的可以把人社會性杖殺的。
在觀念紛爭中,用常識來校準(zhǔn),其實(shí)是用同理心和現(xiàn)實(shí)感來校準(zhǔn)。失掉了同理心,沒有了現(xiàn)實(shí)感,就容易陷入觀念的迷障里無法自拔。
所謂同理心,是設(shè)身處地地把自己代入那個情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現(xiàn)實(shí)感,是實(shí)際的經(jīng)驗(yàn)和對細(xì)節(jié)的熟悉。英國思想家伯林有本書就叫《現(xiàn)實(shí)感》,他說,使我們能夠洞察實(shí)際的人與物之間關(guān)系的現(xiàn)實(shí)感或歷史感就是對細(xì)節(jié)的熟悉,所有的理論相反地處理的是一般屬性和理想化了實(shí)體,也就是普遍性的東西。
以普遍性來理解事情,容易產(chǎn)生一種“深刻感”,但普遍性的概念和理論的基礎(chǔ)是有特定時空范圍的事實(shí)和細(xì)節(jié),因而有其適用范圍,不是一把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尺子,可以到處衡量短長。
舉例來說,華人曾被臉譜化的認(rèn)識,以一些生物特征為標(biāo)識,這種現(xiàn)象被人認(rèn)識到,提煉出歧視性的“刻板印象”等概念和理論,幫助更多人理解此種現(xiàn)象和心理。可過了這么久,在中國再用它當(dāng)作尺子,無差別地衡量所有那些生物特征,是否也會誤傷到很多人,比如那些專業(yè)的模特。
理論和觀念是幫助人理解世界的,不是代替人來感受世界的,在活得“深刻”之前,還是先活得有同理心、有現(xiàn)實(shí)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