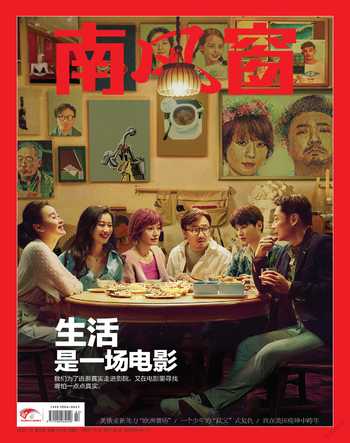拜登為何緊盯供應鏈
雷墨

1月3日,拜登召集了一次農業、肉禽行業的會議,主要談的是供應鏈問題。這是去年12月22日,白宮發布“更公平、更具競爭力和韌性肉禽供應鏈行動計劃”的后續。眾所周知,從去年初夏開始,拜登政府就被國內供應鏈紊亂弄得焦頭爛額。為此,他還在去年10月和12月發表了兩次全國講話。幾乎與此同時,供應鏈問題也成了某種全球現象,成為拉高多國通脹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對于拜登政府來說,供應鏈不只是“問題”,還是正在醞釀的戰略。早在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作為總統候選人的拜登,就在競選綱領中公布了重塑供應鏈的計劃。入主白宮后,拜登在政策調整、推動立法以及外交行為上,都把供應鏈問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拜登曾把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稱為“災難”,認為強化供應鏈才是美國經濟強大的關鍵。入主白宮后,拜登也一直在這個問題上發力。
國內供應鏈出問題,對拜登來說是個大寫的尷尬,但這并沒有改變其政策計劃。從政策思路來看,拜登希望達到的效果是一石二鳥,即一方面強化國內供應鏈,另一方面重塑全球供應鏈。不過,作為“老外交”,拜登的政策重心“本能”地偏向美國之外。美國國內供應鏈緊張得到緩解只是時間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拜登政府在全球供應鏈問題上如何作為。
溯 源
從源頭上看,不難發現供應鏈(supply chain)是個商業或經濟學概念。比如,英文維基百科對它的定義是:供應鏈是一個由組織、人員、活動、信息和資源構成的系統,所涉及的是把產品或服務提供給消費者。“供應鏈活動涉及的是將自然資源、原材料和零部件轉化為終端產品并交付給終端客戶。”
在英文谷歌中檢索相關信息資料和學術文獻,絕大多數內容都聚焦商業領域。學術領域把供應鏈與政治(politics)聯系起來的研究,大多是分析地區熱點對相關行業或企業的影響。即便從權力(power)視角研究供應鏈,主要研究對象也是行業領軍者尤其是大型跨國公司在供應鏈的形成、變遷中的角色,即“企業權力”而非政治權力。
歷史地看,全球范圍內、帶有現代意義的供應鏈,其形成始于1980年代,而美國是主要推動者之一。那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以及其后冷戰的結束,造就了某些學者所說的“超級全球化”。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供應鏈,生成動力主要來自商業,而非政治。
南風窗傳媒智庫推出、2022年將再版的《重新認識美國》一書,對那個時期的世界經濟有這樣的判斷:在那個以自由貿易為導向的經濟體系里,大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通過全球供應鏈活躍在世界經濟舞臺,而國家之手受到規則、制度的約束。
供應鏈在相當長時期里是個“商業概念”,與世界經濟大勢不無關系。而如今經濟全球化遇阻,以及地緣政治的回歸,正在使供應鏈從“商業概念”朝著“政治概念”的方向轉變。這個轉變趨勢,主要的推動者也是美國。
小布什政府時期,供應鏈問題是個很邊緣的政策問題。從公開的資料來看,他執政八年,美國政府沒有發布任何關于供應鏈的官方文件。小布什及其政府高官為數不多的涉及供應鏈的公開講話,主要談及的是如何確保進口安全(尤其是食品藥品等民生商品),以及防范恐怖主義活動對供應鏈的破壞性影響。
供應鏈真正進入政策領域,是在奧巴馬政府時期。2012年1月,奧巴馬政府發布了題為《全球供應鏈安全國家戰略》的文件。這份由奧巴馬簽名的政府文件,正文內容僅6頁,主要涉及如何保護與強化全球運輸、郵寄、海運網絡及其相關基建設施。2015年3月,奧巴馬政府以白宮與商務部的名義,發布了題為《供應鏈創新:鞏固美國小型制造業》的文件(全文22頁),主要內容是如何幫助中小企業適應供應鏈的變化,從而促進就業。
如今經濟全球化遇阻,以及地緣政治的回歸,正在使供應鏈從“商業概念”朝著“政治概念”的方向轉變。這個轉變趨勢,主要的推動者也是美國。
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情況比較特殊,主觀上沒有關于供應鏈的系統性戰略,但客觀上卻將供應鏈問題上升到了戰略層面。疫情暴發前,特朗普政府的興趣是打貿易戰,雖然其主要意圖是平衡貿易赤字,但也有逼迫海外美國企業回流的考慮。這就觸及了全球供應鏈調整問題。疫情暴發后,醫療物資的短缺使供應鏈安全成了異常扎眼的政策問題。而此后經濟復蘇過程中的“缺芯危機”,使供應鏈問題更加凸顯。
特朗普執政的最后一年,美國的政治精英們對供應鏈問題已經形成了共識:美國國內供應鏈出了問題、全球供應鏈對美國不利,而且這些都需要以戰略視角來應對。
轉 變
早在2020年大選期間,拜登就開始醞釀供應鏈戰略。其競選官網上,有篇題為《拜登計劃:建立美國供應鏈、確保未來不面臨關鍵設備短缺》的文章。細讀該文內容,能清晰感知美國在供應鏈問題上態度的明顯轉變。
比如,拜登把供應鏈問題定位為事關國家安全的戰略問題。上述文章寫道:“盡管醫療物資和設備供應是我們最為緊急和迫切的需求,但美國供應鏈危險并不限于這些領域。”文章提到,美國應該解決供應鏈脆弱性的問題,即在關鍵原材料、能源、科技等重要領域對中俄這樣的外國供應者的“危險依賴”。
不僅如此,該文還大致勾勒出后來拜登政府供應鏈戰略的基本輪廓。文中提到的“全政府模式”“綜合應對”“聯合盟友”等,都成了拜登政府供應鏈戰略的核心要件。
最為關鍵的是,把供應鏈戰略與大國戰略競爭結合起來,或者是以重塑全球供應鏈來應對戰略競爭。雖然計劃中不乏關于解決美國國內供應鏈問題的內容,但整體上意圖明顯“對外”,即重點放在海外供應鏈上。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轉變?其中既有國際大環境,也有美國的小環境。而且,這兩種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這種轉變,具有相當的不可逆性。
大背景是超級全球化時代結束,經濟全球化進入調整期。在超級全球化時代,供應鏈上的權力主角是跨國公司。但在進入調整期后,政府尤其是世界主要大國的政府,正在從企業手中收回部分權力,而且是以服務于國家外交或戰略為導向。
在這一點上,美國表現得尤為明顯。2020年2月國會通過的《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同年5月國會通過的《外國公司問責法》,以及2021年4月參議院外委會通過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客觀上都會助長聯邦政府權力的擴張。而這種擴張,是以企業經營權被“侵蝕”為代價的。
另一個原因是政治思潮的變化,導致對供應鏈的認知出現變化。全球化的黃金時代,供應鏈的形成、演變遵循的是“效率”邏輯,即如何讓企業獲得更多利潤。在如今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升溫的國際政治氛圍中,“公平”成了政府決策更加重要的考慮因素。而新冠危機引發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又讓“安全”成了無法回避的問題。這些都已經反映到對供應鏈認知的變化中。
2021年6月,拜登政府公布供應鏈戰略后,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薩梅拉·法齊利說:“數十年來,把勞工視為需要管理的成本,而非需要投資的資產,削弱了美國的供應鏈,侵蝕了工資以及服務于工人的工會使命。”這事實上在告訴美國的企業,別再“效率優先”。而這背后,反映的是政治思潮的變化。
還有一點原因“很美國”:美國深諳“聯結即權力”的邏輯,企圖通過重塑供應鏈削弱對手、強化自身權力。美國歷史學者尼古拉斯·蘭伯特,在一本關于英國金融實力與一戰的書中指出,英國是“聯結即權力”的先知先覺,英國的決策者非常清楚該國的金融網絡對于贏得一戰的作用。
美國學者丹尼爾·德雷納在《相互依賴武器化的使用與濫用》中,把美國稱為將相互依賴武器化的開山鼻祖,最為直接的例證就是美國利用別國對其經濟上的依賴,通過經濟制裁達到外交目的。
目前的情況,正在發生不利于美國的變化。根據相關研究,2001年,與美國的貿易額高于與中國貿易額的國家占比是80%,2018年,這一比例將為30%。美國感受到了危機,企圖通過重塑供應鏈,在重要和關鍵領域施加影響,改變美國在“聯結即權力”邏輯中的不利地位。
當選后喊著“美國回來了”的拜登,是要帶領美國與世界“重新聯結”的。當然,這種聯結絕不是回到過去,而是有選擇地聯結,即重塑全球供應鏈。需要指出的是,將供應鏈視為戰略的思維,肯定比拜登的任期要長,即便拜登之后白宮的主人,是特朗普本人或者特朗普式的人物。
主題是削弱中國優勢
2021年2月24日,拜登簽署行政令,正式啟動供應鏈評估。同年6月8日,拜登政府發布了名為《建立彈性供應鏈、振興美國制造業和促進廣泛增長》的評估報告。自此,拜登政府完整的供應鏈戰略“躍然紙上”。
需要指出的是,將供應鏈視為戰略的思維,肯定比拜登的任期要長,即便拜登之后白宮的主人,是特朗普本人或者特朗普式的人物。
該報告公布之后,輿論和學術界的解讀很多,但幾乎都突出了兩點:這是一項宏大的政治工程;瞄準與中國的戰略競爭。
這份報告長達250頁,與奧巴馬政府時期兩份關于供應鏈的報告(分別僅為6頁和22頁)形成了鮮明對比。
從涉及領域和政策布局來看,與小布什政府時期讓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關注“進口安全”,以及奧巴馬政府時期由商務部牽頭、寄望“促進就業”不同,拜登政府的供應鏈報告主要參與方有商務部、能源部、國防部、衛生與公共服務部(事實上,國家安全委員會、貿易代表辦公室等幾乎所有其他聯邦機構,都有不同程度的參與),聚焦半導體、高能電池、關鍵礦產資源和制藥業,開出的“藥方”幾乎是對美國經濟內在機理與對外關系的重構。
此外,雖然那份報告從標題上看,像是美國想“自我強身”,但字里行間都透露著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報告提及中國(包括腳注)多達458次,而提及國家次數位居第二的日本,只被提及85次。通讀全文不難發現,拜登政府的供應鏈戰略在圍繞一個主題轉,即如何強化美國的優勢并削弱中國的優勢。
目前看來,拜登的供應鏈戰略在布局和實施上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內外聯動。入主白宮以來,拜登的經濟政策很多都帶有“內外聯動”特點,這也符合其“服務于中產階級的外交”之理念。在這一點上,供應鏈戰略體現得尤為明顯。用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學者香農·奧尼爾的話說,“美國的供應鏈就是外交政策”。
在她看來,拜登政府對于供應鏈的評估與重塑,有著“一箭雙雕”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讓美國的供應鏈更安全、更具韌性;另一方面,能夠激活與盟友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奧尼爾分析稱,美國不能單槍匹馬逆轉全球化,也不會追求朝鮮式的自給自足,但可以戰略性地聯結全球供應鏈,重組和分散生產。
從2021年4月16日在白宮接待首位于拜登上臺后來訪的外國領導人(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到2021年10月底最后一輪外訪(出席G20峰會期間召集“供應鏈峰會”),拜登本人及其政府高官,外交議程幾乎都沒有繞開供應鏈問題。
另一點是定向脫鉤。雖然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明確否認“中美脫鉤”,甚至還提“再掛鉤”,但她的指向是貿易,而非供應鏈,尤其是涉及具有戰略意義的供應鏈。無論是拜登作為總統候選人時提出的關于供應鏈的“拜登計劃”,還是就任總統后推出的供應鏈評估報告,都在渲染美國的“脆弱性”,而脆弱之源就是在供應鏈上對中國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