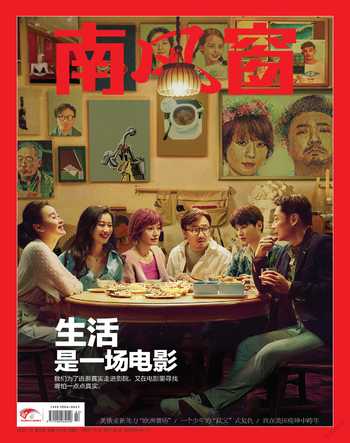一份給予全球勞動者的更優厚待遇
丹尼·羅德里克
過去40年的全球化和技術革新,對那些擁有技能、財富和人脈以把握新市場和新機遇的人來說是個福音,但對普通勞動者來說卻不算是個好消息。
在發達經濟體中,盡管整體勞動生產率有所提高,但受教育程度較低者的收入往往停滯不前。比如,自1979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薪酬增長率還不及生產力增長率的1/3。勞動力市場的不安全和不平等狀況日益加劇,許多社區因工廠關停和就業崗位轉移而遭到拋棄。
在發展中國家,依照標準經濟理論,勞工本應是全球勞動分工擴大的主要受益者,但企業和資本卻再次成為了最大的受益方。即使是在那些由民主政府執政的地方,貿易自由化也與對勞工權利的壓制并行不悖。
而勞動力市場的弊端,則催生了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壓力。最近,經濟學家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記錄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美國男性群體中“絕望死亡”現象的增長。同時有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文獻,將右翼民粹主義在發達經濟體中的興起,與普通勞工優質工作機會的消失聯系起來。
在全球新冠疫情之下,勞工問題正重新受到關注—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勞動者如何才能不僅獲得屬于自己的那一份公平報酬,同時還能擁有為生活增添意義的體面工作?
一種方法是依靠大企業的開明自利行為。快樂且有成就感的勞動者工作效率更高,辭職意愿更小,也更愿意提供良好的客戶服務。
第二項策略,包括提升勞工相對于雇主的組織力量。美國總統拜登明確贊同這種做法,他指出美國中產階級的萎縮是工會力量下降的結果,并誓言要加強有組織的勞工和集體談判。
在美國這類工會力量已被明顯削弱的國家,這種策略對于糾正談判力量的失衡狀況是不可或缺的。但來自許多歐洲國家—這些地方的勞工組織和集體談判能力依然強大—的經驗卻表明,這一補救措施或許稱不上全面。
麻煩在于,強大的工人權利也可能催生一個二元化的勞動力市場—在這種市場中,利益歸于“內部人士”,而許多資歷不夠的勞動者卻找不到工作。廣泛的集體談判和強有力的勞動法規為法國勞動者掙得了許多福利,但該國同時卻是發達經濟體中青年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第三種策略旨在盡量減少失業,即通過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確保充足的勞動力需求。當財政政策使總需求保持在高位時,雇主就會求著工人上崗(而不是相反)且失業率可以保持在低位。但盡管緊張的勞動力市場可以幫助工人,卻也會帶來通脹風險。此外,宏觀經濟政策也無法專門施力于那些只掌握最低技能的勞動者或最需要工作的地區。
因此,第四項策略就是改變經濟中的需求結構,以向受教育程度較低者和蕭條地區傾斜。安穩的中產階級工作的短缺,與藍領制造業崗位和服務部門銷售和文職工作的消失密切相關。政策制定者必須專注于擴大技能分布曲線中段的崗位供應,以扭轉這些兩極分化的影響。
此外,我們必須明確理解新技術是如何幫助或傷害勞動者的,并重新思考國家創新政策。當前的一些理論幾乎只關注應如何重新培訓勞動者以適應新技術,而很少關注創新應該如何適應勞動者擁有的技能。其實,政府政策可以幫助引導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技術沿著更有利于勞動者的道路發展,補全工人的技能而不是取代他們。
歸根結底,提高勞動收入和工作尊嚴,需要加強勞動者的議價能力并增加優質崗位的供應。惟其如此,所有勞動者才能獲得更佳待遇,并在未來的繁榮中取得屬于自己的公平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