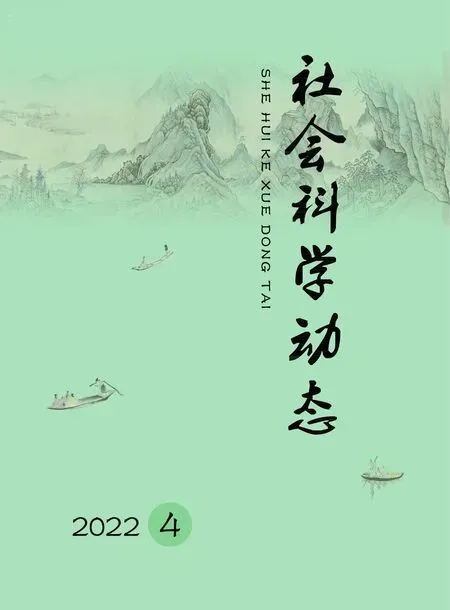存在、呈現與生成:文學意義的語境論表征
徐 杰
當閱讀文學作品時,我們獲取的與其說是文學的文本還不如說是文學的意義。那么究竟什么是“意義”?文學作品的意義與文學語言“意義”是相同的意思嗎?“文學意義”又意味著什么呢?“文學”作為學科知識譜系之中的一種,在整個社會或者人生之中呈現和建構著“價值”,即學者南帆所認為的:文學具有不同于物質生產維度的“意義生產性”。同時,“文學意義”還起源于另一層面的思考:我們讀文學作品,到底讀到的是什么?“意義”這個概念,在語言學之中是與“語境”作為互相綁定的一個概念。從文學語境角度來思考文學意義,就帶來一系列全新的問題:文學意義是從哪兒來的?文學意義又存在于何處?封存于文本中,還是讀者的賦予?是固定的還是流動的?文學語境與文學意義的關系如何?
一、關系性存在:從“意義”到“文學意義”
在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之后,“意義”由于與語言的內在關聯而成為理論界的核心話語和范疇。“意義”是什么?它怎么產生的?這些問題隨著不同文論家關注維度的不同,其涵義差異較大。胡塞爾現象學關注主體的意向活動,認為意義存在于主體的意向性之中。如,樹可以被燒掉,但是對樹知覺的意義不能被燒掉。對象意義產生的過程是主體意向“給定性”的過程。①這直接帶來文論之中的文學“作者論”或“作者意圖”論:作品是作者的孩子,作品的意義根源于作者。后來,索緒爾語言學轉向,將“能指”的意義束縛于“能指”與“能指”之間的“關系”中。文學理論隨之將關注點轉移到文本內部:文學意義產生于語言和作品之中。比如,新批評認為意義來自“張力”、“復義”和“反諷”等,結構主義認為意義來自底層結構和表層現象的關系。維特根斯坦從語言圖像論轉向語言游戲論時,文學意義從之前的“文學世界的賦予”,轉而成為世界之中的“實踐”和“使用”。當哲學“主體間性”理論的興起,文學意義又被視為“說話者和聽話者的關系”。②難怪瑞恰茲在其著作《意義之意義》中對意義的定義,其中主要包括三個維度:將意義視為“一種內在品質”、“詞的內涵”和“一種本質”;將意義看作“投射到對象上的一種活動”(意向)、“任何事物引發的感情”;將意義作為“符號使用者應該在指稱的東西”。③
語言學轉向之中,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傳統意義的理解進行了批判,它認為,意義并非“自然的”、“確定的”和“共享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秉持語言與世界之間的割裂關系,其基礎來自于“能指”與“所指”的任意性,“能指”與“能指”的區別性之中。語境論認為語言意義并非來自能指之間的差異性,也并非來自共時語言在個體語言使用者身上的具體性,也就是說,它并非像一本本字典分發給每一個人。恰恰相反,語言來自每個個體在具體情境之中的反復使用,最后歸納成為一個語言系統。按照洪堡特的說法,語言與人類精神、生命感受之間有著內在的、密切的關聯,而非任意性關系。
語言作為一種實踐而非作為一種客體。如果遵循結構主義語言學,我說“把門關上”,這句話的意義獨立于我的內心想法和意象,僅僅是語言本身的功能,而不是來自心靈。但是正如伊格爾頓所說,如果我讓被綁著的你去關門,或者去關已經關上了的門,你會問“你是什么意思?”。這個問題針對的不是這句話本身,而是主體的意向。語言是一種實踐而非客體。④巴赫金則認為語詞的全部意義并非固定在某個詞語符號之上,因而對語詞的理解表面是理解符號的意義,深層則是通過符號媒介進行對話的主體之間的意義傳輸。杜威也認為語言本質不是對既有的對象的表達工具,而是在社會關系之中塑造人們思想和意義的力量。即語言并非鐵板一塊地存在,而是各種異質的行為、意識的“對話”和“交往”。奧斯丁的語言行為理論認為,語言并非都是描述事實,也不完全是對內心情感的表達,語言還可以“做事”。語言的“行事性”就是通過語言來完成某個事情,比如,婚禮儀式中的語言“定事性”:“我特此宣布汝二人為夫妻”。“對話”與“行為”理論皆是以對語言意義實體論的反駁,走向關涉意義主體和社會文化的語境論。
赫施提出“作者意圖”理論,為文學作者保留了位置,他認為文本的“含義”來自作者。我們知道,存在于腦子里,尚未形成作品的“意圖”是一種混沌,尚未明晰成形的意向性而已。只有經歷語言的“洗禮”,“意圖”才能成為“意義”。換句話說,語言對人的想法和感覺具有“固化”的作用。按照柏格森的說法,我們對于外在事物的印象、感受和情緒是混亂的、流變的和不可言狀的;我們只能用公共形式(語言)將這種私人意識狀態套住,才可將其變為明晰的。在文學創作經歷之中,無數的作家就描述過這樣的創作感受:小說是寫出來的,而不是想出來的;只有將模糊的想法落實到筆端形成文字,才會明白腦子里想的內容和筆下的文字有著多大的差別。語言文字自身作為主體精神的外化具有客觀性,會裹挾和改變作家的創作原初意圖。正如帕烏斯托夫斯基所說,人物會反抗甚至改變動筆之初的預設提綱,而作家有時毫無辦法。⑤在此,我們便產生一個疑問:文學語言的意義與作者的意圖等同嗎?答案是否定的。語言就具有“公共性”或“社會性”,即所有的人都遵循的同一套符號規則,且規則相對穩定。因此,作者尚未形成文字的意圖或“私人語言”,一旦被公共語言過濾和洗禮,意圖已經不再是作者原初意義上的了,而是被融入了整個文化系統的意義網。故而,作品的含義必然不同于作者的意圖。所以,伽達默爾干脆提出,文學的意義不是來自作者的意圖,也不是來自文本自身,而是來自解釋者所處的整個歷史語境對文本的賦予和投射。
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文論倡導文學意義本質上是“文本意義”:文本意義是與作家和讀者沒有關系的內指性意義。⑥這種文本意義只關注文本作為客體的本質,而不關注文學意義與世界情狀的關系。“形式”和“結構”是他們關注的中心;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文學性”是他們尋求的本體,“語詞作為語詞而被接受,而非僅僅只是所指代客體的代理人或感情的迸發;在于語詞及其措置和意義,其外在和內在形式都要求其自身的分量和價值”。⑦意義不再是語言之外的現實生活的組成,而是語言自身的一部分。就像保羅德曼所說,文學意義變成語法意義和邏輯意義,文學意義之中的“意義體驗”被排除,比如“作品由于投入而與讀者的人生感、存在感相通連,直接融入并構成讀者的人生體驗、價值觀照和精神生命的一部分”⑧。因而,“文學意義”不僅存在于文學語境的“作品語境”層面,還要復歸于主體維度的“情景語境”層面,更要滋生于“超主體”的“社會—歷史語境”。故而,筆者以為,文學意義應該是從文學的“作品語境”到“情景語境”,再到“社會—歷史語境”的互動關系性之中產生的。
從對意義理論流派的爬梳之中,我們發現,關于意義思考存在兩種極端的想法。第一種,語言孤立論。語言的意義內在于語詞自身,即孤零零的一個詞語依然可以被人們理解。第二種,語言語境論。語言的意義完全是從語境之中獲得的:語詞是一個空架子,它固有某種意義是一種虛妄;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意義是千差萬別的。對于此爭辯,我們首先拎出語義學之中的“折衷派”思路。“折衷派”清晰地區別了“字面義”(含義)和“使用義”(涵義)。“含義”像字典一樣客觀固定不變,可做真假對錯的判斷。“含義”是事物的性質,如“單身漢是未結婚的人”。但是,“涵義”是在語境之下產生并發生變化的,非事物本身屬性。故而,沒有真假的判定,如“這個離婚男人是個快樂的單身漢”。也就是說,意義之中的“價值判斷”不能用于“事實判斷”,反之亦然。
這種意義“二分論”并不能讓邏輯經驗主義者信服,奎因和維特根斯坦堅決反對有“含義”的存在,甚至認為所謂內在于語詞的“含義”(字面義),本身也是在語境中抽象出來的。“客觀意義”是作為語境使用和歸納而存在的。奎因認為,meaningful讓人誤以為有一個客觀的意義(meaning)的存在,其實語言的意義并非客觀實在地存在于詞典之中。如果我們相信“單身漢”的意義即“未婚男子”是因為詞典里如此寫著的話,這無異于我們生活的種種情況都必須通過詞典來進行意義解釋。殊不知,詞典編者恰恰是根據生活之中的詞語使用語境來編寫其意義的。⑨因而,意義不是固定客觀地存在著的,而是在使用之中產生一種隱喻式的“同一性”,從而給人以意義是一種實體的錯覺。就像巴爾特認為作為語詞的“埃菲爾鐵塔”,其意義是空的,但是被不同時代無數的巴黎人加入了“巴黎品質”,因而具有了巴黎的象征意義。⑩意義的爭辯有點類似柏拉圖“從理念到事物”,和亞里士多德“從事物到本質”的論爭,即“共相”和“殊相”之爭。到底世界的真實存在是以“共相”為基礎,還是以“殊相”為根本?如果意義是客觀的,它一定先在地確定了自身所有的使用方式;如果意義是語境性的歸納,它就只存在于使用過程之中,并且所有的確定性都是暫時的,意義的“殊相”會不停地流動和變化。這就是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語境論”:意義不可能本質化和心理化,只能存在于反復的使用之中。
當然,這種思想也遭到了質疑:我們對意義的把握是瞬間完成的,而使用則是在整個時間之中都遍布著,所以意義不可能慢慢悠悠地在使用之中產生。如,別人對我說“立方體”,我們直接知道的是意義而非關于它的全部。維特根斯坦反駁說,“語義本質主義者沒有任何根據來這樣說:在‘立方體’這個詞跟世界中的對象聯系起來的無限多方式中,某種一種方式是正確的”1?,但語言的使用者可以在無數次的使用訓練之中正確運用符號。因而,語詞向我們呈現的意義即便是瞬間的事情,但是它已經內在地包含了反復的使用過程。難怪利科認為,語詞只是一種“潛在意義”?,語詞的意義本身就是來自其語境性的使用,字典的“歸納”和固定依然鎖不住語詞意義的“增殖”和“流動”,這其實就是意義來自語境的有力證明。所以,語言意義從意義實體論轉向了語境論。可以說,意義是一種關系性語境的產生物或者生成品,并非一種內在于語詞的客觀實體。戴維森的語境主義走得更為極致,他強調:其一,符號沒有本質,只有被安置到某一語境的能力;其二,符號的意義是由它的語境所決定的;其三,沒有最終語境,或者說沒有所有語境的語境(context of all contexts)。?意義從本質論走向語境論,對于文學意義來說又意味著什么呢?
受意義語境論轉向的啟發,我以為文學意義并非類似實體一樣的對象存在的,而是一種文學語境各要素關系之中的生成物。人類所有的語言都有自己的意義,這種語言的意義以一種原初狀態成為文學意義的起點。在對一般語言意義上的文學文本理解基礎上,才能在文學語境之中獲得更高層面的文學意義。難怪赫施將作為一般語言層面或者符號層面表達的東西稱為“含義”,認為它來自于所要表達的事物中:“意義則是指含與某個人、某個系統、某個情境或某個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間的關系”。?“含義”和“意義”的區別就是在意義內在論和意義語境論之間的劃界。
二、動態性呈現:舒茨現象學視域下文學意義的語境層域
文學語境對于文學意義來說,具有明晰性和多義性的悖論性效果。文學意義產生于限定性的語境,這減少了文本的誤解,增加了意義的明確性和清晰度。但同時,文學在不同的文學語境之中具有多義性,且這種多義性恰恰不能也不必要祛除。意義的游走性增加了文學的可琢磨性,即意味。筆者認為,文學意義的悖謬來自于“文學意義”概念使用的模糊性和“文學語境”范疇應用的“非分層性”。從廣義上說,“文學意義”包含兩層:文學意義和文學意味。文學意義是具有明晰性和可言說性的存在,它主要取決于文學的情景語境層;文學意味具有模糊性和不可言說性,它來自于文學的“社會—歷史語境”層。
文學意義的明晰性和可言說性,來自文學主體意識的反思性和情景語境的具體性。從現象學角度來說,文學意義來自于主體的意向性與對象自身條件的耦合。比如“鴨—兔”圖,主體帶著什么樣的理解和預設,圖像就為其呈現什么圖景。這就好比中國文化之中“象”與“像”的區別:“像”是一種自然和客觀存在的圖景或現象;“象”則是外界的“象”在內心之中呈現出來的心像,具有主體對對象的精神性滲透和主觀性建構。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意義的客觀性和靜止性是一種虛妄,它一定來自非文學的主體語境的意向性。當然這種意象性如果僅僅停留在“體驗”層面,文學意義依然不能產生。對于“鴨—兔圖”,維特根斯坦指出,“我看到這個東西”是一回事,說“我把這個東西看作……”是另一回事。?那么,“看到”是一種體驗;“看作”則是思想和體驗的混合體。體驗處于一種沉浸狀態之中,而“看作”從內在沉浸中反身出來,讓詞語意義和想象的多義之間具有相似關系。故而“看作”就成為了一種行為和活動。在這種語言活動之中,語詞的意義不是來自本身,而是來自主體情景語境。也就是說,對文學的“體驗”并不能產生意義,意義生成于“反身而思”之中。舒茨從胡塞爾現象學角度來思考“體驗”與“意義”,他認為,體驗是一種意識的體驗,而意識又是綿延的。因而,沒有所謂的“一項”體驗,只有從體驗之流之中通過反思將某部分截取出來進行關照。人類追求意義的根源來自于人天生的意識,意識之流在理性維度只能通過反思才能被把握,故而表述為體驗、生成意義;“正在經歷”的體驗雖然有意向性,但是其處于意識流程之中,不能被“理解”、“區分”和“凸顯出來”,故而并不構成意義。故而文學意識的反思性成就了文學意義的清晰性和可言說性。
文學情景語境于舒茨的“社會的周遭世界”,它在一種具體性(當下性、共同性和直接性)之中與文學文本發生意義關系。情景語境之中,主體根據當下的、具體的與個人化的文學“經驗”,在文學文本的寫作和閱讀之中,對所有的文學語言進行了一種“賦義”行動。這種“賦義”擴充、改變甚至決定著語言曾經和現有的“公共意義”。因而,這種作者的“意圖”(非“意義”)和讀者的“感受”融合為文學意義的情景語境。同時,情景語境是主體共同和相同的享有性。世界是我們共同的世界,非個人的私人世界,共同體驗是互主體性世界的前提和保障。?這種文學主體之間的共同性,使得文學意義的維度具有凝合性而非分散性,故而文學意義具有明晰性。清晰性還體現在周遭世界的情境中我與你的“同步性”。即便我無法真正體驗到你的體驗,但是當我們共同面對小鳥飛翔時,對我來說“你”的生命流程與我的生命流程同步前進著,正如同對“你”來說我的生命流程與“你”的生命流程同時前進著一般。?所以,在共同面對文學作品時,“我還能在想象中將一些歷史人物的心靈放在和我宛如同步的情境里,經由他們的著作、音樂與藝術來理解他們”。?
文學意味的朦朧性和不可言說性主要從文學的“歷史—文化”語境之中生成。文學和藝術的不可言說性,主要是相對于文學意義的可言說性來說的。藝術能被我們感知到,是因為它通過語言向我們敞開;而藝術還存在于不可言說的狀態之中,“每件藝術品,即使是一首詩,也存在于另一個空間中,在那里它沒有意義——并且連意義這個概念也沒有任何意義了。只要它存在于這個空間,在這個‘非制作的’空谷中,藝術作品就是難以言說的,但這并非異乎尋常。因此,當我說所有的藝術媒介都是語言時,僅僅是因為語言將一切事物都理解為語言”。?奧爾布賴特從媒介角度區分文學與語言之間的差距,并為文學劃定出不可言說的領域。這塊空域與可言說部分,構成意義的賦予關系。一般意義上說,差異性的文學語境必然賦予文學文本不同的意義,這使得文學具有意義的不確定性。但是,文學意義的“不確定性”并非文學意義的“不可言說性”:“不確定性”是從文學意義的動態角度來看的;“不可言說性”是從對文學意義的超越性角度來說的。筆者認為,讓語言呈現文學感覺的地方,不是已經說出的文學“意思”,而是尚未說出的文學“意味”。就像海明威的小說,在骨頭一樣的文字下面,可以回味出比肉還有味的東西。“未言明”性成為文學的“意味”,而非僅僅是赫施所說的“意義”和“含義”。這種“意味”與中國傳統文論之中的“意境”、“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和“韻外之致”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與蘇珊·朗格的文學內涵的“不可言說性”以及克萊夫·貝爾的“有意味的形式”等,在審美意義生成機制上具有相似性。具體來說,“意味”作為文學意義,可以用朱光潛先生《談美》的例子來說明。他舉例談到唐代溫庭筠《望江南·梳洗罷》中的兩句詞,“斜暉脈脈水悠悠,過盡千帆皆不是”。一個人在期待心中的有情人歸來,從早晨一直到夕陽西下。望著遠方的帆船,每一艘船都去仔細辨認,可是都不是那個“他”——詞人的深情在“千帆”中,在字里行間里蕩漾開來。但是,詞人最后一句“魂斷白蘋洲”,把這種“未言明”的感覺說破了,詞的意味蕩然無存。
筆者以為,文學的“社會—文化語境”近似舒茨的“社會的共同世界”。在“社會的共同世界”中,人并非作為具體化的狀態的存在,而是以理念型狀態產生意義。具體化的人有自己的所思所想和個人特點;理念人只是一個“郵政人員”和“警察”似的、重復相同行為模式的類型化“幻影”,而非活生生的人。我們不能經驗到作為個體的人,而只能是“你們”——“類型化”的理念人。
其一,文學“社會—文化語境”不是單數的“語境”,或者此時此刻的當下語境,而是一種“語境群”的疊加和融合。這種“語境群”并非理論上的無數情景語境的總和,而是情景語境將個人化、具體化和生命化的部分隱匿起來,只剩下“理念型”的語境或者“共同世界”式的語境。所以,“社會—文化語境”對于文學來說,并沒有時間和空間上的直接性,只有間接性。在這層語境之中,我們并不能直接經驗到作為個體的文本所面對的情景,因為文學“社會—文化語境”是一種“理念型”的語境,是“文本群”對“語境群”的關系。
其二,文學“社會—文化語境”是一種客觀確定的、具有模式化內容的、具有公共性的“語境群”。文學“社會—文化語境”不是“你”的語境,而是“你們”的語境。好比“明月”這個文學符號意象,它具有跨地理空間性和跨歷史時間性,因而在中國的歷史文化語境之中必然地和思念人和懷念故鄉相關。在“社會—文化語境”之中,我們互為“理念型”的人。所以,在情景語境之中的、具有不同生命意識狀態的人是不可能互相融為一起的。但是,在“社會—文化語境”之中,“你”不是真實的人,而是類型化的人;我們彼此采取的是“朝向你的態度”,彼此是“他們中的一個”。反過來,“我”也不被視為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種“他們其中之一”。故而,“社會—文化語境”對于主體的情景語境具有最大公約數的性質,這使它自己具有跨越主體之間的體驗差異的共同性。
其三,文學“社會—文化語境”具有時間縱深感和空間無限感,可以達到“回味綿長”的文學意味之感。關鍵是這種文學意味并非只有一個人能感受到,通過文本和情景語境的分析,相同文化之中的個體都可以以一種“共同體”狀態體會得到。文學的意義在不同的語境之中,可以是有連貫性或者斷裂性的,而這取決于文學語境關聯度以及語境關聯的個人化還是集體化。
文學“社會—文化語境”與文學的非文學語境(歷史、文化和社會)之間存在模糊的界線。文學意味的不可言說性或者說“不盡之意”,恰恰來自于非文學語境向文學語境的動態生成過程之中。這種生成過程是語境內和語境外的意義,以隱喻性或者相似性的方式相關聯。文學意味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是一種持續性地產生新義的狀態。文學意味可以不斷被主體回味,并且每一次的琢磨都會有不同的感覺和意義。故而,從邏輯上可以判斷,如果是固定的文學語境,其意義只能是同一性的和靜止的;如果文學意義要產生“不盡之意”,那么其所處的語境一定是不斷流動的。我們知道,從一個點(具體作品)出發的語境是相對確定的,就像靜止站立的人所見的視野一定是確定的。不管作品還是語境自身的運動,都會產生全新的意義,并且是源源不斷的。一部文學作品本身作為語言和文字的集合體,它是不會發生變化的,會變的只有文學語境。從此作品出發,相對確定的文學語境被語境外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因素介入時,已有的文學語境被不斷擴充,文學意義則變成每一次全新的體會,都有新意味的感覺。
三、整體性生成:文學語境與文學意義的共在
傳統文學觀認為,文學通過語言表達思想和精神,即意義的維度。語言學轉向,讓我們意識到:語言不是意義傳達的工具,相反,語言是決定意義的本體。“精神存在在(in)語言之中而不是用(through)語言傳達自身。……這意味著它不與語言存在外在的同一。只要精神存在能夠傳達,它與語言存在就是同一的。”?外在事物并不給予我們以意義,除非通過人的語言。人按照自己的語言給事物命名,這種命名過程將萬事萬物帶入了語言的世界之中。“只有通過萬物的語言存在,他才可以超越自身,在名稱中獲得關于萬物的知識。”?事物被語言化,同時人存在于語言之中,故而,人通過萬物在語言之中傳達著人的精神和意義存在。語言的存在與意義的存在是同一的。本雅明的語言存在論讓我們明白語言和意義的同一關系或者本體關系。那么,語言又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呢?后期的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并非世界圖景的描摹,而是在一種“使用”情境之中產生和存在的。當然,其意義必定是一種語境性存在;不存在抽空的、純粹的和非可表達的意義。
弗萊將語言分為“內向型”和“外向型”語言:前者與外部事物是描述性或論斷性的對應關系,其意義在于其對外部事物表征的精確性和真實性來判斷;后者作為純粹的內指性語言,只在文本和文本之間產生關系,依靠文學語境完成自我意義生成。弗萊認為,在“向心”的角度上,文學文本是一個自我不斷生成的“關聯域”(即語境)的存在,因為文學詞語意義是含混的、多義的和可變的。一般來說,詩歌不是理性地對外界事物進行描述和模仿,而是對情緒和感情的描繪以及表達。在象征主義詩歌看來,情緒只是走向明晰感情的某個階段。故而,在談及文學的“程式化”時,弗萊更多地是站在“詩歌具有獨創性和原始性”這種觀點的對立面,他認為詩歌是語言語境之中的產物,而非脫離已有語境的奇思妙想。“新詩,就像新生嬰兒一樣,誕生于已經存在的詞語序列之中,是它所依賴的詩歌結構的典型。……詩歌只能產生于其它詩篇;小說產生于其它小說。文學形成自身,不是從外部形成:文學的形式不能存在于文學之外,就像奏鳴曲、賦格曲、回旋曲的形式不能存在于音樂之外一樣。”2○同時,文學意義的自我語境建構性還表征為一種時空整體性。在《批評的剖析》中,弗萊將文學置于音樂和繪畫的交叉點上進行思考,認為音樂按照時間“節奏”復現,繪畫按照空間“布局”展開。但是藝術都同時具有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不同的藝術差異在于某方面更為突出。由此,弗萊將音樂和繪畫各自側重的維度結合起來,對詩歌文本進行審視。“當詩從頭至尾移動的時候,我們在聽詩;但是當它一旦作為整體進入我們頭腦中時,我們便立即‘看到’它的意思。更準確地說,所反應的不只是整首詩,而是詩中所包含的整體性。”?這與語境論不謀而合。語境詩學認為,我們是從整體上感知整個作品的,每個文學字符之間的意義是互相滲透的;后面的語言總是覆蓋到前面語言的意義之上,以整體姿態呈現給我們的。無論是在文本間性的維度,還是在文學媒介屬性的維度,文學意義的生成都是對語境的證明。
即便語言作為一種本體存在時,文學藝術的意義難道只能束縛于語言內部嗎?答案是否定的。文學作為一種語言的理解,與將萬物作為一種語言來把握,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思考。弗萊將文學意義確定為“內向型”語言維度使然,并將文學形式(技術)之間的互鑒性與影響性作為文學的本然。萬物作為一種語言的存在,就意味著文學意義還來自文學文本之外的情境之中,即便情境中的眾多事物都是以語言存在被主體把握的。以現代藝術為例,現代藝術特別注重在空間上凸顯藝術語境的位置,比如實在主義藝術,其藝術情境就是一種空間關系。傳統理論認為藝術的意義內在于作品內部,而實在主義藝術則將其自身價值置于關系情境之中。在情境之中,空間、光線和參觀者都是一種語言存在,但是其語言性與藝術作品符號的語言性是區別性和斷裂性的異在關系。情境在藝術之中逐漸提升自己的地位,降低了作品的地位。對藝術的審美和感知,逐漸從波蘭尼所說的“焦點覺知”逐漸走向的附帶覺知,也從在場之物走向了不在場的存在——情境本身替代作品成為審美對象。對事物的感知必須在整體情境之中完成,物是情境的一部分,其物性在情境中確立。?因此,文學和藝術的情境語境同樣生成和生產著藝術意義。
文學語境生成著文學意義,同時文學意義反過來創造著新的文學語境。生活世界離不開意義,文學通過意義生產加入意義整合和搏斗的交織之中。?一旦文學內置在生活世界之中,與之產生意義關聯,生活世界就成為文學的語境:文學意義從之而生,為之而動,成之一體。文學意義除了存在于文本符號形式層面和作品周遭的物性情境,還生成于與人所內居的生活世界勾連的公共語境中。文學作品通過公共語境生產著意義,而不僅僅被動接受著公共語境的意義“填充”。文學作品對公共空間具有介入性,使得文學的意義在公共語境之中得到增殖。繪畫、雕塑、音樂等藝術的公共性主要發生在物理的公共空間之中,如廣場、公園、街道、綜合商場等地點。這些藝術門類所依賴的媒介載體,以固定化或物質化的方式將其自身呈現出來。在傳統意義上,文學的介質是語言和文字,通過印刷術而被規約到紙質文本之中。書籍少有將廣場和公園這種物理空間作為展示自己的主要舞臺,但是,它可以存在于所有人類能存在的空間之中。原初人類洞穴之中所講的神話、古希臘雅典廣場上高聲吟誦的詩歌、17至18紀法國貴族的閱讀沙龍、手捧著另一種語言翻譯過來的文學、現代地鐵上上班族通過聲音聆聽的網絡小說、莫言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學術團體的文學批評等等。所有這些情狀形成一種“氣氛”,文學在物理空間、文化空間甚至心靈空間里無處不在。由于語言較之于顏料、石材和鋼琴等介質更為自由,同時人類普遍地、靈活地使用著語言,文學通過受眾具有公共空間的介入性。但此時,只能說文學具有一種社會性。社會性不等于公共性。為什么呢?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即便一個人在絕對私密的空間之中,他“使用的工具、語言、他的經驗等等”都是社會歷史給予的。?公共性除了涉及人行為的“社會性”,更重視主體對公共空間意義建構的主動性。因此,只有當文學作者、文學作品和文學讀者介入外部公共空間,為公共精神狀況、時代道德風尚和公眾政治訴求等等進行把脈時,可以說它才真正具有了一種公共性。我們這個時代,人們進入公共空間主要是通過媒介以及媒介的視角,“公共領域的實在性依賴于無數視角和方面的同時在場”。文學作為視角之一,其公共性是怎樣存在的?“文學并不是政治學的例證或者社會學的圖解,文學制造的審美歡悅形成了公共領域獨一無二的聲音。”?文學可以形成自己的公共空間,在總體公共空間之中生產審美的意義。學者趙勇認為:“所謂文學公共性是指文學活動的成果進入到公共領域所形成的公共話題(輿論)。此種話題具有介入性、干預性、批判性和明顯的政治訴求,并能引發公眾的廣泛共鳴和參與意識。”?所以說,文學的公共性使得其對現實和政治具有一種審美式的塑造或介入的作用。文學所產生的“共通感”,使得意識形態試圖達到的“想象的共同體”得以加固,因為“體驗、理解現實生活,想象、憧憬理想生活,構建人類整體生活目標,建立人類自由的公共層面,是敘事的基本功能”。?文學不是純然抽空的對象,它存在于公共空間的其中一個視角之中。公共空間依賴于無數視角和方面,意義也是在多視角下得以生產和增殖。那么,文學意義的實現就不僅僅來自文學作品內部或者創作者,來自文學文本語境和文學情景語境。文學意義還來自此公共空間之中的其他話語,并且與這些話語形成“操控、被操控或同謀的關系”。?同時,當文學知識譜系被福柯的“話語”透視后,文學必然被視為一種滲透著公共空間話語的符號集合。文學脫離開自為存在的力量,以意義生產為基礎解釋和建構著世界。文學通過審美方式對社會、歷史和文化進行著價值反思,對人類本體意義上的生存困境進行著意義思考、創造和生產。
結語
當印刷媒介替代口語媒介成為文學存在的主要形態之后,我們成為紙媒文學的“土著”,將文學視為紙質媒介呈現的對象成為理所當然。因而,文學意義在媒介偏向影響之下有著實體化傾向,也即是說,文學意義被理解為先在地封存在文本之中的。語境論以關系性的方式將實體意義拉到真實的狀態之中。不僅如此,語境論更適合對口頭文學的活態性進行闡釋,也能對數字媒介文學之中以語—圖方式進行語境重構的現象作出理論反應。舒茨的現象學社會學理論提出的“周遭世界”與“共同世界”理論,為語境層域理論注入了社會關系的維度。這為文學意義天生存在的悖論(明晰性與模糊性)提供了理論支持。在語境詩學之中,語境與意義的關系,并非從上到下的單向關系,而是平等的“互嵌”關系。意義的整體呈現就意味著作品與周遭環境的同時顯現,并非是一種前后或表里關系。故而,意義與語境是互相成就、互相生成的。
注釋:
①③趙毅衡:《意義的意義之意義:論符號學與現象學的結合部》,《學習與探索》2015年第1期。
②汪正龍:《文學意義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9頁。
④ [英]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頁。
⑤ [蘇]康·帕烏斯托夫斯基:《面向秋野》,張鐵夫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頁。
⑥周憲:《從文本意義到文學意義》,《求是學刊》2015年第5期。
⑦ [美]V·厄利希:《俄國形式主義歷史與學說》,張冰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74頁。
⑧吳興明:《視野分析:建立以文學為本位的意義論》,《文藝理論研究》2015年第1期。
⑨李國山:《意義是實體嗎?——奎因的意義理論探析》,《哲學研究》2005年第3期。
⑩趙毅衡:《形式之謎》,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頁。
? [美]J·J·卡茨:《意義的形而上學》,蘇德超、張離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頁。
??保羅·利科:《活的隱喻》,汪堂家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292頁。
?宮銘:《經驗與語言——使用主義文學理論轉型研究》,北京大學2011年博士論文。
?[美]E·D·赫施:《解釋的有效性》,王才勇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7頁。
???[奧]阿爾弗雷德·舒茨:《社會世界的意義構成》,游淙祺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37、228、144頁。
?[美]丹尼爾·奧爾布賴特:《繆斯之藝:泛美學研究》,徐長生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8—9頁。
??[德]瓦爾特·本雅明:《寫作與救贖——本雅明文選》,李茂增、蘇仲樂譯,東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4、7頁。
??[加]諾思洛普·弗萊:《批評的剖析》,陳慧等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97、69頁。
?[美]邁克爾·弗雷德:《藝術與物性——論文與評論集》,張曉劍、沈語冰譯,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頁。
?王偉:《文學:日常生活與意義調配》,《文藝爭鳴》2011年第1期。
?馬俊峰:《語境、視角和方式:研究“公共性”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7期。
?南帆:《文學公共性:抒情、小說、后現代》,《文藝研究》2012年第7期。
?趙勇:《文學活動的轉型與文學公共性的消失——中國當代文學公共領域的反思》,《文藝研究》2009年第1期。
?駱冬青:《小說敘事的公共性與政治美學意蘊》,《江蘇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王熙恩:《文學公共性——話語場域與意義增殖》,《黑龍江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