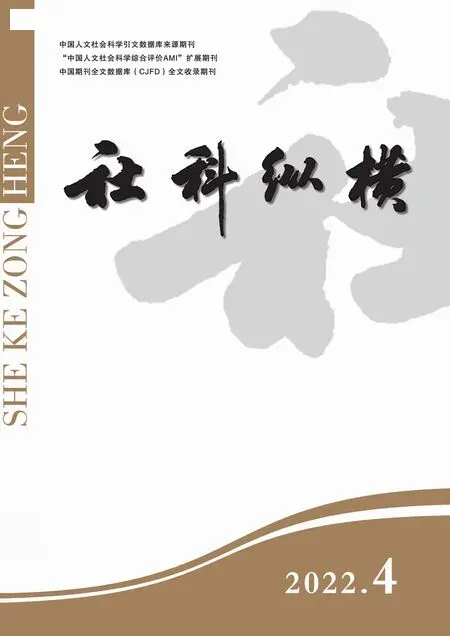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理論基礎、歷史進程與世界意義
段晶晶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 北京100081)
現代化作為世界歷史的必然環節,是世界各國發展的總目標。在“人類和地球的歐洲化”[1]成為世界歷史的主導邏輯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無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2]。從學理上深入考察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基礎、歷史進程、世界意義,對更好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可行性、時代性,從而更好地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
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包含著對現代化的診斷、批判和超越,對中國的現代化探索具有指導和啟示意義。
(一)現代化是世界歷史的普遍規定
在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中,“現代”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時間概念,而是一種社會歷史的時間概念,是社會變化的一種概括性區劃。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等論著中,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指出,以蒸汽機為代表的工業革命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時期——現代時期。在這個新時期,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3]405。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所指稱的“現代”特指“資產階級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實現了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變,推動了人類文明的整體進步。“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3]404這里馬克思恩格斯以氣勢磅礴的語言描述了資產階級開辟的現代化的進步意義:現代化是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的過程,代表著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是所有民族國家都無法避免的歷史命運。
(二)資本主義只是世界現代化的“階段性重合”[4]
在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積極作用充分肯定的基礎上,馬克思還深入研究了現代化的動力問題,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的核心問題。馬克思用生產方式這一科學概念闡明其社會發展理論,并據此分析現代化的動力問題。在他看來,生產力的發展所造成的生產方式的變化是劃分社會發展階段的依據。“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5]由此可見,馬克思把生產方式的變更看作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也即現代化的根本動力。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歷史性,資本主義現代化也就具有歷史性,因此不能把現代化等同于資本主義化。
(三)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可能性
馬克思深入歷史的本質的維度,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本質進行了深刻批判。通過剖析現代社會存在論的根基,馬克思揭示了隱藏在資本主義現代化背后的物質動因——資本的本質。資本的趨利性和增殖性決定了資本擴張必然會導致各種社會矛盾,從而使資本主義社會陷入危機,帶來諸如人的物化、自然的異化、社會的分化等無法克服的內在困境。因此探索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就成為一個新課題。馬克思晚年進一步深化了對東方社會的研究,他明確將資本主義現代化邏輯的“歷史必然性”僅僅限制在西歐國家,為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開辟了理論空間。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蘇聯現代化建設取得一定成功,這種理論可能逐漸轉變為社會現實,也再次證明了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可能性與可行性。
二、歷史進程:探索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相統一的中國道路
中國現代化的探索同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選擇密切相關。一方面,社會主義道路的確立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根本前提、明確了性質方向;另一方面,現代化訴求又構成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之初始規定。這兩者內在地相互作用,共同呈現出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發展歷程就是探索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相統一的過程。作為既追趕現代化又區別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一種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通過扎根于具體國情的本土化方式,開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新模式。
(一)社會主義定向的基本確立
由西方開啟的現代化憑借在特定階段獲得的“絕對權利”,建立起“東方從屬于西方”[3]405的中心—邊緣世界格局。處于這一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近代中國,在探索中國道路的過程中必然以這種現代化訴求為開端。從1860年洋務運動開始到1919年五四運動,無數仁人志士在西方現代化的啟發下,提出過各式各樣的方案,但最終都以失敗而收場。反思這一段中國人認識現代化的歷史,可以說這是中國現代化意識的朦朧開啟階段。從器物、制度到文化,中國一步步效仿西方,結果卻是“學生”總被“老師”欺負。有學者概括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現代化的探索,只是在地域意義上重新復制一個西方,這種“空間上的跨界平移”終究是水土不服的。直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尋找到中國共產黨這一主體力量,中國現代化探索逐漸放棄了對西方模式的幻想,開始探索植根于本土化發展的可能。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首先必須獲得民族國家獨立,這就需要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為之奠基。“中國的社會革命最終采取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定向”[6],從此中國的現代化探索由資本主義模式轉為社會主義模式,社會主義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定向。
(二)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交匯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真正開啟。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中國社會的首要任務和重心所在。囿于當時條件所限,“公有制+計劃指令+集權型現代國家”的蘇聯現代化模式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之初模仿的原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具體國情,以和平、有序的方式推動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以農村集體經濟和城市國營企業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體系,并依靠強大的國家計劃指令構建起比較完整的工業和國防體系。但由于缺乏歷史經驗,加上對“什么是現代化、怎樣發展現代化”這一問題缺乏正確認識,中國在現代化道路的探索過程中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把市場化、社會化、城市化等現代化的基本特征看成資本主義的專利,從而把社會主義和現代化對立起來,造成了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分離與脫節”[7]。有學者將這一時期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歸結為“反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模式”[8],即僅僅從資本主義的對立面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踐中脫離生產力空談社會主義,忽略了現代化本身的內涵和要求,未能全面深刻理解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內在聯系,因而沒能開辟出一條成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仍在探索中艱難前行。
(三)社會主義與現代化關系的深刻調整
回顧中國現代化探索的歷程可以發現:全盤西化不可取,反之亦不可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的認識,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解決的歷史課題。這一時期的現代化探索不再從教條的社會主義理念出發,而是以更加務實的態度,包容不同社會主體的實踐探索,不斷調整對社會主義與現代化關系的認識。現代化不再僅僅作為社會主義的附屬存在,而是成為社會發展的中心議題,市場化、城市化、法治化等現代化的一般規律逐漸得到尊重。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也不僅僅拘泥于制度形式上的抽象規定,而是建立在更為扎實的現實基礎上。強調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也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9]。在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上,糾正了以往把社會主義與現代化分離開來的錯誤傾向,強調社會主義只有與現代化密切結合,不斷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才能吸引人、征服人,才有牢固的根基。在“發展才是硬道理”“三個有利于”等一系列科學理念的指導下,中國逐漸探索出一條立足本國國情而非教條式照搬、扎根本國實踐而非堅持固有模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一道路厘清了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差異與沖突,把握住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更加特殊的規律,實現了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真正結合。
(四)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深度融合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也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完善。進入新時代,在回答“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重大時代課題的過程中,我們對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也不斷豐富發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要命題的提出,把現代化提升到制度現代化的新高度,標志著我國現代化內涵的整體躍升。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理念,如“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10],“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1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12]等,進一步加深了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在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上,社會主義和現代化被視作“一體兩面”的統一體,二者共同構成當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完整目標。這也意味著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必需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深度融合。這既是實踐發展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自信的體現。
三、世界意義:人類現代化的中國方案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實踐證明,“這條道路,不僅走得對、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夠走得穩、走得好”[13]。這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新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世界社會主義、人類文明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開辟了現代化發展新路徑,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
西方現代化憑借其“身位優勢”書寫了現代化的經典版本,以至于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人們對“現代化=西方化”的神話深信不疑,并堅信“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14]。在“西方中心論”話語體系的籠罩下,二戰以后,除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外,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走上了西式現代化道路,結果卻“遭遇到傳統與現代、富裕與貧困、發展與秩序、解構與重建等一系列悖論,造成現代社會發展的斷裂”[15]。面對實現現代化這一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立足“走自己的路”,圍繞“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一主題,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出了一條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現現代化的新路。這一道路的成功實踐,意味著西方模式——曾經被視為唯一值得效仿的發展模式——“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時代終結了,證明了現代化發展路徑的多樣性,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現代化道路并沒有固定模式,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16]
(二)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為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注入新動力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其與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20世紀90年代初發生的東歐劇變,不僅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也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遭受普遍質疑。隨之而來的是“歷史終結論”等理論大肆宣揚社會主義已經“歷史性退場”,并宣稱“資本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成為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17]。社會主義真的退場了嗎?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開創,這一問題終于有了明確答案。“中國的發展給人們指出了一條擺脫全球資本統治的出路,也使人們產生了對社會主義前景的希望。”[18]實踐證明,面對金融危機、生態危機、能源危機、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的現實挑戰,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正愈益暴露其弊端,陷入一系列現代危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長期穩定的世界奇跡,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終結,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證明了科學社會主義強大的真理性,為世界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增添了全新的內涵。
(三)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長期以來,西方道路塑造的西方現代文明一直被視作人類文明的最高形態。資本主義性質的西方現代化本質上是暴力的、反和平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言,“資本主義作用的內部邏輯——最大限度地尋求利潤,總是迫使它不斷擴張,從而廣泛地占據整個地球”[19]。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西方現代文明也呈現出鮮明的對抗性特征,整個人類歷史圖景都被想象成“原子式的帝國”之間自然的、永恒的沖突。與此不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其“和平主義”的基本定向,使人類文明摒棄了二元對立思維,樹立了和諧共生理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有明確的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和方向,因此不可能像西方道路那樣與擴張和戰爭相伴隨,更不會走向西方式霸權主義。需要強調的是,作為中華文化一以貫之的傳統,“和平主義”并非停留于想象的和平,而是表現為現實的歷史運動,這一點在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發展中到處可以找到依據。近些年中國大力倡導的“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對“和平主義”這一文化傳統的生動詮釋,也是為民族國家的和平崛起、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的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