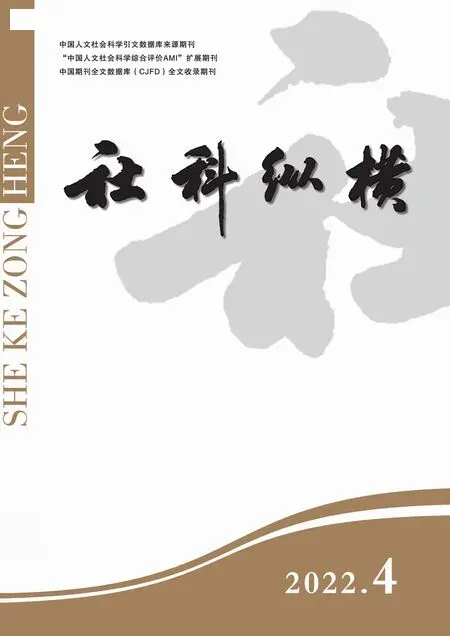孟子對孔子“政者正也”的理論推進
解曉燕 張會蕓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 山東 青島266580)
孔子首提“政者正也”,開啟了君主的一己之正與天下政通一體圓融的政治文化傳統。對于“政者正也”,孟子繼承孔子思想,同樣主張“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孟子·離婁上》),將治國理政的政治責任集中于政治領導者,反復勸誡政治領導者強化自我修養;也將政治的終極目的歸為道德教化,認為“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孟子·滕文公上》)。在此基礎上,孟子對“政者正也”的思想引申與發展,從仁與禮、王與霸、德與位三個維度總結出內圣之道、外王之道及君臣之道上的“正”之闡述,引申出上承天意、下符民意、更合心性的“正治”理論體系。
一、仁與禮:孟子論“正治”的內圣之道
“政者正也”并非孔子對“政治”的辭典式定義,但集中體現孔子對政治活動本質的認識。在孔子看來,“正”是指領導者德行之正,政治的要點就在于執政者發揮其道德表率的作用。孟子論“正”的一大發展在于突破早期儒家容禮之學的范疇,打開個體心性哲學之門對“正”的主體性進行深入挖掘,使得君子之“正”不再只是由外向內安頓的以禮正身的過程,更成為由內向外擴充的存心養性之路。
孔子一生尊重三代相傳的禮樂制度,認為禮樂傳統經夏、商、周三代損益相繼,到周代呈繁盛之態,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在此基礎上,孔子談“政者正也”之“正”大半屬于以外在禮制規范要求君子涵養威儀之論,可歸于早期儒家容禮之學的范疇。《論語》中提及“正”字24次,共計16則。除個別如“正唯弟子不能學也”的介詞使用外,其他悉數是對君主、卿相、士大夫等為政主體的規訓直言,其豐富內涵主要在于以等級名位規定下的禮制對一己之身進行嚴格的自我馴化,打造“事上也敬”與“臨其民以莊”的身體魅力。具體視之,孔子論及“正”的相關語段涉及身姿之正、衣冠之正、容貌之正及顏色之正等多個方面。如《論語》強調君子站坐間的身姿要端正,合乎禮制。對此,《鄉黨》篇載“席不正,不坐”,《論語注疏》解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1],另載“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與此同時,《論語》指明君子在國君前的行與立要添一份敬重感,如《鄉黨》篇寫明“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等。另如,《泰伯》篇載曾子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指出君子的容貌、臉色、語氣皆要莊重合禮,才可使他人敬重與信任,終可使得“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堯曰》篇則言“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強調位居人前的君子要衣冠端正,目不斜視,眼神堅定。在衣冠體貌之外,孔子雖未以“正”言之,但始終要求君子的行止要踐履“禮”的規范以達到正身之目標。
春秋時期禮樂逐漸淪為僵化的形式而不復有內在的生命,孔子也曾一度感慨道“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試圖重新為日益僵化的禮制貫注新的精神基礎。《論語·八佾》記載林放問禮之本,孔子答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篇另一處有言“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學而》篇也言“禮之用,和為貴”。儉、戚、敬、和等明確表示外在禮樂需要扎根于一種本源性的內在情感。對儒家思想體系而言,孔子最大的貢獻之一在于援仁入禮、以仁釋禮,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評,“儒家繼承了禮樂傳統而同時企圖從內部改造這個傳統,賦予禮樂以嶄新的哲學涵義……仁義之說乃是突破禮樂傳統而出”[2]。然而,作為社會性規范的禮與作為主體性規范的仁兩者如何融通,孔子言之未深。論及禮,他承繼并整理舊的禮樂經典,但未能指明“克己復禮”的內在自覺到底源于何處;論及仁,他多從具體表現隨宜而言,如孝、悌、忠、恕,也沒有指明仁的根據由何而來。由此,在孔子的理論中,“政者正也”的“正身”尚存在“正出于二”的困境,呈現為以禮正外在與以仁正內在的二元隔閡,仁與禮的融通顯然需要進一步推進。
孟子對孔子論“正”的發展即在于嘗試打通仁與禮以及社會性之身與主體性之身①的隔閡,使得君子“正己”不再是外在規范與內在自律的兩層皮。孟子所處的時代與孔子已明顯不同,諸侯各國進入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煩瑣的禮制大多名不副實,周禮進一步衰落。處此背景下,孟子的理論對以禮制規范由外往內安頓的正身重視度不高,甚至對孔子以禮制為要義的正名之論都未曾提及②。孟子對孔子“正身”理論發展的第一步在于將仁、禮與“心”結合。在孔子那里,以心論仁尚未出現,“仁”作為其頻繁提及的良善情感未能扎根于“心”,這使得“仁”缺少落實于普遍個體的情感著力點③。而孟子承子思而來,以私淑孔子自居,他自覺地繼承孔子關于“仁”的睿識,發展出“仁心”之說。《孟子》中“心”出現117次之多④,將“仁”與不忍人之心直接對接,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盡心下》),另一處孟子在關于四端的論述中,將不忍人之心表述為惻隱之心: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皆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孟子·公孫丑上》)
《告子上》篇表述稍有不同,但意義相近: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⑤。這其中,孟子強調“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凸顯仁、義、禮、智的心之本源與各具差異的情感實質。在論及仁、義、禮、智四者關系時,對比孔子的仁禮并重,孟子關于仁與禮的論述可謂大異其趣。在孟子這里,他明確地指出仁是所有一切之大本大源的情感,是人心向善的最初動因,根源于人之為人的惻隱之心或不忍人之心。“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而義、禮與智位于仁之后,與作為仁之端的“惻隱之心”相比,作為義之端的“羞惡之心”、作為禮之端的“恭敬之心”、作為智之端的“是非之心”皆處于后置位置,需要先在“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一更根本的衡量標準,解答因何羞惡、因何恭敬以及因何是非認定的問題⑥。從大本大源之意出發,孟子口中的“仁”有時也有囊括四心的統合性內涵,此所謂“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來,“政者正也”的“一己之正”與“天下政通”皆淵源于仁,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與這一過程同步,孟子對“禮”進行了“內向化”的重新闡釋。在孟子之前,“禮”主要是作為一種國家的基本制度,即作為“禮制”來被定義的。然而,禮崩樂壞的現實使得禮的制度性理解越發名存實亡。孟子之“禮”在傳統的外在制度內涵上大幅萎縮,反而向內收斂為根植于心的一種觀念或者情感,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或“恭敬之心,禮也”⑦。換言之,孟子之“禮”成為一種表象,它的本則深藏在人的內心感應之中,表達的是一個人發自內心對人、對事所表示出的尊重。禮之用必須出自誠心的敬意,“致敬盡禮”(《孟子·盡心上》)實為一體。《孟子》中有“禮人不答,反其敬”(《孟子·離婁上》)的說法,指出禮若落實不到日常,需要反求諸己,捫心自問是否心意誠敬⑧。“禮”也不作為一個單獨的倫理道德范疇而孤立存在。以恭敬之心為端緒的“禮”,后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與“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并為前者所統攝。禮以仁作為存在的根據,禮所誠敬之對象在于“仁心”與“仁政”,崇仁心、尊仁政的“敬”就成為禮的情感實質,即仁本禮用。禮演化為一種君子“以仁存心”之后衍生的恭敬、辭讓之觀念,復而再轉化為約束君子的外在德行規范。
由是觀之,孟子對仁與禮的統一,尤其基于仁的先在性及本源性進行的新“禮”改造,突破了封建舊禮的桎梏,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給予了“禮”以嶄新的情感實質與哲學內涵。孟子的理論努力完善了孔子言而未盡的仁禮關系論,他主張存心養性,由內往外擴充式地以仁正心進而正身,這其中就囊括了“禮”的全新理解。此“禮”逐步脫離尊容禮、正威儀的制度內涵,蛻化為尊仁敬道的觀念與德行,進一步奠定了儒家“有諸內而形諸外”的思考模式,解決了孔子懸而未決的“正出于二”的邏輯困難,完成了“政者正也”的本源內求化過程,使得政治運作與為政者的主體品性聯系更為緊密⑨。而自另一方面來講,孟子論禮的新舊之別,代表著戰國中晚期“政”的合法性論證正在發生質的轉變。禮樂原本是代表著三代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學,是政治權力合法性的集中表現,但在孟子看來,本于仁的德行之禮較之于舊有的規范之禮處于更高的位置,甚而兩者矛盾時,孟子主張“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孟子·離婁下》),這實質上確立出王道之于霸道、道統之于政統的超越性位置,開啟了先秦時期論“正”與“政”的新篇章。
二、王與霸:孟子論“正治”的外王之道
孟子將孔子“正出于二”的仁禮并重轉化為仁本禮用,對“正”的把握更明確地收緊為對“仁”的內在皈依,“正”治之“正”的主體本源被根植于“仁心”之上。孟子基于此以正為政、以正導政,在為政者的內在心性與外在政治之間建立起直接的關聯。依孟子之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仁心與仁政是一體貫通的,天賦本然的良心善性是實現王道仁政的人性根據,以仁政平治天下乃是惻隱之心自君主內心逐步推至“政”的客觀化過程,或言之,“政在經驗生活中的達致具體就展現在仁的倫理向度中”[3]。為政之道的關鍵之處在于君主對惻隱本心的自覺與發現,進而面向黎民百姓的存養與踐行。由此,建立在統治者天賦本然的良心善性基礎上的仁政成為一種君民憂樂與共的人性化政治。
如果說孟子論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賦予了孔子的“政者正也”以本心本體,孟子論君王的“不忍人之政”則將內在的君主心正與外在的政通人和實現了邏輯整合,賦予了“政者正也”更明確的民本指向。孟子將此種人性化的民本政治稱之為“王道”,曰: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孫丑上》)
在孟子看來,儒家的內圣之學是存養本心之學,其存養的惻隱之心轉化為外王之道則顯現為民本之學。“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若君主將自己的不忍之心運用于民之疾苦上,則為不忍人之政,此種不忍之政就是仁政,是王道。王者因民而王,君主為民信任與追隨的緣由在于其與民憂樂與共,欲民之所欲,惡民之所惡,由此關心民生,制民以恒產。這種共情恰恰肇因于王者自覺挺立、擴充其內心隱微之處的“不忍人之心”這一端緒,此所謂“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在孟子這里,“政”成為統治者與人民休戚與共的實現過程,由此,“政者正也”之“正”在指涉修己正身的內圣之道外,也擁有了直指政治權力正當性的第二重含義,即政治權力的實行過程必須符合“保民”“安民”的“外王”之道。
孔子論“政者正也”,基本不包含對政治權力的正當性或合法性的深入探究。《論語》中與政治權力合法性問題直接相關的就是孔子的“正名”之說。《論語·子路》篇記載衛國國君衛靈公去世,流放在外的其子蒯聵與繼承君位的其孫輒父子二人爭奪國君之位,作為父親的蒯聵成為流放在外的臣下,身為兒子的莊公卻是身居上位的國君。基于父子爭國的特定史實,孔子提出為政之要在于“正名”,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與此同時,他卻難在各有劣跡的父子二人中點明誰更有資格成為一國之君,此事甚至成為后世爭訟的一樁疑案⑩。事實上,在禮崩樂壞的春秋亂世中,孔子雖倡導復古,強調因襲傳統之“名”,卻也隱隱生發出擺脫血緣正統論,尋求“以實正名”,以此為政治權力的合法性進行論證的自覺,只不過這種自覺尚是潛在的、隱匿的,未與保民、安民產生切近的關聯。孔子的理論中存在大量關于養民與重民的闡述,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論語·堯曰》),即便如此,民本思想在其理論體系中仍是蜷縮的。孔子曾言“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但未就此引申,進一步點明若上位者殘暴不仁,君子在“事上也敬”與“養民也惠”之間如何果斷抉擇。君子“行己也恭”的內在之誠指向等級禮制還是仁心仁政?這樣的矛盾還沒有赤裸裸地袒露于孔子的經驗視野中,由此道統與政統、王道與霸道的區分尚隱沒在其字里行間,這也是孔孟二人關于“霸”以及管仲態度不一甚至立場相對的原因所在。
孔子對“相桓公、霸諸侯”的管仲評價比較復雜,但無可爭議的是他評管仲以仁:“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論語》中,仁人低于圣人、高于君子,配享仁人稱呼的僅六人: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以及管仲[4]。管仲九合諸侯,匡扶周室,維護了周室的存續,這對于“吾從周”的孔子來說是天下要緊的大事大功,在此意義上,孔子認為管仲之作為可比肩極少數的古圣先哲。原本依孔子之見,禮樂征伐的政治大權應該出自周天子,此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諸侯若越俎代庖,便反映天下無道,不合于孔子的理想。管仲輔佐的齊桓公乃一介諸侯,竟做起“一匡天下”的大業,這在孔子正名主義的嚴格解釋下是離經叛道的,其所作為不是其所當為。但由孔子對管仲相桓公一事的評價看,諸侯操持大權若用以尊王攘夷、回護周禮,孔子不惟不非議,更稱許不已。此處,孔子評管仲以“仁”不是由保民安民而論,而是從周禮存續的結果出發默許了管仲違禮行權的霸道11○。
戰國禮壞樂崩的情景更加嚴重,各個強國均主張兼并,“霸諸侯”成為君主們心心念念的政治目標,征伐頻仍,時局動蕩。處此背景下的孟子在王道與霸道之間劃下了清晰的分割線,與孔子站在相對的立場上批判管仲。在孟子看來,“以力假仁者霸”“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孟子·公孫丑上》),“霸”是缺乏政治正當性的純暴力統治方式12○。孟子不認可霸道,認為“一匡天下”必須以王道行之,霸道絕對不可取,在他看來“征之為言正也”(《孟子·盡心下》),一匡天下的政治征伐必須祭出民心所向的“正”之大旗。如孟子與齊宣王談及伐燕時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一國如行暴政、虐其民,另一國對待虐民之國加以征討是正當的,因為“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以民意為衡量標準,孟子贊成征伐虐民之國,誅殺國君以“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下》)。同樣以民意為衡量標準,孟子反對嗜殺,反對為爭地而戰,為爭城而伐,為國君的私利而殺人,他始終強調的是“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在這個意義上,孟子認為管仲輔佐齊桓公征伐天下、稱霸諸侯不足稱道。孟子借曾西之口言道,“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子·公孫丑上》)。在孟子看來,管仲只是依靠齊桓公的信任專齊國之政,也只是順齊國之強成就了本就屬于齊國的霸業,所謂霸業也不過“功烈如彼其卑也”,這種評價恰恰是因為管仲止步于霸道,沒有能向前多走一步貫徹王道。
由是觀之,孔子言“正”與孟子言“正”的含義指向不同,兩人對于“政”也生發出理解上的演化。因為孔子“正出于二”的標準設定,管仲才可在其評價體系中擁有“如其仁”的極高評價。孟子則將“正”的價值基礎定位于仁,主體本源根植于惻隱之心,其理解的“政”自然也摒棄了孔子的多向理解,聚焦于“不忍人之政”,著力尋求保民與安民。基于此種民貴君輕的認知,孟子對統治及征伐的合法性作出了獨到的“正”治闡釋。可以說,孟子對王道與霸道的區分以及王道高于霸道的論說,在王綱失序、君與民日益分離乃至對立的情況下,將君與民重新聯系在一起,并以保民安民的責任為突破口開啟了統治者的“名之自覺”[5]。對此,蕭公權曾評價道,孟子的養民之論深切著明,為先秦僅見。在這一點上,孟子甚至多次重申西周以來“天民合一”[6]的思想,借助天的權威拔高民的位置,指出“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依孟子之見,作為天下的最高統治者,天子統治權力的合法性最終取決于“天與人歸”。就政治權位而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只是天不再是會表達情緒的人格神,“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13○。由此,天成為虛懸的至高主體,民升為天意反應的載體,權力的合法性雖由天與,實賴人歸,人之所歸就是民心所向14○。在孟子看來,無論是禪讓、世繼甚至是征伐,都可能是正當的權位轉移方式——“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萬章上》),但前提在于民心所向、民意所歸,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
論述至此,孟子關于“正治”大致完成了一體圓融的體系建構。孟子延續《禮記·中庸》之論,云“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下》)。“誠”作為人心深處一種真實無妄的狀態,成了天道與人道的內在連接,因“誠”之故,天道不需要任何的媒介就可以直接地落到人(或曰“勞心者”)的內在道德生命中,而主體通過內在的心性就可以領悟天,此所謂“盡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而在“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的論述中,不言之天摒除了人格化的特征,民(或曰“勞力者”)成為天放置于外在人世間的代言群體。由此,孟子形成了以天為“正治”的超越性根據、以仁為“正治”的主體性本源、以民為“正治”的實踐性落腳的邏輯整合,開拓出上承天意、下符民意、更合心性的“正治”理論體系。
三、德與位:孟子論“正治”的君臣之道
儒家主張“德位合一”,但在實際的政治中德與位多數時期并不統一,發展到孟子所處的戰國中晚期,德與位甚至呈現出各據兩極的趨勢,道統與政統趨向二元分立。若以政統言,王侯本應為主體,君尊臣卑,但現實中的君主多為私欲與野心所蒙蔽,居高位而無德;而以道統言,原本固定在封建關系中各司其職的“士”因動蕩的局勢成為以道自任的“游士”,他們在擺脫封建身份羈絆的同時,獲得了對天下正道探索的自由,進而逐步從居高無德的強權者手中接過了道義話語權。在此前提下,德與位相待而成成為孟子論及君臣關系時的理想之境,他寄托于“賢君”與“賢士”雙方的自覺努力,為孔子的“政者正也”增加了君臣“相責以善”的新內涵,開拓出以德“正”位的新面相。
孟子從道統的超越性視角來審視現實的政治權力,其對君臣關系的定位超越了以往儒者主流的“君尊臣卑”的范疇。在孟子看來,雖然以政統言君高于臣,但以道統言,君主絕對不可屈盛德之士為臣,而應將賢士“舉而加諸上位”,時時以一種無確定之規的師徒之禮尊而養之。
孟子主張君主“恭儉禮下”,尤其要以師徒之禮尊賢養賢。就尊賢而言,他曾有“不召之臣”的闡發。原本為人臣者有義務服從君主之召,甚而臣子聞君之召應唯恐不及,否則與禮不合,是為不敬。孔子就有“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的明確態度。孟子挑戰這種傳統禮制觀念15○,《孟子·公孫丑下》曾載齊宣王召孟子前往朝堂,意欲請教治國之道,但孟子托病不朝。孟子認為“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若君主的德性不如臣民,他應該屈尊降貴、親自登門,敬賢人如師,虛心請教。針對不召之臣,孟子友人景丑曾直斥其非,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孟子·公孫丑下》)景丑所持有的觀點就是基于君尊臣卑的政統而發。但在孟子看來,敬作為禮的情感實質,呈現出層次之別,他辯解道“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公孫丑下》)。依孟子之見,君主雖居高位,但就輔世長民一事恰居于下位,其“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孟子·萬章下》)。不召之臣作為君待賢之“禮”,背后所體現的“敬”正是君主對仁政之道的尊崇。朱熹認為此處“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7],即以爵與位為衡量標準的敬是“敬之小者”,以道與德為衡量標準的敬是“敬之大者”。
孟子不排斥君主“養賢”,只是主張“養”應該是君主尊重賢者道德人格的延伸,是“尊而養之”的自然之舉。《孟子》文本中屢次提及堯待舜之道,認為那才是“悅賢能養”的典范。為君者的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他看重舜的賢能,就給予其充足的生活資料,“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孟子·萬章下》),而后舜又被堯“舉而加諸上位”,委任以重要的政治職位來發揮其才干,甚至于到“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最終成就流傳千古的尊賢佳話。另一處,《孟子·離婁上》中曾載:“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孟子·離婁上》)此處君對臣的“三有禮”,首先強調君主“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即君主敬重賢臣的道德志向,聽從其所持的治國之言,以民生為重,施仁政于天下;其次要求君主體恤為臣者的生活艱難,預先免除臣子的后顧之憂。
“三有禮”在重要性的排序上是不可顛倒的,如果抽離人格尊重,君主僅僅表達對臣子的物質體恤,恰恰可能成為孟子所言的“非禮之禮”(《孟子·離婁下》)。孟子與萬章的一段對話,恰說明君主對有德之士僅以富養之是不可取的非禮之舉: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曰:“繆公之于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于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馬畜彶。’蓋自是臺無饋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萬章下》)
繆公欲以物養賢者子思,但未能以師生之“禮”向子思學習仁政之道,其屢次贈送食物就變了質,成為一種褻瀆君子道德人格的“無禮”表現,甚至在子思眼中已經形同豢養犬馬。孟子認為君對賢士之禮的“養”必須以在切實行動上尊重其賢能才具與道德人格作為關鍵前提。此種情形在孟子身上也曾發生。齊宣王不尊其道,孟子致為臣而歸,王欲挽留之,便通過時子傳話,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孫丑上》),孟子義憤之下辭而不受16○。
孟子主張為臣者應以道輔君,“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甚至將為臣者的進諫推向一種必然的道德要求,拓展出儒家“正治”理念中重要的“他正”維度,使得“諫正”(即批評政治)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氣節與血性所在。
事實上,孔子對“以德諫位”也有相應闡述,但囿于禮制的規范,其表述相當克制。在臣事君的行為要求上,孔子希望臣子事君,“敬其事而后食”(《論語·衛靈公》),認識到事君“忠焉,能勿誨乎”(《論語·憲問》),做到“勿欺也,而犯之”(《論語·憲問》)的時時勸誡,強調為臣者勇于正君之不正。不過,孔子認為臣子選擇“犯之”的時機很重要,應“信而后諫,未信則以為謗己”(《論語·子張》),其背后暗含之意是君主對臣子未能建立起足夠的信任時,后者可選擇閉口不諫,孔子贊寧武子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便是此意。甚而再退一步,孔子支持“有道則見”的入世原則,也不反對“無道則隱”的避世行為,他視蘧伯玉為君子,正是因為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總體而言,孔子對君主仍保持著較高的敬意,他在“德”與“位”發生矛盾時,選擇以溫和的“以德諫位”方式處理,局限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中君尊臣卑的禮制約束仍時時可見。
不同于孔子的克制,孟子對“以仁為本”之新禮的改造突破了封建舊禮的約束,他稱“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孟子·離婁上》)。依孟子之見,敢于“責難于君”“陳善閉邪”才是對君上的真正的恭與敬。反之,無原則地迎合君上的私情己欲,可稱之為“賊”。另一處,孟子稱“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孟子·萬章下》),認為臣子立身朝堂之上但君主不行仁政,是臣子勸諫的職責未盡,可稱之為“恥”。孟子甚至認為“長君之惡”“逢君之惡”不僅不是臣子對君主應有的禮節,而是“罪”(《孟子·告子下》),是對君上最大的不恭不敬。“賊”字、“恥”字、“罪”字的使用,實際上已經將“諫”與為臣者的職責進行了緊密的道德捆綁,臣子不應只是君主命令的執行工具,而必須具備抨擊暴政的獨立人格,應“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上》)。在奔走列國宣揚仁義的途中,孟子常拿著儒家的這個人臣倫理去拷問尸位素餐的官員,例如,孟子曾對自己的學生樂正子話帶譏諷,“子之從于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孟子·離婁上》),認為樂正子只是從飲食起居上侍奉君主是不應該的,學古之道的終極目的應在于以道侍君。
孟子所倡導的諫諍,尚屬為臣者作為“有言責者”的外在行為標準,其最終目的在于由言而心、由外而內的“格君心之非”、觸君主本心。《孟子·離婁上》曾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是對孔子“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的同義表述。具體到君主,孟子認為在心與政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孟子言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孟子·公孫丑上》),另一處相似的表達講“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孟子·滕文公下》)。生于其心者與作于其心者即為君主的私欲,君主以其私欲吞噬不忍之心就是孟子所言的“放心”,若君主與民憂樂與共的心之本源被吞噬,落實到政事之上便會威脅到百姓生活甚至生命。孟子以君師自居,又以好辯揚名,其終身所求就在于通過諫諍的方式匡正君主的非正之心,使君主在自身的世俗欲望中實現善端的覺醒,回歸到仁義之心上來。如此,這段話中的“一正君而國定”的“正”強調的就并非孔子所說的君主自正,而是“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的結果17○。
如果“格君心之非”是賢臣“正君”的核心目標,諫諍就成為可選擇的手段之一。若將孟子的邏輯再向前延伸,處于道義一方的“大人”尋求“格君心之非”這一最終目的,其外在的形式手段可能就不拘泥于“以德諫位”。在此之上,孟子繼承先賢“以德諫位”的傳統,并表現出更強硬的姿態,如《孟子·盡心上》記載孟子與弟子公孫丑討論伊尹流放太甲的事,因太子太甲不順義理,作為輔臣的伊尹將太甲流放于桐邑,公孫丑的疑問在于“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但在孟子看來,伊尹“放”太甲于桐,是“格君心之非”的正當之舉,“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孟子·盡心上》)。伊尹作為孟子所列的“圣之任者”,是朱熹所謂“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7],其品行之高使得他有資格以放逐為手段求格君心。另一處,孟子曾向齊宣王直言,“貴戚之卿”肩負著重要的政治責任,即“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告子上》)。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有“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的激進之言,也曾申發“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的暴君放伐論,這兩處的闡發中,孟子部分揚棄了周公、孔子等先賢的樂觀態度,更深切地意識到個別政治上位者的幽暗人性難以改過遷善18○,但若是將其君臣相責以善的以德正位引申為“人民革命”思想仍存在過度解讀之嫌疑。孟子所言的以德正位實際上仍延續著孔子關于“道假勢以行”的明確要求,一方面他對易位之舉做了貴戚之卿的身份限定,同時更明確指出人臣不得動輒就言易位,“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孟子·萬章下》)。
綜上所論,孟子對君臣之道的論述無不體現出其對“道”的皈依立場和以道之“正”治位之“不正”的理論旨趣。此處,孟子盡管與孔子一樣推崇“政者正也”,但他賦予賢士以道為依歸的道德使命與政治自覺,士以“道”為依據考察君主行為,不斷“正其不正”。換言之,“正”的部分責任從君主之位轉向賢士之德,從君主自正位移到賢士對君主的“他正”上。在這個意義上,雖然孟子也講過“其身正天下歸之”“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但其前提已經加入了“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的批評諫正,相對孔子而言,“孟子的政治觀已經不是狹義的美德政治,而是偏重于士大夫立場的批評政治”[8]。
注釋:
①誠如楊儒賓所論,正威儀最大的底色在于它是以社會共同體規范的身份(即禮)展現出來的倫理,雖然在君子個體上表現出來,但它仍然只是社會性身體的意義,缺乏內在主體性的真實內涵。參見楊儒賓.儒家身體觀[M].臺灣中央研究院,1997:40-41。
②孔子對正的理解中“正名”占據重要位置,他借齊國蒯聵與輒之間君臣父子關系的錯位凸顯禮制的重要性。《孟子》中“名”出現10次,分別表“名字”“名目”“名譽”之義,與禮制相去甚遠。
③《論語》提及心6次,只1次與仁有所關聯,即《雍也篇》載孔子評價顏回道:“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但也并非以心論仁。
④《孟子》中心另有3次用于人名,不計入內。
⑤梁濤從孟子思想發展的歷程解讀四端之說的兩處不同,他認為《告子上》中所載孟子與告子辯論時,其四端說尚未完全形成,甚而與告子的辯論加深了孟子對四端的思考,但彼時其表達仍有不準確之處。后來他到齊國與齊宣王會面時再提四端,已經是比較成熟的說法。參見梁濤.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05-310。
⑥梁濤認為孟子之禮是對禮內涵的縮小,以辭讓之心推廣的禮只能表現為進退之間的禮儀形式,而不能再為社會等級制度提供合法性論證。筆者認為仁本禮用應該理解為權力的合法性論證的轉向。
⑦《孟子》中辭讓出現2次,恭出現11次,敬出現39次。恭敬與辭讓并不完全相同。就恭敬而言,在貌為恭,在心為敬,朱熹講“恭者,敬之發于外者也;敬者,恭之主于中者也”正是此意。辭讓則指不敢徑自接受而有所謙讓。兩者的共性在于將他者放在更高的優先地位上。在這幾個詞中論及禮的情感實質,“敬”確實更具代表性。
⑧《論語》曾提到“修己以敬”“居處恭,執事敬”,但論述的是君子之所為,未如孟子這樣直接將“恭敬之心”與“禮”畫上等號。關于論語中的敬可以參見陳立勝.“修己以敬”:儒家修身傳統的“孔子時刻”[J].學術研究,2020(8):30-37。
⑨有學者認為孟子的理論體系中存在兩種禮,一種是規范之禮,一種是德行之禮,參見劉旻嬌.請“禮”讓位合理嗎?———孟子論“禮”的雙重內涵[J].哲學研究,2020(4):70-79。
⑩后人對孔子這段話出現“糾名正分、以名正名”與“循名責實、以實正名”兩種解讀,前者主張以父子之道正君臣倫理,如朱熹引胡氏曰:“夫蒯聵欲殺母,得罪于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主張以父子倫理正君臣之道,由此該公子郢繼任君位。參見朱熹.論語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142。后者主張以君臣之道正父子倫理,如吳林伯曰:“有實而后有名,名緣實而生,故曰名附實也……孔子答子路之問,特征其中政治之名”。參見吳林伯.論語發微[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151。
11○金耀基認為孔子評管仲以仁是因為管仲的民本思想,筆者持不同意見。參見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史[M].法律出版社,2008:50.另可參見譚延庚.論孔子稱管仲以“仁”——“思想史事件”視野下的分析[J].管子學刊,2016(3):20-26。
12○《論語》僅圍繞管仲提及“霸”1次,孔子并未如孟子一樣揭示王霸之別,他提及“霸”沒有貶損之意,甚至稱許齊桓公“正而不譎”,贊許管仲“如其仁”,與此同時,孔子也提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似乎隱喻由霸至王是一個階段性的量變過程。孟子則明辨王與霸的不同在質不在量,在本性不在過程。孔子與孟子對于“霸”的理解已經發生轉變,這也代表著兩人對政治合法性問題的討論基點發生了位移。關于孔子論“霸”的歷史背景可參見劉仲敬.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80-81。
13○夏世華認為“天不言”是孟子重要的理論改造,他祛除了天的人格神特征。不言之天若被確立為最高權位授予主體,必須要為之配備一個能輔助傳達命令的實際權位授予主體。于是孟子才能主張“天與之”即是“民與之”,將后者作為傳達天授予權位命令的輔助原則。參見夏世華.孟子對早期儒家禪讓學說的反思與重構[J].2020(5):135-143。
14○孟子有時過于強調民意,反而在言語中忽略天意。如齊宣王認為伐燕順利,不是齊國之力所能為,必有天助,想以天意為借口進一步奪取燕國,他探尋孟子的看法,曰“不取,必有天殃”,孟子直接規避了天的問題,回答道“取之燕民悅,則取之,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孟子·梁惠王下》)。
15○孟子在現實上下等級的禮制規范與君主好善而忘勢的君臣新禮之間多有平衡,以緩和兩種“禮”之間的沖突。他也承認禮制規定臣對君命之召要積極服從,但同時又有不服從君王之召的情況,辯解之論大約有二,其一,他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孟子敬王也,這種敬就是禮。再退一步,他認為”市井之臣”和“草莽之臣”都算作庶人,庶人“不敢見于諸侯,禮也”。另可參見方旭東.服從還是不服從——孟子論人臣的政治義務[J].文史哲,2010(2):40-49。
16○魯繆公、齊宣王雖不用賢士之道但仍欲尊其人,甚至有意以物質財富的贈予來保持一種友人關系。孟子顯然反對與君主之間生發出非師非臣的“友”之狀態,他指出:“‘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這種模糊的“友”滲透著君主的物質供養,士因德而自持的尊貴便可能畏縮混沌,進而在君主面前惡化為“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的境況(《孔叢子·居衛》)。
17○孟子對“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的論斷,與他對為臣者的理想人格——“大人”——的道德想象相關。《孟子》中“大人”出現12次,大體可分為兩種不同的意涵指向。一種是指類似君主這樣的位高之人,如“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上》),其中的“大人”就是位高權重者。第二種指具圣人品性的輔君賢臣。孟子認為大人者養其大體、從其大體,即以心之官鉗制耳目之官,以良心本心充盈整個生命,居仁由義,不沉溺于食色利欲。
18○關于孟子的幽暗意識可參見晏玉榮.性善論、寡欲觀以及義利之爭——論孟子的幽暗意識[J].道德與文明,2017(5):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