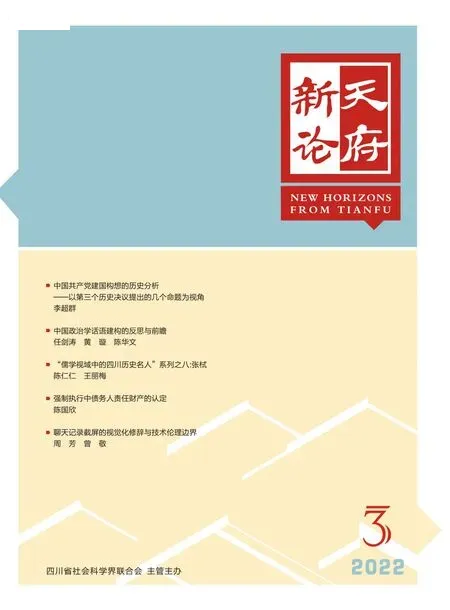聊天記錄截屏的視覺化修辭與技術倫理邊界
周 芳 曾 敬
一、引 言
截屏技術在當今社會生活中已無處不在,是人們信息化生存的一種方式。截屏技術是虛擬場域中時間與空間的“切片”,指向了一種觀看的方式與傳播的能力。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對視覺思維的理論探索,不僅揭示了視覺認知的思維方式和信息加工原理,更是“提供了一種通往圖像‘形式’的視知覺理論路徑,即在視覺思維層面進一步把握藝術的‘形式’問題”(1)魯道夫·阿恩海姆:《視覺思維》,滕守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頁。。因此,對聊天記錄截屏的探討不僅應從對話的語言和文本來考察其在交往中的實踐功能,更應關注“觀看”這種語言維度,審視其語言和圖像以何種方式“結合”,截屏作為動作特征的意向在這種視覺關系中充當著什么角色,指向了什么傳播場域,產生了什么新的意義。由此,對聊天記錄截屏的討論既是一個心理接受問題,更是一個命題論證問題和技術倫理問題。
當前對聊天記錄的研究多將其視為一種法律意義或勞動關系上的證據(2)王春:《微信記錄,怎樣才能成為證據》,《法治日報》2021年9月12日。(3)吳鐸思:《微信截屏能否證實勞動關系?法院這樣判》,《工人日報》2021年7月22日。,抑或從現實層面探討其在“跨場景傳播”(4)胡沈明、王若男:《聊天記錄跨場景傳播的意義異變與影響探究》,《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21年第1期。中的“法律邊界”(5)李歡、徐偲骕:《隔“屏”有耳?——聊天記錄“二次傳播”的控制權邊界研究》,《新聞記者》2020年第9期。與“社交規范問題”(6)莫潔:《“截屏社交”也該有禮儀和規則》,《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20日。。對截屏的討論多從其“類型”(7)龐晨、陳孟南:《淺析截屏圖片的功能、特征與風險》,《新聞愛好者》2020年第1期。與“功能”(8)劉戰偉、李嬡嬡、劉蒙之:《圈層破壁、知識流動與破圈風險——以截屏與錄屏為例》,《青年記者》2020年第18期。出發,以“可供性”視角描繪截屏從“‘拍攝屏幕’到‘用屏幕拍攝’的技術演變過程”(9)宋美杰、陳元朔:《為何截屏:從屏幕攝影到媒介化生活》,《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從而更深層次地探討截屏在社交中的“權力異化”與“規制”問題(10)張愛軍、朱歡:《“截屏”社交的權力異化:邏輯、風險及其規制》,《新視野》2021年第4期。。這些成果以聚焦現實的方式展開了對聊天記錄及其截屏傳播的討論,或多或少都指向了信息時代的社會關系建構與數字化生存圖景,并以紓困的姿態關注聊天記錄截屏傳播的風險與規范問題。然而,在現有研究中,“截屏”沒有脫離技術現象維度,它被作為一種中介體驗之上的動作和行為,在這種視域下,聊天記錄被簡單化為截屏的對象,其自身的語圖關系被嚴重低估了,對截屏的討論應引入更多“非技術”視角,注重其在信息編碼方式和心理認知上的差異,從一些看似“正常”和“無害”的內容中看到實際蘊含的重要意義。
二、截屏:關于記錄的記錄——一種基于視覺修辭的視角
“人們在使用新的數字技術時,往往會依據物質實體來命名、使用它,也會采用物質隱喻來理解它。”(11)章戈浩:《網頁隱喻與處理超文本的姿態》,《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11期。截屏技術也不例外,作為一種基于“屏幕窗口”的“‘人-機’交互方式”(12)宋美杰、陳元朔:《為何截屏:從屏幕攝影到媒介化生活》,《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截屏技術的發展伴隨著計算機“圖形用戶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操作系統的發展,以程序或插件的形式集成到計算機系統之中,是一種基于“視覺界面”的信息處理方式。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與普及,“聊天對方將聊天內容復制、截屏并進行轉發的‘二次傳播’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13)李歡、徐偲骕:《隔“屏”有耳?——聊天記錄“二次傳播”的控制權邊界研究》,《新聞記者》2020年第9期。。在這一過程中,截屏既指向了對話內容的時間性,也為聊天記錄的空間延伸提供了可能,但這種記錄實際上又是一種被再次編碼的記錄,即一種“關于記錄的記錄”,是對話在時空語境中的“切片”,生產的是一種可流通、交替、切換的“界面”(14)保羅·維利里奧:《消失的美學》,楊凱麟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6頁。。
要注意的是, “截屏”并不僅是對話的直接“描摹”與“復刻”,還是“視覺在‘瞬間加工’和‘建構’的產物”(15)Barthes R., “Rhétorique de l'image,”Communications, 1964,pp.40-51.,截屏這種技術形態是事物的構成結構中被“提煉”出來的一種抽象關系。換言之,作為動詞的截屏不僅代表一種行動過程,也意味著一種慣習甚至意識知覺。從這個維度上看,截屏是基于視覺認知思維方式和信息加工的手段,是一種通往圖像“形式”(16)約翰·伯格:《觀看之道》,戴行鉞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4頁。的路徑,是作用于記憶的圖像力。因此,從視覺修辭的角度討論聊天記錄截屏,有利于以“形式”去把握圖像的修辭意義,即通過對視覺形式的識別與分析,挖掘出隱藏于修辭結構中的含蓄意指,這也給對話的研究提供一種新的空間和路徑,是自反性與批判性的一種審視。
(一)基于關系建構的多模態敘事
在視覺修辭視角下,聊天記錄是一種多模態的媒介文本,截屏是一種視覺修辭手段,對聊天記錄的截屏則是一種“策略性”的文本生產過程。聊天記錄是以文字或表情符號為內容的記錄框架,其功能是通過對語言文字或具體符號的對位與引導,產生一個話語場和敘述系統,從而發揮闡釋與導向的作用。當前對聊天記錄的研究多將其置于傳播活動場域,關注聊天記錄的意義與話語問題,這是一種傳統的信息研究路徑,著眼的是當下、是現象。而將其引入視覺修辭的維度則意味著關注其難以被我們觀察的策略、結構和機理問題。
“截屏”是一種對“對話敘事”的記錄,體現了承載信息和溝通功能的語言與圖像之間的“對話主義關系”,其文化后果往往是“現代主義的或后現代主義的”(17)劉濤:《語圖論:語圖互文與視覺修辭分析》,《新聞與傳播評論》2018年第1期。。對于聊天記錄截圖的意義生成而言,其同時包含了語言和圖像元素時,究竟是語言主導還是圖像主導?其圖文敘事反映出怎樣的深層文化語境及偏向?從敘述主體來看, “我”與“你”的人際對話構成了“聊天”,并通過截屏產生了記錄。在傳播未發生時,“它”——聊天記錄的本體是靜態的、孤立的,指向的是“我”與“它”、“你”與“它”的虛擬的人內傳播關系。當傳播發生后,這種模態便指向了更多元的傳播類型,如“我”與“他” (一次傳播過程,此處“他”為接受聊天記錄截屏的第三人)、 “他”與“它” (第三人將接收到的聊天記錄截屏進行二次傳播的過程)、 “他們”與“它” (指代聊天記錄截屏通過不同類型的媒介被更多人傳播的過程),這些關系指向的不僅是人際傳播和群體傳播,甚至是大眾傳播。
在這種多模態的關系下,敘事的互文便發生了。文字、圖片、表情、語音、外部邊界信息圖例共同構成聊天的場域,指向某一在場空間,體現了對話者的在場性,易給讀者一種置身于語境之中的“情境” (The Psychology of Situation)。(18)Caprara, G. V., Van, H. G., Modern Personality Psychology,New York:Wheatssheaf,1992,p.422.聊天記錄截屏是語圖關系的重新構成:聊天以語言的表征為特色,沿著固定的線性邏輯,是基于順序思維的歷時意義上的信息加工,體現的是符號體系構成中的“組合關系”;而截屏后的圖像是基于聯想思維的共時維度上的意義生產與空間延伸,是用圖像化的方式回應意義問題。截屏所生產的是一種特定的圖示。然而,這種由圖像和文字共同構建的體系中,究竟是誰指向了“實指性”(19)趙炎秋:《實指與虛指:藝術視野下的文字與圖像關系再探》,《文學評論》2012年第6期。?或許這涉及的是一個角度問題,即如何看待這張聊天記錄截屏,是以內容思想作為判斷依據,還是以表象為參考條件。這也指向了圖文關系研究的兩個向度:既要關注圖文自身的運作要素和方向,也尤其要將外部條件納入考慮。
(二)基于視覺心理的修辭認知
當我寫下“聊天記錄截屏”幾個字時,你是否本能地在視覺意義上尋找它的“對應物”?對于聊天記錄而言,呈現出來的文字僅是視覺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截屏技術構成的帶有圖像屬性的元素如由顏色、形狀、數字、排版方式等構成的“視覺規則”則賦予了“對話”以情形和場景。從大腦對語圖信息的加工機制來看,圖像信息會以一種先行者的姿態出現,“由此而知覺到的形狀模式,具有兩種性質足以使它們成為視覺概念,一是它的普遍性,二是其容易識認性。”(20)魯道夫·阿恩海姆:《視覺思維》,滕守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頁,第38頁。基于信息生產的經驗,聊天記錄截屏以其“普遍”和“日常”的形狀直導我們的認知,從而在心理上產生一種類似于“存在” “在場”的感覺。在這種特征之下,截屏的圖像形態往往會率先吸引觀者的注意力,并在瞬間產生一種強烈的認同。這種心理的本能反應正是建立在對這些形狀的斷然識認上,在阿恩海姆看來, “對形狀的知覺,就是對事物之一般結構特征的捕捉”(21)魯道夫·阿恩海姆:《視覺思維》,滕守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頁,第38頁。。這些“形狀”是事物突出而又確定的特征,使得其被我們識別和認識,而后才是做出反應。截屏技術所提供的正是這樣一種基于形狀的知覺,一種相對穩定的“視覺意向”,使對話和內容形成某一刺激物的大體輪廓,從而在大腦中喚起一種“屬于一般感覺范疇的特定圖示”(22)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滕守堯、朱疆源譯,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54頁。,這種圖示通常與我們的視覺經驗相關,并促進了知覺的形成。
在知覺的組織活動中,人眼不局限于直接呈現于眼前的材料,而是把看不到的那一部分也列入所見物體的真正組成部分,這種視覺認知包括“對象跟蹤、因果關系的視覺表征和感知相似度空間”(23)Gauker, C., Words and Images: 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Ideas, Kingd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45.。聊天記錄截屏作為一種視覺意向,通過其“繪畫功能”——界面布局、顏色、排版方式、頭像展示、時間信息等作用于人眼并產生視覺邏輯關聯,隨后由“視覺符號”來完成人際交往想象互動的意義表征功能,最后指向視覺意向的“記號功能”——指征個人的對話實踐記憶。嚴格說來,沒有一個知覺對象僅僅是指向獨特的一個,這一點對于聊天記錄的截屏傳播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對話發生的語境、對話參與人的表達風格以及潛在的傳播欲望和訴求都由截屏賦予了一種心理“裝飾”。換言之,截屏是基于視覺心理的修辭認知方式。
(三)作為記憶的“物質”邊界承載形式
“當前媒介技術與物質性研究對象從過去歷史中的各種顯在可見之物,更多地轉向了CPU、內存、圖標、手勢、點贊等‘不可見之物’。”(24)宋美杰、陳元朔:《為何截屏:從屏幕攝影到媒介化生活》,《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這種研究通常批判性地檢視人類與媒介技術的關系,是一種“后人文主義的媒介技術論”(25)張昱辰:《走向后人文主義的媒介技術論——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媒介思想解讀》,《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4年第9期。。基特勒更是通過從“詮釋批評”到“后詮釋批評”的轉向完成了對文本意義詮釋慣習的摒棄,將視線轉向“那些讓意義生產成為可能的外部性條件”(26)徐生權:《意義之外:后詮釋批評與基特勒媒介研究的奠基》,《新聞界》2020年第9期。,即意義之外的媒介物,關注“媒介技術與群體意義上的身體和心智技藝的綜合,以及這種綜合對于文化與社會所呈現的那種‘培育性’”(27)曾國華:《媒介與傳播物質性研究:理論淵源、研究路徑與分支領域》,《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11期。。聊天是意義的生成,記錄是記憶的建構,當記憶不再只是“回憶”,而是可以被看見、被搜索、被傳播、被“偶遇”的對象,記憶發生了什么?截屏這一具有動作指征的“技術”又如何“培育”個體、社會與文化的記憶呢?
屏幕是記憶的“物質”邊界載體,卻并不作用于多維的記憶本身,而是體現了一種思維、一種移情方式、一種字面意義上的傳送(轉喻)。聊天記錄是對“消失的記憶”的抵抗,截屏則提供了一種保留“消失的記憶”的驅動力。“消失的記憶”不是物質性邊界,而是認知性邊界,處于旁觀者的眼睛之中、視網膜之上。從這種意義來看,聊天記錄不處于“呈現”的狀態,而是處在一種隨時可消失的危險之中,信息可被“撤回”,記錄存儲于界面之內卻被遺忘在界面之外,速度便是對“消失的記憶”進行抗爭的動力機制。在維利里奧看來,技術是速度的表象。由此,截屏不僅是一種技術指征,更是一種動作的速度指征,表現為對時間的視覺修辭。它服務于觀察,是與信息的不確定之間的競速(在信息被遺忘前的記錄也表現為一種競速),是記憶“證人”觀察點的位移,提供的是一種象征意義。
古斯塔夫·布雷提什(Gustaf Britsch)認為,視覺思維的形成條件就是“用一條邊界線把一個有心得到的(或意圖性的)位置或景物,從一種無心得到的(非意圖性的)背景中分離出來”(28)Britsch G., Kornmann E.,Theorie der bildenden Kunst,Frankfurt am Main: Klassik Art Verlag, 1926,p.55.。正如前文所述,截屏是一種基于視覺心理的認知,是記憶的“保留之術”。聊天記錄截屏便是用一個“物質邊界”把一種有心保存(意圖性)的記憶,從一種無意保存的(非意圖性的)記憶中分離出來。基于對話的記憶是流動的、易被沖淡的,而聊天記錄截屏是對話的“假肢模型”,使“他者”介入了虛擬的對話生產與記憶建構,也是“我們”在世界中移動的另一種方式。截圖將“運動”的對話推向極限,推向“脫落”和“肢解”。聊天記錄的截屏傳播是對眼球運動的縮減,體現的是信息的加速傳遞。截屏技術通過對記憶的邊界重塑,在隱匿中把玩信息世界,享受處于記憶的權力頂峰。
三、證據:個人敘事時間的凝固與空間移動
聊天記錄在實踐中如何被推向了作為“證據”的信息存在方式?其中的規則是什么,蘊含著怎樣的修辭結構?在這個“空口無憑” “截圖為證”的視覺傳播時代,對話不再是實際空間的聚落鄰近,而是實況時間的立即性鄰近或虛擬性鄰近。聊天記錄的私密性被截屏剝奪,是視覺修辭實踐中一種指向認知思維和信息習慣的產物。“修辭實踐強調的勸服過程、對話過程或溝通過程都建立在特定的文本生產基礎上。離開修辭文本的生產,修辭意圖將失去符號載體,修辭效果也就無從談起。”(29)劉濤:《視覺修辭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58頁。研究截屏技術下的聊天記錄如何成為證據,便是將“證據”置于修辭實踐過程中,探討其修辭效果的問題。
(一)指向視覺論證的意義生成
聊天記錄的截屏傳播往往帶有鮮明的論證屬性:可能是“對事件、現場的目擊,也可以是一種信息、證據的間接在場”(30)張超:《圖像不一定霸權:數據新聞可視化的語圖關系研究》,《編輯之友》2021年第9期。。在聊天記錄的截屏傳播中,我們不得不去反思一個問題:“觀看先于言語”(31)約翰·伯格:《觀看之道》,戴行鉞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4頁。。約翰·伯格強調將圖像置于觀看結構中,通過理解觀看的“語言”來把握圖像的意義,即關注視覺修辭。這一論斷強調了圖像的意義受制于觀看的方式。因此,對截屏的討論不能滿足于給觀者提供一種看見眼前某個運動完成的幻覺,它應該引導觀者對產生該運動的力量感興趣,對該力量的強度產生思考。“形式化技術試圖控制任何可能的語言,并通過可能說出的東西的法則而懸于語言之上。”(32)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390頁。截屏造就的是一種視覺工業化,建構了一種遠離直接或間接觀察的綜合直覺場,使得由這種技術所產生的工具性虛擬圖像成了一種“再現”的等同物。它既是言說,又是圖像;既是意義,也是形式;既是對話的充實,指向感覺的現實性,又是語言符號與外在形象的固定指涉,醞釀著新的意義——“證據”。
“有圖有真相”折射的是圖像的表意問題:一種事物難以直接通過視覺化的方式呈現,需要借用另一種事物“取而代之”,這實質上反映的是概念對圖像的依賴。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證據?要想理解這種原本概念化、難以表達的意義,需要通過可見的、具體的、可以感知的視覺符號來編織相對抽象的內涵,這便是圖像的“表達記號”,又被稱作“人為記號”(33)D. 威爾特恩、 靳希平、 鄭辟瑞:《另類胡塞爾——胡塞爾現象學的“標準化”和“非標準化”的解讀(續)》,《世界哲學》2008年第3期。。因此,截圖是對“真相”這一概念的“表達”和“轉喻”。作為一種視覺修辭手段,截屏不僅是符號層面的再現,也加工著意指維度的意義。聊天記錄截圖在“系統性認知機制”(systematic processing)上依托認知語言學,是對話內容的文本化和視覺化書寫,強調“對信息做出整體性的追問、分析與回應”(34)Dillard J.P., Peck E., “Affect and Persuasion Emotional Responses to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s,”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27,No.4,2000.,這指向了“證據”的直接意指;經過截屏后,在組織化、結構化和系統性的話語情境下,聊天記錄成為“高度凸顯的實體”,激活了“啟發性認知機制” (heuristic processing)——側重于“借助某些便捷的決策法則來構建自身的行為態度”(35)Dillard J.P., Peck E., “Affect and Persuasion Emotional Responses to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s,”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27,No.4,2000.,這指向了“證據”的間接意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間接意指”中,一些“其他意義成分”,如由情感、態度、策略構成的概念實體在指向“真相”時常常被忽略。對聊天記錄的截屏,好比使用指紋作為身份識別符號的做法,是人們的一種電子化“簽名”。“寧可相信在犯罪地點采集的指紋,也別相信罪犯的招供”(36)Goddefroy E., Locard E., “Manuel élémentaire de police technique,”Police Administrative Et Judiciaire,1922,p.42., 將指紋作為證據的方式,標示了“敘述、作證、描述模式的衰落”(37)保羅·維利里奧:《視覺機器》,張新木、魏舒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7頁。。不同于指紋身份的是,經過截屏后的聊天記錄,不僅有指涉身份的可能,也能指向對話的描述。然而,這種意指結構中的“部分→整體”常常被忽略:截屏是一種視點、視角、視域的選擇過程,同時這也意味著對其他意義上可能的視點、視角、視域的放棄,這指向了截屏在修辭學上的“策略”和“功能”問題。 “證據”一旦進入圖像,其意指行為就成了一個反自然化的言說過程。截屏篡改了對話的內涵,將反自然翻轉為自然,對話的現實性被召喚為形式的象征意義。
(二)讓位于圖像的公共展示
“所謂‘技術’,指的并非機器以及關于機器的活動所構成的復雜網絡,相反,它意味著當我們介入到這些活動中時所預設的態度。”(38)斯拉沃熱·齊澤克:《事件》,王師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38頁。截屏是一種“再現”的放縱,“逼真性”與“非逼真性”的哲學問題將壓倒真與假的問題。言外之意,聊天記錄的截屏傳播并不是其能否成為證據的問題,而是在這種技術之下對逼真性的哲學反思。截屏使對話的傳播在發送、接受之間瞬間切換,這將替代對話中的交際原則,因為交際還需要某種時限。在這種語圖關系中,關注點從對話轉為圖像,從對話空間轉向截圖時間甚至轉向瞬間。這種轉移過程中的選擇與修辭才是影響其現實或形象的根本要素。于對話的存儲與傳播而言,我們思考的不再是對話處于什么樣的時空距離,而是我們所感知的截圖處于什么威力之上。
截屏是瞬時性抓取與潛在性轉移,有利于一種展示,是對知覺的供應。就像“書寫是話語的補充,‘電傳’出現是實體出現的補充,一種(時間與空間雙重意義上)不在場的補充。”(39)保羅·維利里奧:《消失的美學》,楊凱麟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70頁。在網絡社交中,“聊天”是話語的情景,“記錄”是議題的情景,而“截屏”則是空間的情景。聊天記錄截屏一旦被置于傳播維度,其必然就會讓位于圖像的某種展示功能:截屏呈現的是話語的邊界,記錄構成了議題邊界,而截屏卻因其“不在場的補充”功能將空間邊界大大拓展。從當前由聊天記錄引發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來看,截屏已經成為一種 “可見性” (visibility)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聊天記錄指向的是人際傳播和群體傳播領域,多依托口頭語言,而其被截屏后,在指向大眾傳播(通常依托書面用語)的過程中往往因為語言的“分裂”——“書面語和口頭語、學校和市集使用的語言都有清楚的區分”(40)羅伯特·E·帕克:《移民報刊及其控制》,陳靜靜、展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5頁。而面臨著一種“言語”分裂的現象,甚至可以制造一種公共的“話語暴力”(41)黨西民:《視覺文化的權力運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7頁。。
截屏作為一種個人敘事時間的凝固方式,產生的是工具攝影和實用方法啟發的圖像。截屏技術使聊天記錄走向現時性,而截獲的圖像便是一種“過渡區域”——從威力走向行動的過渡區域。在屏幕后, “我”看不到聊天記錄;在屏幕前,聊天記錄撲面而來,它的截屏圖像“看”到了“我”。這是知覺的反轉,更是一種知覺的暗示。截屏技術強加于注意力并強迫目光的維系,其中載入了對時間的鋪展,使“光學”——“圖像”與“運動”混為一體,將圖像的再現漸漸地讓位于一種真正的公共展示。于是,截圖便擁有傳播的屬性,并自帶“動作基因”,這種屬性要求它必須有“證人”。
自公共空間向公共圖像讓步之時起,私人空間便失去了其相對獨立性。截屏技術為私人話語的公共傳播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由此“生產”的聊天記錄截圖一旦進入傳播領域(無論是人際的、群體的,還是大眾的),就成為一種“細節資源”,帶著強烈的說服使命,滿足的是窺視者的新型視覺慣性,是一種反常的在場,一種證人視點的位移。聊天記錄截圖在傳播中的真實性部分依賴于對證人眼球運動的這種求助,這其實暗含了一種對對話實踐的參與和感知的整體性。在聊天記錄的截屏傳播中,我們以主觀的闡釋來辨別形式與話語(語言與圖像),辨別我們充當證人的場景。
四、陷阱:警惕技術的視覺規訓
“如今,要談論視聽技術的發展,不得不召喚虛擬圖像的發展及其對人們行動的影響,還不得不宣告這種新型的視覺工業化,即一個綜合知覺的真正市場的建立,還有它暗示的倫理問題。”(42)保羅·維利里奧:《視覺機器》,張新木、魏舒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 118頁。在意識到信息技術對知覺的輔助后,更應該將目光投向對視覺技術本身的配置與評估的反思之中。
(一)技術倫理:基于聊天記錄雙向生成的傳播知情權的討論
聊天記錄的生成依賴于兩個或多個主體平等的信息參與建構,但截屏技術卻是“霸權”的,對于個人而言意味著一種圖像生產的權利。盡管希冀于人的信息倫理自覺,但在一方截圖過程中,另一方處于完全“不知情”的狀態,個人的通訊秘密權受到侵犯。馬賽克、裁剪等技術手段能“保護”的人,也僅僅只有“自己”——保護自己的“面子”,維持一種尊重他人的形象,而信息的內容卻處于一種暴露之中。在部分對話情景里,接受聊天記錄的人甚至可以根據實際交往經驗和對話的前后語境猜測出被掩飾“頭像”的“他者”的真實身份。
同時,有必要討論截屏在加速信息傳播的過程中是否存在一種作用于“閥下知覺”的潛在功能。當聊天記錄被大量截屏,傳播處于危險的“過分暴露”之中,傳播者與觀看者將會產生一種適應性,并失去對這種修辭技術的反思能力與風險感知。不同于拍攝屏幕,截屏已超出了它們的復制功能,轉而有一種更為隱匿的特性,屏幕截圖在傳播中容易因其特殊的形式使人們忘記它的來源與作為截屏的“他者”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看,截屏是一個動作,一種界面活動(interactive),更是“‘社會技術系統’的一部分”(43)Nancy A. Van House, “Feminist HCI Meets Facebook:Performativity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Vol.23,No.5,2011.。它重構著人類的信息實踐方式和習慣,并不斷取代或擠壓物理和地理空間里的人類社會活動,從而失去了向現實世界“神馳敞開” (ecstatically open to reality)的特性。界面中“對方正在輸入……”提示著對話的“順暢進行”,使對話的參與者感知到一種反饋與共時,從而以一種更積極的姿態迎接“聊天記錄”的動態生成。然而,從技術設計的角度來看,是否也應有一種反饋方式來作用于另一種動作特征——“對方正在截屏……”?
(二)“技術謠言”警惕
聊天記錄截屏作為一種“日常”的視覺文本,其“表征信息進行遴選的過程無疑潛藏著巨大的權力規制”(44)張偉:《從“技術驅遣”到“體制建構”——現代視覺傳媒藝術的權力運作與敘事策略》,《現代傳播》2016年第5期。。截屏是“事實”的“外衣”,是信息流動中的一種存儲“戰略”,而問題在于它同樣能通過一種去信息化的手段從戰略上隱藏部分信息。正如齊澤克強調對媒介的觀察應從一些看似正常和無害的內容中看到其實際蘊含的重要意義。對聊天記錄而言,最終被看到的視覺形式,注定存在一個意義上的“畫框”和“時限”。這意味著它的呈現是受制于一定的“邊界”,是從所有實際中抽離出的“虛擬部位”,其“連貫性的真實(real consistent)被給予了虛擬,如同真實一般來處理它,作為將存在者裝載于它的存在中之物來掌握”(45)阿蘭·巴迪歐:《德勒茲:存在的喧囂》,楊凱麟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8頁。。
在社交媒體時代,“謠言”以聊天記錄的形式卷土重來。此處的謠言并非指涉新聞中的虛假消息的一種表現,而是借用這個詞匯來表達技術邏輯生成中依然存在著“假冒”的問題。如一些聊天記錄生成器,這種技術能夠創造虛擬對話主體、建構對話空間與時間、生成對話內容,借用人們對圖像信息的依賴從而生成虛假信息,使截屏成為一個生產謠言的裝置與機器。除此,裁剪、馬賽克、部分刪除等技術使聊天記錄成為一種“去定位”的語言,這種語言在制造“戰爭”——傾向于遠距離的傳播、形成討論、引導輿論上充滿了風險。這兩種“假冒”不管是部分造假還是整體造假,本質都是生成“替代性”的視覺資源,以制造“意義”。
在視覺傳播時代,公共事件依賴圖像。換言之,想生成公共事件則可以以視覺作為修飾方式。這就是聊天記錄得以從私人領域向公共領域移動的原因。正是由于當前網絡社會心態中的信任危機使截屏成為一種抗爭工具,聊天記錄截圖成為一種抗爭性資源,實現的是對意義的爭奪。然而,在社會運行過程中,截屏人的行動不能僅歸結于個體的行動主義,也不能將其視為一種簡單的表面現象加以理解。相反,要將其置于社會運行的更深層,將這一行動置于“個體與集體的互動與和合過程”(46)姜寧寧: 《走向行動主義:互聯網社會中的組織哲學》,《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中。截屏技術成為公眾集體挪用的視覺修辭結構(框架)生產著具有抗爭性的意義,同時也極易造成一種“認知無意識”。“視覺學的潛能在于產生失明的視覺(sightless vision)。”(47)約翰·阿米蒂奇:《維利里奧論媒介》,劉子旭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74頁。維利里奧用近乎偏執的言論抵制視覺文化生活的虛擬化。在他看來,構建當代文化的各種后現代“視覺機器”正越來越多地涉及“失明的知覺”。就像阿恩海姆所描繪的那樣:“今天,我們對這些影像的訴求,已經習以為常,因而甚少注意到其整體的影響……可是我們接受廣告影像的整個體系,卻猶如接受氣候中的某個因素……我們十分熟悉這種效果,也就變得視若無睹。”(48)約翰·伯格:《觀看之道》,戴行鉞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85頁。
五、結 語
聊天記錄截屏不僅是話語的記錄問題,更是圖像的認知和技術倫理問題。以視覺修辭的方式來討論聊天記錄截屏,是以語言與圖像的互動關系和指涉意義為出發點,以論證的方式去思考“形式”的情景與功能,由此走向一條反思性的批評之路:聊天記錄的截屏傳播并不是其能否成為證據的問題,而是在這種技術之下對“逼真性”的哲學反思。截屏并不是一種絕對意義上的不偏不倚的信息記錄中介,對它的運用需警惕屏幕上看到的直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