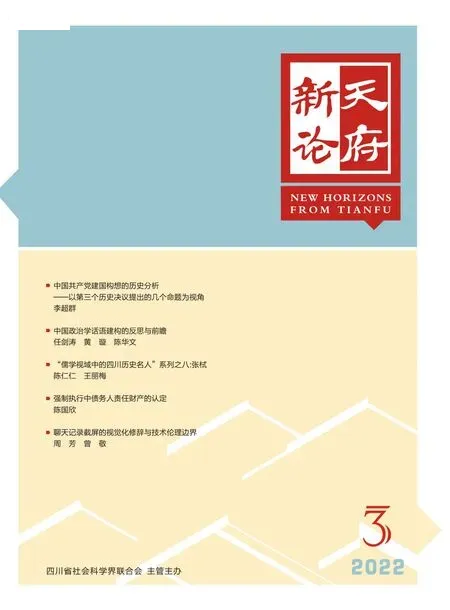裂變與循環:從諾蘭科幻電影看后工業時代的時空敘事
司 培
一、引論:后工業時代的時空敘事重寫
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指出,“當技術的性質發生重大變化時,人們就會想到后工業社會”(1)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高铦等譯,新華出版社,1997年,第67頁。。他將社會分為“前工業社會” “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前工業社會從自然中直接攫取資源,生產力低下。工業社會與“加工的自然界競爭”(2)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高铦等譯,新華出版社,1997年,第110頁。,利用能源把自然環境改造為技術環境。后工業社會則是以“信息為基礎的智能技術”(3)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高铦等譯,新華出版社,1997年,第110頁。走向前沿,“在高新科技的應用中使用算法、程序設計以及虛擬模式”(4)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高铦等譯,新華出版社,1997年,第15頁。的電子化、智能化技術社會。這一分析大體上勾勒出了后工業社會中人類所面臨的生存境遇,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技術變革對人類生存境遇所帶來的改變。
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發展,能夠更新人的時空經驗,重塑人的時空想象與時空敘事。在前工業社會,人類對自然有著較強的依賴性,人類直面自然,依照自然的節律而生活與認識世界,其時間觀念也“是自然律動的象征”(5)吳國盛:《時間的觀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00頁,第100頁。。到了工業社會,面對“加工的自然界”,人類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與自然的直接聯系,創造出“各種工具設備和機械裝置,形成了一個獨立于自然界而運行的人工世界”,時間與空間變成了抽象性的“物理世界的代言人”,“單向線性的時間觀”占據了主宰地位。(6)吳國盛:《時間的觀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00頁,第100頁。后工業時代的科學技術革命改變成了這種情況:熱力學第二定律與相對論的提出在物理學上拓寬了人類時空認知的維度,信息技術、數字技術、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媒介技術等一系列新的技術變革又進一步更新了人的文化經驗,打開了人類的時空想象。時空不再是一種外在的狀態,它具有與人類意識相關聯的可能。科幻作品成為人類表達新時空經驗的重要載體。電影文本以其豐富的視聽表現力成為人類重寫時空敘事的重要媒介。
通常而言,討論時空問題的科幻電影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為討論意識時空或虛擬時空的作品,如《盜夢空間》《黑客帝國》《頭號玩家》等;一類為探討宇宙時空的作品,如《2001太空漫游》《星際穿越》《流浪地球》等;還有一類則是探討時空回溯乃至重寫的作品,如《彗星來的那一夜》《前目的地》《信條》等。在此之中,由諾蘭導演的系列作品較為全面地涵蓋了對時空討論的幾個維度,具有一定的連貫性與代表性,可以作為我們探討科幻電影時空敘事的重要樣本。本文試圖以此為切入點,探討后工業時代時空敘事的幾個重要表征,以及其與人類文化精神世界之間的密切聯系。
二、虛擬時空敘事的擬真性與分裂性
虛擬時空,從其呈現樣式上來看,也可被視為一種意識時空。笛卡爾在《第一哲學沉思集:反駁和答辯》中指出:“我的本質就在于我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或者就在于我是一個實體,這個實體的全部本質或本性就是思維。”(7)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反駁和答辯》,龐景仁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2頁,第82頁。肉體“只是一個有廣延的東西而不能思維”(8)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反駁和答辯》,龐景仁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2頁,第82頁。,所以它次于心靈而存在。笛卡爾在此將身與心分開,通過意識的存在確證了“我”的存在。意識脫離物理實體的存在,便可以被視為虛擬的存在。這樣的存在方式,在想象的時空中得到了較多呈現。唐人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便記有一人在夢中做了大槐安國南柯郡太守,醒來才知不過大夢一場。夢則可視為承載其意識的虛擬時空。蒲松齡的《聊齋·畫壁》亦講一書生從古剎壁畫入一幻境,其文曰“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動耳”(9)蒲松齡:《聊齋志異》,張式銘標點,岳麓書社,1988年,第5頁。。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意識對時空的虛擬性處理。但在這些作品中,虛擬時空與現實時空具有統一性與明確的邊界,其存在維度單一,內在結構較為穩定。數字技術創造了一個新的網絡時空,數字化生存成了一種新的存在形態,虛擬時空獲得了相對獨立性,具有在視覺甚至感知上有形化的載體。在電影《黑客帝國》中,這種虛擬的數字時空得到了深入的刻畫。人類意識被從肉體中抽離出來,載入一個叫“母體”(Matrix)的計算機系統之中,意識在虛擬世界完成自己的一生。到了諾蘭的電影《盜夢空間》,意識時空被進一步展開。雖然它與《黑客帝國》的代碼世界不同,意識時空以夢境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從本質上看,夢就是虛擬的隱喻,將《盜夢空間》的夢境世界替換為《黑客帝國》的代碼世界似乎也并無不妥。縱使全片并未直接涉及數字技術、虛擬現實等要素,它所探討的仍是一個后工業時代的夢境時空,一個擬象化與數字化景觀中的夢境時空。此種夢境已然不同于“南柯一夢”,它與現實的邊界逐漸模糊,甚至于要向現實滲透。并且其內部結構也變得更為復雜,多個時空之間交錯重疊又分岔裂變,充滿了后現代的偶在性與多重性。
《盜夢空間》主要講述一群盜夢者在他人夢境世界植入意念,以此改變現實的故事。這就牽涉到虛擬時空與現實時空之間的相互滲透與影響問題。虛擬時空的問題雖在過往的人類文化傳統中也有涉及,但其僅作為精神層面的一種設想,并沒有像今天這樣引發如此大的討論,甚至影響到人類對現實時空的理解。鮑德里亞、德波等一批西方理論家,便以“擬象” “景觀”來解釋后工業時代人類的生存世界。鮑德里亞有言:“原始社會有面具,資產階級社會有鏡子,而我們有影像。”(10)讓·鮑德里亞:《消失的技法》,羅崗等主編:《視覺文化讀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76頁。德波則指出:“世界圖像的專業化已經完成,進入一個自主化的圖像世界,在那里,虛假物已經在自欺欺人。”(11)居伊·德波:《景觀社會》,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頁。他們的觀點指向了一種對數字化時代真實消失的隱憂。“這種巨大的消失不僅是事物之潛在變換的消失和對真實之嵌套的消失,也是主體之無限分化的消失和意識在真實的所有縫隙中連續分散的消失。”(12)讓·鮑德里亞:《為何一切尚未消失》,張曉明、薛法藍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人的存在似乎只能“以自身在技術層面的消失和融入數碼技術的秩序為代價才能獲得永生。”(13)讓·鮑德里亞:《為何一切尚未消失》,張曉明、薛法藍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媒介—虛擬—網絡構筑了一個新的存在時空,“擬真”侵蝕了真實,模糊了“真”與“非真”的邊界,虛擬成了一種長久的存在方式。《盜夢空間》中就有一個揭示了虛擬對現實侵蝕的寓言式場景。
在光線昏暗的地下室里,一大群人整齊地躺在略顯簡陋的鐵架床上,流動著黃色藥劑的管道插入他們的頭頂,將他們長久地帶入一個虛擬的夢境時空。這般批量化生產夢境的情形,與今日媒介化、數字化、信息化的文化工業生產體系倒頗有幾分相似。影片中有人問那位看守地下室的老人: “他們來這里是為了做夢?”老人答:“不,他們是為了醒來。”夢境于他們而言已然成了現實,現實似乎才是夢。正是在此種顛倒之中,虛擬時空擁有了與現實時空產生糾葛的能力,甚至在反復的“擬真化”實驗中不斷向現實逼近,從而消解與現實之間的差異,最大限度地對現實世界產生作用。這是影片時空敘事的基礎文化邏輯,以此邏輯為前提,虛擬時空內部結構的復雜性特質才得以顯現。
影片構造了一個多重嵌套又分岔裂變的虛擬時空。夢境被設置為多個層次,每一層夢境都是一個獨立的時空體系。在現實世界中入夢可以進入第一層夢境,在第一層夢境中入夢則可進入第二層夢境,以此類推,直至第四層夢境將會到達潛意識的邊緣,有進入迷失之域的危險。從這個架構上看,夢境時空內部是分裂而又嵌套的關系。每一層時空從上一層時空中分裂而出,又嵌套在上一層時空之中,分裂體與母體共存,既并行運作又層層交疊,形成了一個立體交錯的時空網絡。
分裂是這個虛擬時空網絡形成的原初動力。就整體構造而言,多重時空由分裂而產生。按照影片的設定,每一層夢境在進行分裂之時都會比上一層夢境的時間延長20倍,也就是說分裂帶來了多個不同時空體系的并置。這些時空之間依靠延時的方式發生聯系。時間的一貫性與連續性被打破,成為多個有待重組的序列。在博爾赫斯的小說《小徑分岔的花園》中,就描寫了一個分岔與裂變的時空迷宮。文中說道:“時間有無數系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復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絡包含了所有可能性。”(14)豪·路·博爾赫斯:《博爾赫斯全集(小說卷)》,王永年、陳泉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132頁,第132頁。并且“時間永遠分岔,通向無數的將來。”(15)豪·路·博爾赫斯:《博爾赫斯全集(小說卷)》,王永年、陳泉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132頁,第132頁。這種文學作品中的時空想象,體現出分裂在時空敘事中所發揮的拆解與重組效能。《盜夢空間》正是在此種分裂力量的推動下構建了一個迷宮般的虛擬夢境時空。
在影片中,夢境作為虛擬時空的藝術呈現形態,同時也是主人公流動意識的重要載體。夢境的分裂同時也意味著意識的分裂。主人公從夢境中再度進入夢境,由夢生夢,因意識的層層流動與分裂而生出一個個虛擬的子時空。沿著一條意識流動的主軸線,又生出許多細小的分岔,塑造了每一層夢境中具體的意識活動。不過,此種虛擬時空中意識的流動往往具有一定的隨機性與偶然性,常常不受主人公的控制,甚至會從自我中分裂出來,對其進行干擾乃至抵抗。較為典型的例子便是盜夢者柯布每每在夢境中執行關鍵任務,便會有與妻子有關的意識從自身意識中分裂出來,對其執行任務進行阻撓。可見,在夢境時空中,意識并不具有絕對的穩定性,它并非完全整一的,而是層層分裂,充滿了無數變化的可能。
這種復雜的分裂力量使影片的虛擬時空在內部構造上呈現出兩個方面的顯著特質:其一是多重子時空之間鮮明的差異性。分裂意味著對徹底的整一性的拒絕,正是在這種拒絕中,夢境時空才得以從原初時空中剝離,繁衍出多個與之不同的子時空。這些子時空一旦分裂而出,就會成為其自身,而非完全地聽從某種整一力量的集中指揮,顯現出極為鮮明的差異性。在影片中,這種差異表現為每一層夢境的時空場景之間要素與內涵的變化。差異性將多個分裂的時空體系區分開來,構建出一個立體的時空結構。其二是多重子時空之間錯位的同時性。同時性意味著多重子時空可能存在的并置狀態,錯位則由多重子時空之間的差異而生。分裂致使夢境時空被切割為一個層層疊疊的立體結構。這些子時空之間彼此錯位且同時存在,即便是處在近乎交叉的狀態之中,也不能完全重疊。它們之間既有所關聯又彼此背離,構成了一個交錯嵌套的不規則時空體系,滋生出無數分岔的路徑與復雜交織的通道。夢境作為虛擬時空敘事的重要載體在這里真正呈現出它的內部結構張力。時空的分裂與意識的流動交織,塑造出后工業時代的詭譎迷夢。
這不僅僅是某個導演的創造,它與一種新的群體性時空想象相關聯。在時空敘事的分裂背后所隱含的是數字化時代符碼編織與信息流動中的文化意識分裂。德勒茲在《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中提出了一種控制論與信息論社會的基礎文化構型。他以“根莖”的概念來比喻一種“多元體”的文化生長形態,并作出了如下論述:“一個根莖可以在其任意部分之中被瓦解、中斷,但它會沿著自身的某條線或其他的線而重新開始”(16)德勒茲、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輝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10頁,第15頁。,且“始終具有多重入口”(17)德勒茲、加塔利:《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輝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10頁,第15頁。。這意味著“根莖”具有無限分裂與增殖的能力,甚至因此而呈現出生長上的無序性。此種打破主體統一性的分裂意識一直在新的技術社會中生長綿延。利奧塔便將后工業時代對應的文化狀況解釋為“對元敘事的懷疑”(18)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槿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3頁。,即對一種宏大敘事的徹底解構。韋爾施則進一步將其闡釋為“整體的消解”與“部分的釋放”。(19)沃爾夫岡·韋爾施:《我們的后現代的現代》,洪天富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1頁。也就是一種徹底的多元化,每個部分都在作為其自身而存在。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將整一的消解作為反抗極權的積極要素,認為其促進了“多元的異質化”。這或可被視為分裂性時空敘事的深層文化趨向。
《盜夢空間》的時空分裂便發生于對整一的消解之中。但它并未完全像后現代主義理論家所預設的那樣,走向一種徹底的解體。其因在形式上受敘事體系的牽引而不至于崩壞,又因在多重分裂時受到主體意識的強力拉扯而產生了回歸整一的可能。它有一種多元化的趨向,卻又受到整一性的牽制。在其時空分裂的內部潛藏著一種離散性力量與整一性力量之間的博弈,故而“多元化”成了其分裂的趨向而非恒定的狀態。這種復雜的時空敘事狀態建構了虛擬意識時空的內在張力,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后工業時代文化的內在矛盾。
三、多維宇宙時空敘事的流動性與循環性
現代物理學的發展與新技術的變革促發了人類對宇宙時空的想象,重寫了人類的宇宙時空敘事。事實上,人類的宇宙時空敘事早已有之。遠古時代的人類因“未能將自己從自己的自然狀態中分離出來”(20)路易·加迪等:《文化與時間》,鄭樂平、胡建平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1頁。,在自然世界的 “淹沒” 與 “滲透” 中, 形成了一種與自身具有同一性的宇宙時空觀。列維-布留爾將之概括為“互滲律”(21)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丁由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62頁。。這種思維方式將一切自然事物具體化、形象化,神話敘事亦由此誕生。這一時期人類對宇宙時空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與其自身的感性直觀有十分密切的聯系。因此,宇宙時空大多被視為人類生存時空的展開,與之有關的神話敘事也未能完全突破人類所認知的三維空間限制。而“當人類自發產生神話幻象的非理性時代被理性時代所取代,指引和驅動想象力的要素從動物精靈變成新的科技手段,神話大傳統也就自然會轉化為科幻小傳統。”(22)葉舒憲:《從神話學看人類命運共同體》,《文藝報》2020年1月15日。科學技術的革新影響了科幻敘事的革新,人類也從三維的宇宙神話敘事走向了多維的宇宙科幻敘事。
近些年來引起熱議的科幻小說《三體》,就有大量有關多維宇宙的敘述。其中較為典型的一個場景便是高維文明向銀河系發起降維打擊,導致三維立體空間極速坍塌為二維平面。高維時空與低維時空在此發生碰撞,宇宙成為多維文明競爭與博弈的舞臺。《三體》所描述的雖是一個多維時空并存的宇宙,但它并不將重點放在對時空的刻畫上,而是著力于呈現宇宙間冷酷的殺戮游戲,并對多維文明體系做出相應的反思。要論及對多維時空更直接的表現,當數諾蘭執導的影片《星際穿越》。其所塑造的兼具流動性與循環性的多維宇宙,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后工業時代時空敘事的內在復雜性。
這部影片的故事設定與諸多充滿末世和災難色彩的科幻片相似,講述人類如何尋找地球以外新的生存家園。由此便牽涉到宇宙中多維時空的流動問題。在今天的人類看來,宇宙時空混沌、神秘、充滿了未知與無限的可能,具有極強的開放性。宇宙中的時間與空間也不完全如以往那般被認為是“事件發生在其中的固定舞臺”,而被視為一種“動力量”,它們“不僅去影響,而且被發生在其中的每一件事影響”(23)史蒂芬·霍金:《時間簡史》 (第3版),徐明賢、吳忠超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第34頁。。科幻電影更加大膽地演繹了這一思想,將時間與空間穩固的邊界打破,把整個宇宙推入一種完全不可預測的流動狀態。諸如《星際穿越》這般的科幻電影在呈現宇宙時空的流動時一般會采取如下敘事策略:首先,設置流動的起點與動力。這一起點常常是人類視野下的當下時空生存危機。在影片中,由于沙塵暴的強力威脅,人類不得不尋找新的宜居星球,恰好土星附近出現了神秘蟲洞,可以將宇航員送去更為遙遠的星系探索新的居住時空,故事便由此開啟。實現星際間流動的動力量往往是一種超越現有科技水平認知的宇宙力量。《星際穿越》中的星際流動推力被設定為“蟲洞”。它是連接兩個遙遠時空的狹窄隧道,借由此人類得以實現跨越時空的流動。“蟲洞”的敘事設定既帶來了人類在宇宙時空流動的動力,同時也加大了這種流動的不穩定性。其次,構造流動的多維性。宇宙時空的流動通常能夠突破三維乃至四維的物理限制,形成一種不同維度時空并置的流動。影片中的男主角在墜入黑洞后被卷入五維生物創造的時空,與處在三維世界的女兒并存,就屬于此種多維共在的流動。這樣的構造能夠為宇宙時空的敘事帶來一種極為多元的可能性。最后,推促流動自身的流動。這意味著在敘事上突破時空流動中邊界與連續性的限制,將其推入一種徹底的流動性狀態之中。時間與空間由此便不僅僅是某種衡量的尺度或某個具體的坐標,也可以作為某種動力量而存在,以其自身推促自身的運轉。此種敘事策略打破了時空在經典物理學意義上所具有的穩定性,將其徹底拆解為一堆流動且有待重組的要素,加劇了時空內部的分岔與裂變,呈現出宇宙時空難以預測的流動狀態與潛在的危險。
與流動性的宇宙時空敘事癥候相對應的是循環性的時空呈現狀態。循環既是流動的一種呈現方式,也是流動中的一種反復性行為。但反復并不意味著完全的重復,科幻電影的循環性時空敘事所要呈現的重點在于反復中的不一致。其所表達的是由差異性帶來的無限可能,而非由同一性帶來的徹底靜止。雖然前現代人類的時空敘事中也存在循環的思想,但這種循環是一種無法與周遭自然世界分離的靜態循環。有西方學者指出,“我們在希臘思想中發現了把時間說成是循環的或重復的許多不同觀念”,“荷馬也提到了年的‘復歸’”(24)路易·加迪等:《文化與時間》,鄭樂平、胡建平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6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時常出現“年復一年”“周而復始”這樣的時空認知。無論是“復歸”的循環還是“周而復始”的循環都意味著一種重復,它是過去的一次又一次抵達,在一圈又一圈的疊加中形成一個封閉的圓環。這種循環之中蘊含了較為有序的時空流逝觀念,在整體上趨于穩定甚或靜止。后工業時代的時空循環敘事顯然與此種近乎靜止的前現代時空循環敘事有著極為鮮明的不同。按照利奧塔的說法:“建立在電子學和信息處理之上的各種技術,它們的重要性在于它們更多地解放了地球上的生活條件,解放了對記憶生成的編排和操控,也就是說把不同的時間綜合為唯一的時間。”(25)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非人:漫談時間》,夏小燕譯,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89頁,第91頁。此時的“文化模式并不是一開始就根植于地方語境中的,而是由于地球表面的最廣傳播立馬形成的”(26)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非人:漫談時間》,夏小燕譯,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89頁,第91頁。。這就意味著與周遭世界聯結的循環意義體系遭到了瓦解,時空敘事體系被徹底打開,從趨于穩定的狀態走向了一種被電子系統編織的復雜流動狀態。即便是有關時空循環的敘事也不再著力于對過往的再現,而是試圖在反復性過往再構的間隙中制造差異。《恐怖游輪》《源代碼》《環形使者》皆屬此類作品,《星際穿越》更是在以循環貫穿始終的基礎上,構筑了一種超越多重時空維度的宇宙間循環,拓寬了我們對時空循環敘事的認知域。
如果說前現代時空循環敘事的核心在于趨于同一的穩定狀態,那么后工業時代時空循環敘事的核心則在于制造流動中的差異與變化,從而使每一次循環都成為一個新的意義生產鏈。《星際穿越》的整個故事便是在一種流動式的循環中展開的。在故事的開頭,被卷入黑洞的男主人公借助高維生物創造的時空回到過去,以引力波砸落三維時空中女兒書房墻壁上的書,試圖提醒女兒阻止過去的自己前往宇宙探險,卻以失敗告終,他眼睜睜地看著過去的自己再度走向現在的時空,循環亦由此開始。這場循環貫穿了整部電影始終,成為推進故事發展的重要動力。它并不僅僅是已發生事件的一次復歸,而是多維時空的差異性并置。在事件第一次開始時,只有三維時空中的一個男主人公。當事件第二次開始時,存在高維時空與三維時空、未來的男主人公與過去的男主人公之間的并置。對過去的男主人公來講,一切都未發生,還有太空探險等待著他去完成。但對卷入黑洞被困高維空間的未來男主人公來講,他要打破循環發生的過去,創造一條通往新的未來的路徑。依照影片的設定,在高維生物制造的時空中時間是可以觸摸的實體,男主人公可以輕易地完成時間穿梭回到過去,他雖不能突破所處時空的限制,卻可以通過引力波向身處三維時空的女兒傳遞量子數據信息,助她找到新的家園與太空中的自己。循環在此不僅跨越了多個時空維度,還打破了過去的重復狀態,生成了一個在流動中轉化的循環結構。在這種跳出循環的時空循環敘事方式中,循環的意義由復現變成了制造差異。循環系統也因差異而被打開,具有了產生新通道的可能性,于多維宇宙中呈現出放射狀的敞開狀態。此種時空循環敘事邏輯已然與傳統意義上的循環敘事大相徑庭,顯現出后工業時代的新時空循環想象。
四、時空逆轉敘事的瞬時性與斷裂性
逆轉時空的想象與敘事在當下社會文化中有著較高的關注度。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不僅涉及人類對現在與未來時空的新理解,同時也關涉人類在面臨新技術變革時對未來世界的隱憂。時空逆轉意味著時間的倒流,該類型作品往往講述主人公從未來或者現在回到過去對過去施加影響的故事。我國目前的網絡小說與自制劇中就存在大量的此類作品,它們被統歸為“穿越”題材。不過, “穿越”主題作品一般將時空逆轉作為一種預設前提,并不以此為主要敘事內容。對時空逆轉問題有較多討論與演繹的,通常是科幻類文藝作品。諾蘭的電影《信條》便以大量的篇幅對時空逆轉問題進行了描寫。《信條》的故事背景是一起未來人類與現在人類的爭端。由于現世人類對各類資源與能源的消耗導致未來人類陷入生存危機,因此未來人類中的一些群體試圖毀滅現世人類,從而改變其自身的生存境遇。時空逆轉便成了未來、現在與過去發生交互作用的重要方式,每一個瞬間都成了連接新未來的重要入口,時空逆轉敘事中的瞬時性與斷裂性亦由此顯現。
按照影片的設定,人類可以通過一種時空逆轉裝置進入倒流的時空之中。在這一時空中,現在會流向過去,今天會流向昨天。由此人類可以利用這一裝置進入逆向時空,等待時間流動到自己希望到達的過去時刻時再利用機器轉回到正向時間,從而得以回到過去,并再度從過去走向現在。在整個逆轉過程中,時間沒有出現斷層,但時空的序列增多了。在這種設定中,源始時空、逆向流逝的時空、通過兩重逆轉再度回歸正向流逝的時空之間會發生交疊現象,多個時空序列也會在彼此交疊的瞬間相互作用糾纏,一個新的未來時空便有了生成的可能。
因此,瞬時性是時空逆轉敘事的重要特質。它意味著每一個“瞬間”都有可能成為改變未來時空的重要節點,其背后蘊含著過去、現在與未來交互作用的復雜關系。通常而言,時空逆轉敘事的核心意圖在于重寫已發生的事情,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以現在作為切入點,進入一個與現在處在同一條時間線上的過去對其施加影響,從而構筑出一個新的未來。這就牽涉到“現在”或者說“此刻”的來源問題。關于這一問題有兩種思考路徑:一是肯定時間內部的連續性,將“此刻”視為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統一;二是拆解時間內部的連續性,將“此刻”視為一個無數可能性綻出的動態性瞬間。
胡塞爾以意識統一性所建構的連續性時間當屬第一種。其在《內時間意識現象學》中提出了一個“滯留-原印象-前攝”的時間結構。按照他的解釋, “原印象”在狹義上指當下、現在與此刻,它區分了過去和將來;“滯留”是流入過去的現在,它如同逐漸變弱的聲音一般向消逝的方向延展(27)埃德蒙德·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現象學》,倪梁康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62頁。;“前攝”則是現在對未來的敞開與預期,“它是可確定的將來意象”(28)埃德蒙德·胡塞爾:《關于時間意識的貝爾瑙手稿(1917—1918)》,肖德生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8頁。。胡塞爾在此將“過去”與“未來”統攝于“現在”之中,建構了一種意識時間的連續性。梅洛龐蒂將之解釋為:“新的現在是從一個將來到一個現在、從以前的現在到過去的轉變,時間一下子從一端運動到另一端。”(29)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524頁。這顯然肯定了現在所具有的廣延和深度,確證了時空內部的連續性與統一性。
但利奧塔卻從對這種連續性的解構開始,開啟了第二種有關時空問題的思考路徑。他認為,在信息迅速更迭的后工業化時代,意識無法“攬括各種(如今天人們所說,‘信息的’)時刻而且每次必然將這些時刻現時化”(30)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非人:漫談時間》,夏小燕譯,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87頁,第85頁。。也就是說, “意識”的連續性并不總能葆有對信息化時間更新的能力。因此,“當下無法如其所是的被把握,它是絕對的,它不能與其他當下綜合在一起,它可以與其他當下有關系,其他當下必然而且即刻變成被呈現的當下,也就是被變成過去。”(31)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非人:漫談時間》,夏小燕譯,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87頁,第85頁。這一觀點徹底地與胡塞爾等人對“現在”的解釋劃清了界限,將現在從連續性、均質性的線性時間中抽離出來,使之成為一個具有偶在性的時刻。在利奧塔看來,與流動化的信息社會相適應的是一種離散化、非連續性乃至瞬時性的時間。“現在”在他這里成了一個極具偶然性與動態性的瞬間。
利奧塔與胡塞爾的分歧,是關于“現在”的連續性與偶在性之間的分歧。其爭執的焦點在于,“現在”究竟是一個由過去與未來有序綜合而來的時刻,還是一個在與過去、未來的相互糾纏中造就的動態性瞬間。這關涉時空逆轉敘事的根本性問題,即時空如何被改寫。《信條》似乎還是更偏向于利奧塔式的瞬時性時空敘事策略,在多個時空交織的瞬間編織出了新的未來。雖然按照影片的設定邏輯,無論是初始時空或者說通過逆轉裝置再造的新時空皆以一種線性的方式流逝,每一個“現在”都有一個過去作為依托,但未來并沒有依照胡塞爾式的邏輯在現在中得到綜合,即將發生的一切并不具有預兆性,它并未與過去一起統一于“現在”之中。“現在”成了一個極不穩定的瞬間,在多個不同時空序列的糾纏中坍塌向未來。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續性關系在此轉變為一種博弈性關系,時空逆轉敘事中潛藏的斷裂性文化意識也由此顯現。
斷裂既是時空逆轉題材科幻作品的底層文化邏輯,也是后工業時代時空敘事的重要表征。在時空逆轉類科幻作品中,過去和未來都成為被改寫的對象,時空的穩定性與連續性遭到質疑,斷裂的文化意識貫穿始終。《信條》更是將這種斷裂意識擴大化,以未來人類向過去人類的攻擊為敘事推力。按照傳統的歷史邏輯,未來是現在和過去的延伸與承續,未來人類對先祖應當保有一定的尊重。但在《信條》中,這一歷史文化上的連續性邏輯被徹底瓦解。未來人類將先祖當作一種負擔,認為其消耗了過多的能源與資源以致未來環境惡化,故而試圖剿滅他們以改善自己的生存境況。這種與過去的徹底斷裂雖具有一定的驚奇與夸張色彩,卻顯現出后工業時代的某種典型性文化癥候。
斷裂意識早就在現代性思想中埋下了伏筆。伯曼援引馬克思“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的論斷來描述一種現代性的體驗,并且明確指出:“現代性從根本上威脅到了自己的全部歷史與傳統。”(32)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現代性體驗》,徐大建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6頁。吉登斯更是在《現代性的后果》中提出了“現代性的斷裂”這一論點,指出“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從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態”(33)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4頁。。依照這些學者的觀點來看,現代性內部蘊含著一股對歷史與傳統的剝離力量,至少在形式上與過去的社會形態產生了斷裂。后現代主義理論家詹姆遜則將這種形式的斷裂擴大到意義的斷裂。他認為, “歷史的意識在后現代主義文化普遍的平淡和淺薄中已經消失了。”(34)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290頁。從現代性思想中孕育出的對傳統的懷疑至此被推向了極致,一種強烈的斷裂沖動毫不遮掩地顯現出來。斷裂敘事不僅意味著與過去聯系的瓦解,同時也潛藏了歷史意義消散的隱憂。世界建立的可靠性因此遭遇一種根源性質疑,科幻作品中大量涌現的時空逆轉敘事也就不足為奇了。
時空逆轉類科幻電影用有關未來的想象來反思當下的文化問題,將今日人類文化意識中對斷裂的理解投射到未來人類身上,呈現出人類與其歷史之間復雜與矛盾的關系。這種時空內部的博弈同時也蘊含著深刻的人類世隱憂。在信息技術、數字技術以及智能技術不斷革新的社會中,世界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與無參照性愈發顯現。過往的歷史經驗愈發難以解釋正在發生的一切,人類對難以預測的未來懷有極大的憂慮。時空逆轉敘事中的瞬時性與斷裂性皆為此種憂慮的顯現。有所不同的是:斷裂性更像是一種對危機的診斷;瞬時性則在強烈的不穩定與不可控性中暗藏了新生的可能。如同《信條》的時空糾纏中既蘊含了摧毀的力量也蘊含了拯救的力量一般,時空逆轉類科幻作品總是在未來與現在之間設置無數的通道,冀圖在這無盡的變數中尋找新生。科幻想象在此終究為后工業時代的文化危機給出了一種假設性解決路徑。
五、結 語
科幻電影在對虛擬時空、宇宙時空與未來時空的呈現中,構筑了人類思考多維時空問題的參照系。多樣態的時空敘事映照著人類對所處世界的不同思考維度與探索維度。與虛擬時空敘事相聯結的是電子化、景觀化的生存狀況。在信息技術日益發展的時代中,虛擬化生存已然成了一種新的生存形態。現實感知與虛擬感知的邊界不斷模糊,人類意識依靠科技賦形參與到虛擬世界的構造之中,伴隨著大量數字與符碼的編織,意識的分裂性被顯露到極致,虛擬與現實糾纏所帶來的不穩定性也在科幻的世界里得到充分表達。宇宙時空敘事所承載的則是人類探索地外星系的強烈欲望,不過由于缺乏對未知宇宙的直觀經驗,科幻作品往往以人類所處世界的認知為參照來想象宇宙中人的復雜狀態。流動性與循環性的敘事特質除了觀照宇宙自身的不可預測性,同時也指向了人類有別于以往的時空流動體驗。未來時空敘事的內部所隱藏的是一種對過去與未來關系的新理解與新想象,時空的逆轉便意味著對過去與未來的重寫。但是當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浪潮卷過,時空的穩定性與連續性遭到質疑,斷裂的意識便悄然萌生于逆轉時空的科幻想象之中。這種強烈的斷裂感混合著人類世資源枯竭的隱憂,頻頻涌現于科幻作品中,時刻提醒人類以危機意識洞察生機。科幻電影時空敘事的本質亦由此逐漸顯露,其以不同的時空樣態為變量,在投射人類精神危機與文化反思的種種境況的同時,又為處身于虛擬蔓延世界中的人類構造出一重照見自身的虛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