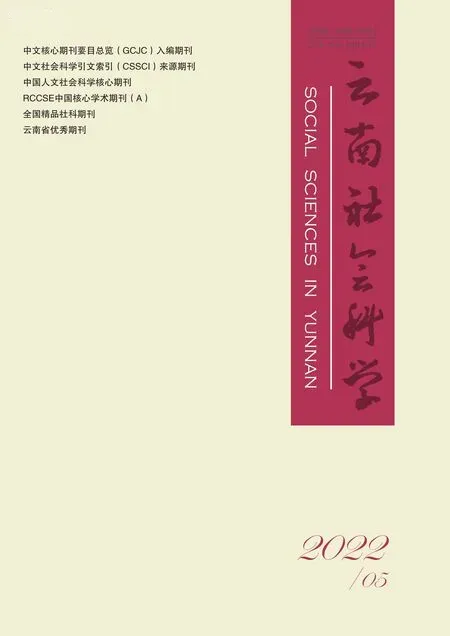論法人責任歸屬規則
——《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解釋論重構
孫新寬
《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是關于法人為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行為承擔責任的重要規范。中國民法理論對該款的認識包括兩個重要層面:第一,在理論層面,認為該款的重要作用是在實證法上采納了法人實在說①參見李適時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釋義》,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年,第174—175 頁;梁慧星:《民法總論》(第6 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年,第138 頁。;第二,在適用層面,一般認為該款僅適用于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引起的侵權責任②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編釋義》,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 年,第154 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編理解與適用》(上),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第326 頁。。上述觀點均值得商榷。其一,《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不同的法人理論之下都有可能得到解釋,比較法上也有類似例證。③Vgl.Staudinger/Schwennicke (2019) BGB § 31,Rn.3 ff.其二,在適用上,《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所規定的法律效果為“民事責任”,并不僅限于“侵權責任”,該款是否可以適用于違約責任、締約過失責任值得探討。有必要對《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規范屬性與適用范圍予以深入研究,以明晰其理論定位,促進該款在司法實踐中的正確適用。
一、《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作為法人責任歸屬規則
(一)《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與法人本質理論無關
關于法人本質問題,學界長期存在法人擬制說和法人實在說的爭論,而法人是否具有侵權能力,往往被看作是法人實在說與法人擬制說的重要區分標準。①謝鴻飛:《論民法典法人性質的定位——法律歷史社會學與法教義學分析》,《中外法學》2015 年第6 期。學者們在理論上往往將《民法典》第62 條第1款理解為中國法承認法人侵權能力和法人實在說的證據,主要理由是基于法人實在說的立場,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造成他人損害的行為即為法人自身的侵權行為,故應由法人承擔侵權責任。②李適時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釋義》,第174—175 頁。但《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能否被認為是支持法人實在說的證據,不無疑問。比較法上,《德國民法典》第31 條的規定與中國《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類似,且同樣存在法人實在說和法人擬制說的爭論,因此,對《德國民法典》第31 條的相關爭論進行簡要介紹,可以為理解《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提供重要參考。
1.《德國民法典》第31 條未采納任何一種法人本質理論
《德國民法典》第31 條制定過程中的下述立法材料可以清楚地展現該條背后的立法理由:“毫無疑問的是,團體作為無意志的存在不具有侵權能力,然而新近的法律發展展現了……決定性的趨勢,即讓團體承擔廣泛的民事責任,而且,這種法律觀基于不容忽視的交易需求。特別是,當代理人的行為違反所謂的法定債務時,或者,當團體經營營業且代理人在執行營業活動中損害第三人時,司法判決確定了這種責任。在對這種責任進行論證時,人們正確地指出,當團體通過代理獲得在法律交往中的行動可能時,其也必須承擔此種人為允許的代理所帶來的不利后果。”③該段為本文作者翻譯,原文參見Horst Heinrich Jakobs/Werner Schubert (Hrsg.),Die Beratung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in systematischer Zusammenstellung der unver?ffentlichten Quellen,Allgemeiner Teil,1.Teilband,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1985,S.164 f.
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德國民法典》第31 條采取了實用主義的立法思路,目的是滿足實踐中的交易需求,并以公平思想作為價值基礎,法人通過代理人對外做出行為并獲得利益,也就要承擔由此可能產生的損失。④Vgl.Detlef Kleindiek,Deliktshaftung und juristische Person,Zugleich zur Eigenhaftung von Unternehmensleitern,Tübingen:Mohr Siebeck,1997,S.244 f.在這種實用主義立場下,立法者并未借助《德國民法典》第31 條在不同的法人本質理論之間進行選擇。⑤Vgl.Jan-Erik Schirmer,Das K?rperschaftsdelikt,Tübingen: Mohr Siebeck,2015,S.180.
事實上,《德國民法典》的立法史也表明,其在制定時對法人的性質未采納任何一種理論。《德國民法典》的立法理由書認為法人制度不可或缺,同時明確指出“對(法人)概念的建構和正當化是學術的任務”⑥Benno Mugdan (Hrsg.),Die gesammten Materialien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Band 1:Einführungsgesetz und Allgemeiner Theil,Berlin: R.v.Decker's Verlag,1899,S.395.。由此可見,《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認為法人概念與本質的討論屬于學術理論問題,無須通過在法典中制定具體規則予以解決。《德國民法典》早期的評注也認為,很難確定《德國民法典》采納了何種法人理論,而且,也無須借助某種特定的法人理論來理解《德國民法典》的具體規定。⑦Vgl.Fred G.B?r,in: Mathias Schmoeckel/Joachim Rückert/Reinhard Zimmermann (Hrsg.),Historisch-kritischer Kommentar zum BGB,Band I,Tübingen: Mohr Siebeck,2003,§§ 21-79,Rn.13 (S.241).
2.《德國民法典》第31 條與不同法人本質理論的兼容性
在法人擬制說之下,法人被擬制為具有權利能力,但法人天然沒有行為能力(Handlungsunf?higkeit),因為“行為”以思想或意志的存在為前提。⑧Vgl.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Band 2,Berlin: Bei Veit und Comp.,1840,S.282.對于法人對外做出行為的現實需求,薩維尼通過“代理”予以解決,代理人通過法人的組織而產生⑨Vgl.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Band 2,S.283;Werner Flume,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Erster Band,Zweiter Teil,Die juristische Person,Berlin,Heidelberg,New York,Tokyo: Springer-Verlag,1983,S.14.,符合法人組織結構的代理人之行為被“評價為”(angerechnet)法人自己的行為⑩Vgl.Werner Flume,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Erster Band,Zweiter Teil,Die juristische Person,S.15.。在法人侵權的問題上,薩維尼認為,“由于任何真正的侵權都以故意或過失為前提”,而法人欠缺思想意志,不能承擔侵權責任。①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Band 2,S.317;Werner Flume,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Erster Band,Zweiter Teil,Die juristische Person,S.15.根據《德國民法典》第31 條的規定,法人須對其機關在執行職務時引起的侵權責任負責,但在支持法人擬制說的學者看來,這只是立法者補充規定了法人須對機關的非法律行為(如侵權行為)負責②Vgl.Staudinger/Weick (2005) BGB § 31,Rn.2.,而非在立法上拋棄了法人擬制說。
在法人實在說看來,法人具有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法人機關的侵權行為被看作是法人自身的侵權行為,因此,法人實在說的支持者認為,《德國民法典》第31 條只是確認了其理論主張,即法人須為其機關實施的侵權行為承擔責任。③Vgl.Staudinger/Schwennicke (2019) BGB § 31,Rn.4.
由此可見,《德國民法典》第31 條的規定并未消除法人擬制說和法人實在說的分歧,兩種理論的支持者都在該條中找到支持自己立場的論據。時至今日,這種爭論依然并未結束。
3.《民法典》第62 條與法人本質理論
再來看中國的情況,在《民法典》頒布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43 條被解讀為我國法承認了法人侵權能力,從而作為我國法采納了法人實在說立場的重要證據。④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第4 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年,第120、133—134 頁。也有觀點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06 條第2 款是法人侵權能力的規范基礎,參見朱慶育:《民法總論》(第2 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465—466 頁。如今,《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被認為是法人實在說在中國實證法上的延續。但上述對《德國民法典》第31 條的分析恰恰表明,法人侵權責任的實證法規定與法人本質理論并無必然關聯,立法者基于法律安定性和實踐中法律交往的需求,對法人侵權責任在實證法上作出規定,并不意味著是對某種法人本質理論的選擇。這也完全可以適用于對《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解釋。更重要的是,無論采納何種法人本質理論,對《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適用并不會產生實質差異,將該款與特定的法人本質理論相關聯并無實踐意義。對《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研究應更多關注其在法律適用上的作用。
(二)《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性質是法人責任歸屬規則
《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法律適用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性質上是法人的“責任歸屬規則”⑤明確提及該款屬于“責任歸屬規則”的觀點,參見陳甦主編:《民法總則評注》(上冊),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年,第433 頁。德國法上的觀點,vgl.Staudinger/Schwennicke (2019) BGB § 31,Rn.1.,其重要功能是將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對第三人引起的損害賠償責任歸屬于法人承擔,第三人從而可以向法人主張責任。
《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本身不是獨立的請求權基礎規范,該款必須結合其他具體的請求權基礎規范才能適用。例如,A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甲在執行職務時對乙造成人身傷害,受害人乙向A 公司主張侵權損害賠償時,除滿足《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要件之外,法定代表人甲的行為還須滿足《民法典》第1165 條第1 款的構成要件,尤其是法定代表人甲須有過錯,否則,A 公司無須為甲的行為向乙承擔侵權責任。《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僅規定了行為主體(“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損害”和因果關系等要件,并未規定法定代表人的“過錯”要件,對構成要件的規定是不完備的,因此,向法人主張民事責任的請求權人還須以其他具體的請求權基礎規范為依據。⑥陳甦主編:《民法總則評注》(上冊),第432—434 頁。由此可見,《民法典》第62 條第1款的主要作用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請求權基礎規范,而是通過規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這一核心要件,將法定代表人對第三人引起的民事責任歸屬于法人承擔。
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哪些請求權基礎規范可以適用于《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民法典》第62條第1 款所規定的法律效果為“民事責任”,雖然“民事責任”可以包含《民法典》第179 條第1 款所列舉的全部11 類民事責任,但由于《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責任成立層面上規定了“損害”要件,因此,不以“損害”為構成要件的民事責任即被排除在該款的適用范圍之外。例如,一般認為,“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這三種防御性請求權不以“損害”為責任成立要件①程嘯:《侵權責任法》(第3 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年,第747 頁。,《民法典》第236 條和第1167 條也均未要求“損害”要件,因此,此類規定防御性請求權的請求權基礎規范即不適用于《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②此種限制在立法論上值得探討,例如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時對第三人造成妨礙,可能有必要使第三人向法人主張排除妨礙等防御性請求權,這里同樣涉及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法律效果歸屬于法人的問題。
在民事責任類型上,損害賠償責任是最典型的以“損害”為要件的責任類型,《民法典》第179 條第1 款第8 項規定的“賠償損失”毫無疑問可以歸入第62 條第1 款的適用范圍。《民法典》上可以產生損害賠償責任的規范眾多、類型不一,其中,侵權損害賠償責任、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和締約過失損害賠償責任是尤為典型和重要的三種損害賠償責任類型。現有文獻中將《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限縮適用于“侵權責任”的觀點明顯有悖該款文義。③認為《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適用范圍不限于侵權責任的類似觀點,參見陳甦主編:《民法總則評注》(上冊),第432—433 頁。下文針對侵權損害賠償、違約損害賠償與締約過失損害賠償這三種典型的賠償責任,分別研究其與《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適用關系,以明晰該款的適用范圍,進而為其在司法實務上的正確適用奠定基礎。
二、《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適用范圍
(一)《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與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當《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適用于侵權領域時,其涉及的是法人對“法定代表人”侵權行為承擔責任的問題(下文稱為“法人侵權責任”)。與此相對,《民法典》第1191 條第1 款第1 句規定了用人單位為工作人員的侵權行為承擔責任(下文稱為“雇主責任”)。二者在適用上的關系④關于二者關系的歷史梳理,參見翁國民、馬俊彥:《論用人單位侵權責任的統一與分立——基于法人侵權責任與雇傭人侵權責任的關系視角》,《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2 期。,主要取決于如何對《民法典》第1191 條第1 款第1 句中的“工作人員”進行解釋。如果對“工作人員”做較為廣義的解釋,認為其包含“法定代表人”,則就侵權領域而言,《民法典》第1191 條第1 款第1 句在適用上就可以涵蓋《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如果對“工作人員”做較為狹義的理解,認為其不包含“法定代表人”,那么法定代表人的職務侵權行為就僅能適用《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而不能適用《民法典》第1191 條第1款第1 句,《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侵權領域將具有獨立的適用意義。但即便采第二種解釋,法人侵權責任與雇主責任的區分在中國也僅具有形式意義,并無獨立的司法適用價值。
在德國法上,《德國民法典》第31條與第831條在功能上分別類似于中國《民法典》第62條與第1191條。但德國法的規定與中國有重大不同。《德國民法典》第831 條第1 款規定了雇主為事務輔助人所負的責任,但該款第2 句⑤該句規定:“雇主在挑選被用人時,以及,在雇主須置辦設備或工具時或須指揮事務的執行時,雇主在置辦或指揮上盡到了交易上必要的注意,或即使盡到了此種注意損害仍會發生的,不發生賠償義務。”同時規定了雇主可以免責的情形,如今在學理和司法實踐上認為,雇主的免責事由是其盡到了交往上必要的注意義務,具體表現為盡到了選任、監督、指示義務。⑥Vgl.MüKoBGB/Wagner,8.Aufl.,2020,BGB § 831,Rn.40-43.與此不同,《德國民法典》第31 條并未規定法人的免責事由。⑦Vgl.MüKoBGB/Wagner,8.Aufl.,2020,BGB § 831,Rn.20.因此,在具體案例中適用《德國民法典》第831 條還是第31 條,會對責任分配產生重要影響。實踐中,為避免雇主依據《德國民法典》第831 條第1 款第2 句免責,發展出多種規避該句適用的策略⑧Vgl.MüKoBGB/Wagner,8.Aufl.,2020,BGB § 831,Rn.2.中文文獻參見李昊:《交易安全義務論——德國侵權行為法結構變遷的一種解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453—461 頁。,其中一種策略即是擴大解釋《德國民法典》第31 條中“機關”的范圍⑨李昊:《交易安全義務論——德國侵權行為法結構變遷的一種解讀》,第455—456 頁。。銀行分支機構的負責人、診所的主任醫師、供氣企業的工程師實施的侵害行為,都被適用于《德國民法典》第31 條,從而使雇主無法免責。①Vgl.MüKoBGB/Wagner,8.Aufl.,2020,BGB § 823,Rn.120.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個案中是適用《德國民法典》第31 條還是適用第831 條對當事人的責任承擔具有重要影響,二者的區分具有直接的實踐意義。另一方面,為規避《德國民法典》第831 條的免責事由而擴展適用第31 條的做法,使二者不斷趨同,一旦在雇主責任中放棄免責事由的規定,也就沒有必要再進行這種規避。②Vgl.MüKoBGB/Wagner,8.Aufl.,2020,BGB § 823,Rn.120.
中國《民法典》的規定與德國法不同。《民法典》第1191 條第1 款第1 句并未要求用人單位自身的“過錯”要件,也未如《德國民法典》第831 條第1 款第2 句那樣規定用人單位的免責可能,理論上也認為用人單位承擔嚴格責任。③程嘯:《侵權責任法》(第3 版),第450—451 頁。在這種用人單位為雇員承擔嚴格責任的規定下,德國法上雇主因盡到選任、監督、指示義務而得以免責的可能,在中國并不存在。由此可見,《民法典》第1191 條第1 款第1 句與《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用人單位的歸責問題上是一致的,這使得法人侵權的規定完全可以被雇主侵權的規定吸收,④我國有學者早已指出了這一點,參見蔡立東:《論法人之侵權行為能力——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的相關規定》,《法學評論》2005 年第1 期。《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侵權責任領域不具有獨立的價值。
(二)《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與違約損害賠償責任
1.法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歸屬
法人對外簽訂合同,既可以通過法定代表人進行,也可以通過其他工作人員進行(《民法典》第170條第1 款),一旦合同對法人生效,法人成為合同主體,合同義務即為法人自身的義務。法人在履行合同義務時,有可能通過法定代表人向相對人履行,如果法定代表人在履行合同時做出違約行為,此時可能經由《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由法人向合同相對人承擔違約責任。
我國法上,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既有嚴格責任也有過錯責任。在違約損害賠償為嚴格責任的情形下,如《民法典》第577 條⑤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4 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年,第748 頁。,當法定代表人做出違約行為并造成相對人損害時,法定代表人的行為產生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此時可進一步依據《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由法人向相對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如果法定代表人對其違約行為具有免責事由,如構成不可抗力(《民法典》第590 條第1 款第1 句),此時法定代表人的行為不產生違約責任,法人進而也可以免責。
在違約損害賠償為過錯責任的情形,如《民法典》第929 條,當法定代表人做出違約行為并引起相對人損害時,法定代表人還須具有過錯才會產生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此時,根據《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法人須為法定代表人履行合同過程中產生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向相對人承擔責任。
2.《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與第593 條第1 句的關系
雖然學界和司法實務上對《民法典》第593 條第1 句中“第三人”的范圍界定有不同主張,但應無疑問的是,該句規定中的“第三人”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履行輔助人”。⑥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釋義》,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 年,第308 頁;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4 版),第756 頁。有疑問的是,法定代表人是否屬于《民法典》第593 條第1 句意義上的“第三人”。如果將法定代表人納入該條中的第三人范圍,則法定代表人為法人履行合同而產生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時,合同相對人可以援引《民法典》第593 條第1句向法人主張違約責任。同時,由于法定代表人為法人履行合同一般屬于執行職務行為,《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違約損害賠償責任上也可以適用。此時對二者之間的適用關系需要作進一步解釋。
對此,第一種解釋方案是,認為法定代表人不屬于《民法典》第593 條第1 句意義上的第三人,主要理由是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就是債務人自身的行為”①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釋義》,第308 頁。,此種觀點的理論基礎仍是法人實在說。此時,合同相對人若要向法人主張違約責任,則只能援引《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由法人為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做出的違約行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第二種理解是,認為法定代表人屬于履行輔助人中的“法定代理人”,落入《民法典》第593 條第1 句中的“第三人”范圍,此時,《民法典》第593 條與第62條第1 款同樣適用。兩種理解在效果上并無實質差異,合同相對人均可以向法人主張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由于第一種解釋方案的主要依據是法人實在說,只要不固守法人實在說的立場,完全可以將法定代表人納入《民法典》第593 條第1 句中“第三人”的范圍,那么《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法人的違約損害賠償問題上將喪失獨立的適用意義。
(三)《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與締約過失損害賠償責任
如果法定代表人在執行職務中的行為引起締約過失責任(如構成《民法典》第500 條),即產生法人是否要為法定代表人的締約過失行為承擔責任的問題。例如,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虛構相關事實與相對人訂立合同,之后,該合同因法定代表人的欺詐行為被撤銷。②實踐案例如“廣東黃河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與北京然自中醫藥科技發展中心一般股權轉讓侵權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終字第62 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9 年第1 期(但該案當事人未主張締約過失責任)。合同因欺詐而被撤銷后,無論是依據《民法典》第500 條第2 項或第157 條第2 句,相對人都有權要求賠償損失,此種損害賠償在性質上屬于締約過失損害賠償。③孫維飛:《〈合同法〉第42 條(締約過失責任)評注》,《法學家》2018 年第1 期。引起締約過失的行為由法定代表人做出時,在現行法下,法人如何為法定代表人的締約過失行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是法律適用上的一個重要問題。
筆者認為,此時應適用《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將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行為引起的締約過失責任歸屬由法人承擔。首先,《民法典》第593 條僅適用于“違約”情形,對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引起的締約過失責任不能適用,而《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文義上沒有此種限制,適用于締約過失責任并無障礙。其次,上文已經探討,《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適用上也并不限定于侵權損害賠償責任,該款作為責任歸屬規則,本就可以適用于不同類型的損害賠償責任。最后,如果否認《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締約過失責任問題上的適用,將導致現行法上沒有其他法律規范可以處理法人為法定代表人締約過失行為承擔責任的問題,形成法律漏洞。由此也可以看出,與侵權損害賠償和違約損害賠償相比,《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在締約過失責任適用上具有獨立的價值。
三、《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與越權代表無效責任
(一)越權代表無效時法人責任歸屬的可能性
當法定代表人逾越其代表權而與第三人簽訂合同時,其法律效果主要為三種情形:其一,法人對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予以追認,合同對法人產生效力(情形1);其二,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構成表見代表(《民法典》第504 條),合同對法人產生效力(情形2);其三,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既未被法人追認,也不構成表見代表,合同對法人不發生效力(情形3)。以下的討論針對情形3 展開。
在情形3 中,第三人無法依據合同向法人主張權利,但第三人因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遭受損害時,有可能向法定代表人主張損害賠償責任,其可能的法律依據主要包括三種。第一,類推適用《民法典》第171 條第3 款或第4 款。據此規定,無權代理未被追認又不構成表見代理時,無權代理人須向相對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法定代表人與法人之間的關系雖然一般認為屬于代表而非代理,但代表與代理之間具有同質性,④殷秋實:《法定代表人的內涵界定與制度定位》,《法學》2017 年第2 期。由于越權代表可能產生的損害賠償責任在現行法中并無單獨規定,故有必要類推適用無權代理的相關規定,第三人類推適用《民法典》第171 條第3 款或第4 款,可向越權的法定代表人主張損害賠償責任。第二,可能適用締約過失責任(《民法典》第500 條)。法定代表人越權訂立合同,可能同時構成締約過失責任,如法定代表人“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第三,法定代表人無效的越權代表行為還可能構成侵權責任(《民法典》第1165 條第1 款)。法定代表人越權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無效時,第三人由于合同無效而遭受的損失一般屬于純粹經濟損失,此時成立侵權責任須滿足更為嚴格的要件,①程嘯:《侵權責任法》(第3 版),第196 頁。通過一般侵權條款對純粹經濟損失進行保護的不同模式,參見葛云松:《純粹經濟損失的賠償與一般侵權行為條款》,《中外法學》2009 年第5 期。但在法定代表人故意欺詐第三人等情形中,依然存在成立侵權責任的可能。②欺詐訂立合同可構成侵權責任,參見許德風:《欺詐的民法規制》,《政法論壇》2020 年第2 期。
在法定代表人根據上述情形對第三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時,由于越權代表行為經常同時構成執行職務,第三人因此可進一步主張適用《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要求法人承擔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行為給第三人造成的損失。由此,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無效行為所引發的損害賠償責任可能被歸屬于法人承擔(情形4)。
(二)越權代表無效時法人責任歸屬引發的體系沖突與解決路徑
1.越權代表無效時法人責任歸屬引發的體系沖突
法人對法定代表人越權行為的追認權(情形1)是對法人利益的保護。對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法人若不追認,法定代表人越權訂立的合同對法人不發生效力,法人免于為法定代表人的越權行為承擔不利后果,從而獲得保護。③德國法上關于這種保護功能的分析,vgl.Helmut Coing,Die Vertretungsordnung juristischer Personen und deren Haftung gem?? § 31 BGB,in: Marcus Lutter/Walter Stimpel/Herbert Wiedemann (Hrsg.),Festschrift für Robert Fischer,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1979,S.65 f.表見代表制度則對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給予了保護(情形2)。法定代表人做出越權代表行為時,若構成表見代表,法定代表人越權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對法人發生效力,第三人從而可以向法人主張履行合同或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由此可見,對于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行為,法人的追認權和表見代表制度為法人承擔的責任劃定了邊界。
越權代表行為無效時,法定代表人給第三人造成的損失可能接近或等同于代表行為有效時法人可能向第三人承擔的責任。④Vgl.Claus-Wilhelm Canaris,Schadensersatz -und Bereicherungshaftung des Vertretenen bei Vertretung ohne Vertretungsmacht -BGH,NJW 1980,115,JuS 1980,332,334.例如,甲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乙越權以甲法人的名義與丙銀行訂立借款合同,乙之后私吞了丙銀行發放的貸款,⑤Vgl.BGH NJW 1980,115.丙銀行的損失即是貸款數額。乙的越權代表行為若未被甲法人追認且不構成表見代表時,由于乙可能須向丙銀行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丙銀行可經由《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主張由甲法人承擔乙引起的損害賠償責任(情形4),賠償數額為丙銀行發放的貸款數額。此時,甲法人承擔的責任可能與代表行為有效時的責任相同。因為,在甲法人追認乙的越權代表行為(情形1)或構成表見代表(情形2)時,借款合同在甲法人和丙銀行之間生效,甲法人向丙銀行承擔的義務即是返還貸款數額。由于《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適用,即便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未被法人追認也未構成表見代表,法人卻可能承擔類似于代表行為有效時的責任,從而可能架空法人追認權和表見代表制度所構建的責任劃分模式,引發體系上的沖突。
2.體系沖突的解決路徑
化解上述體系矛盾的路徑在于明晰《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法人追認權和表見代表制度各自的功能定位。首先,制度目的不同。《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重要價值基礎在于公平思想,法人從法定代表人的執行職務行為中獲得利益,相應地也應承受執行職務行為產生的責任與風險。法人的追認權給予法人自治空間,使其自主決定是否承認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行為的效力,也能維護法律對法人不同機關之間做出的權限劃分。表見代表制度則重在保護善意第三人對法定代表人代表權的信賴,維護交易安全。其次,構成要件不同。法人的追認權完全由法人自主決定是否行使,第三人無法強迫法人對越權代表行為進行追認。表見代表制度要求第三人主觀上善意無過失,①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釋義》,第100 頁。有過失的第三人無法獲得表見代表的保護,這是一種全有全無式的責任分配模式。《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核心要件是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對第三人構成損害賠償責任時,有過錯的第三人依然可以向法人要求損害賠償,但此時可適用與有過失規則減輕法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由此可見,《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不是一種全有全無式的責任分擔模式,與表見代表制度不同。
對《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適用所可能引發的體系沖突,需要在考慮上述不同制度的目的和構成要件基礎上,結合法定代表人引發賠償責任的不同請求權基礎進行具體分析。
第一,對于類推適用《民法典》第171條第3款和第4款,法定代表人向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并經由《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由法人向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在無權代理中,若構成表見代理,則由被代理人承擔代理行為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172 條)。若不構成表見代理,且被代理人不追認無權代理行為時,可根據《民法典》第171 條第3 款或第4 款由無權代理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由此可見,《民法典》第171 條第3 款或第4 款規定的無權代理人賠償責任處于表見代理制度的對立面,此處產生的損害賠償責任不應由被代理人承擔。②被代理人仍可能構成締約過失或侵權責任,但這并非是基于代理人的無權代理行為本身而自動發生,參見紀海龍:《〈合同法〉第48 條(無權代理規則)評注》,《法學家》2017 年第4 期。相應地,在不構成表見代表時,法定代表人經類推適用《民法典》第171 條第3 款或第4 款向第三人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也不能經由《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適用由法人承擔,否則,有悖于《民法典》第171 條第3 款或第4 款與表見代理(以及表見代表)之間的制度分工。因此,為了避免這種制度間的價值沖突,需要限縮解釋《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排除《民法典》第171 條第3 款或第4 款于此情形的(類推)適用。③德國法上于此情形會排除《德國民法典》第179 條第1 款在第31 條中的適用,處理方式與本文的主張類似,vgl.MüKoBGB/Leuschner,9.Aufl.,2021,BGB § 31,Rn.32.
第二,對于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引起締約過失責任,經由《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由法人向第三人承擔締約過失責任。首先,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本身通常并不足以直接構成締約過失責任;即使認為法定代表人越權行為本身成立締約過失責任,該責任的性質與《民法典》第171 條第3 款或第4 款實質類似,④理論上有觀點認為無權代理人責任的性質是一種締約過失責任,相關討論及不同觀點參見紀海龍:《〈合同法〉第48條(無權代理規則)評注》。基于相同的理由,此時應當排除此種締約過失責任在《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適用。⑤類似的結論,vgl.Staudinger/Schwennicke (2019) BGB § 31,Rn.59.其次,如果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同時符合其他可以引起締約過失責任的要件(如《民法典》第500 條第2項),法定代表人此時引起的締約過失責任有可能適用《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由法人承擔,但對此應嚴格認定。⑥德國法上的討論,vgl.Staudinger/Schwennicke (2019) BGB § 31,Rn.60.
第三,對于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引起侵權責任,經由《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由法人向第三人承擔侵權責任。若法定代表人的越權代表行為構成侵權責任,筆者認為《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即應適用。侵權責任與代理制度之間所預設的適用場景有異,侵權責任制度重在對一般社會交往中造成的損害進行分配,無論法定代表人是否構成越權代表,只要屬于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給第三人造成的侵權責任,即可適用《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由法人承擔。⑦德國法實務和理論上大多采取這種處理模式,vgl.BGH NJW 1980,115,116;Staudinger/Schwennicke (2019) BGB § 31,Rn.62;MüKoBGB/Leuschner,9.Aufl.,2021,BGB § 31,Rn.32.不同的觀點,參見殷秋實:《公司擔保無效責任的復位——基于責任性質、主體與效果的區分視角》,《法學》2022 年第2 期。
四、結 語
《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不足以作為實證法采納法人實在說的規范依據,對該款的研究應回歸法律適用層面,將其定位于法人的責任歸屬規則。該款的適用范圍包括侵權損害賠償責任、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和締約過失損害賠償責任等多種情形,但由于《民法典》第1191 條第1 款第1 句和第593 條第1 句的存在,該款在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和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適用上并無獨立的適用價值。但對于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引起的締約過失損害賠償責任,《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具有獨立的適用意義。對于法定代表人越權代表無效時的責任問題,首先應辨別法定代表人對第三人構成損害賠償責任的具體規范依據,在考慮法人對越權代表行為追認權、表見代表制度和《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的不同功能基礎上,具體分析是否可以將越權代表無效的賠償責任歸屬于法人承擔。
本文的重要目的是明晰《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作為責任歸屬規則的定位,在此路徑下,可以將法定代表人行為的效果歸屬問題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問題范疇予以研究。例如,法定代表人對物的占有、第三人基于法定代表人的妨害行為發生的防御性請求權等,都會產生法律效果是否歸屬于法人的問題。本文對法人責任歸屬規則的分析對此類問題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具有借鑒意義。